|
|
StarCareHome
本平台医疗信息及相关内容(含个案及研究结论)仅供参考,不构成诊疗、医学建议或疗效保证,相关结论可能存在争议。补剂/药品仅限成分分析(不涉品牌),用户自担使用相关内容、产品及外部链接风险;干预或用药前请咨询执业医师。
《LDN 书卷二:低剂量纳曲酮如何革新治疗的最新研究》
“自《LDN 书》第一卷出版以来,我有幸与综合医学领域最优秀的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一起学习和合作。通
过这些合作,我们将继续扩大这种低剂量但高功效药物的广泛应用。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多值得信赖的同事,
他们也成为了朋友,为这项重要的工作做出了贡献。再次感谢 Linda Elsegood,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集
在一起,继续用这种简单而廉价的干预措施寻找解决具有挑战性的医疗问题的方法。”
Nasha Winters 博士, ND,FABNO, 《癌症的代谢方法》一书的作者
“作为一名药剂师,我常常希望出现一种安全、有效、价格低廉的‘神奇’药物,帮助大众恢复健康。
虽然没有一种药物适合所有人,但我亲眼目睹 LDN 改变了无数自身免疫患者的生活。对于一些人来说,
LDN 确实是一种神奇的药物。我强烈推荐《LDN 手册》的两卷,它们都是患者和临床医生探索使用 LDN
最佳实践的宝贵资源。”
Nasha Winters 博士, ND,FABNO, 《癌症的代谢方法》一书的作者
“自《LDN 书》第一卷出版以来,我有幸与综合医学领域最优秀的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一起学习和合作。通
过这些合作,我们将继续扩大这种低剂量但高功效药物的广泛应用。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多值得信赖的同事,
他们也成为了朋友,为这项重要的工作做出了贡献。再次感谢 Linda Elsegood,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集
在一起,继续用这种简单而廉价的干预措施寻找解决具有挑战性的医疗问题的方法。”
“非常棒的资源。所有关于低剂量纳曲酮及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各种用途的最新研究都汇编在这本易于使用
的书籍中 《LDN 手册》第2 卷。我一定会把这本书放在我的办公室里以供参考。”
Jill C. Carnahan,医学博士,ABIHM,ABoIM,IFMCP
Izabella Wentz 博士,药学博士,FASCP,纽约时报畅销书《桥本疗法》的作者
赞扬LDN 书籍第 2 卷
安格斯·达格利什 (Angus Dalgleish ) 博士,伦敦大学圣乔治肿瘤学教授、癌症疫苗和免疫治疗
研究所 (ICVI) 负责人
Sahar Swidan,药学博士、博士、ABAAHP、FAARFM、FACA,Pharmacy Solutions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还有许多复杂层面有待揭开!”
“即使您认为您通过实践经验或其他方式了解 LDN 对某些疾病的益处,这本书也会扩展您的理解并
让您惊叹不已。一种针对特定疾病设计的药物可以以越来越低的剂量应用于许多其他系统,这是一个
了不起的发现。有趣的是,这向我们表明,许多其他药物在低于预期剂量的情况下也可能具有意想不到
的益处。
158 诊所主任Andrew McCall 博士
“多年来,大量关于 LDN 的临床试验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关 LDN 实际作用方式和原因的更好信
息。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发现了 LDN 在医疗治疗中的许多新用途。阅读《LDN 手册》第 2 卷并了解其
他专家如何在他们的诊所开具 LDN 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享受。我的诊所 158 已经开具 LDN 处方
12 年了。我们有成千上万非常满意的患者,他们发现这种药物可以成功治疗各种疾病,而且我们仍在
学习新信息。”
“由于炎症是几乎所有慢性疾病的主要诱因,LDN 疗法几乎涵盖了所有医学专业。在《LDN 手册》第
2 卷中,作者对 LDN 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出色的概述,回顾了支持临床应用的大量证据基础,最重要的
是,报告了 LDN 在成功治疗患者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实际案例。这本书是每位临床医生的必备书籍,在
治疗其中概述的许多疾病时应考虑使用 LDN。”
有望彻底改变创伤后应激障碍、疼痛、炎症性肠病的治疗,
莱姆病、皮肤病等
低剂量纳曲酮
最新研究如何
Linda Elsegood序言:
Phil Boyle 博士
编辑
第二卷
书
这
低密度脂蛋白
佛蒙特州怀特河交汇处
切尔西格林出版公司
英国伦敦
版权所有 © 2020 LDN 研究信托。
版权所有。
未经出版商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传播或复制本书的任何部分。
项目经理:Alexander Bullett
项目编辑:Michael Metivier
发展编辑:Natalie Wallace
文字编辑:Laura Jorstad
校对:黛安·杜瑞特 (Diane Durrett)
索引编制者:Linda Hallinger
设计师:Melissa Jacobson
页面布局:Abrah Griggs
在加拿大印刷。
2020 年 9 月首次印刷。10 9 8 7 6 5 4 3
2 1 20 21 22 23 24
我们对绿色出版的承诺Chelsea Green 将出版视为文
化变革和生态管理的工具。我们努力使我们的图书制造实践与我们的编辑使命保持一致,并减少我们的企业对环境的影响。我们在无氯再生纸上印刷我们的书籍和目录,尽可能使
用植物基油墨。这本书的价格可能略高,因为它是在含有再生纤维的纸张上印刷的,我们希望您会同意这是值得的。LDN书籍第 2 卷是在 Marquis 提供的纸张上印刷的,该纸张由
再生材料和其他受控来源制成。
美国国会图书馆出版编目数据名称:Elsegood,Linda,1956 年 ‑ 编辑。
标题:LDN 书籍。第 2 卷。关于低剂量纳曲酮如何彻底改变创伤后应激障碍、疼痛、炎症性肠病、莱姆病、皮肤病等治疗的最新研究/由 Linda Elsegood 编辑。
其他标题:关于低剂量纳曲酮如何彻底改变创伤后应激障碍、疼痛、炎症性肠病、莱姆病、皮肤病等疾病治疗的最新研究
描述:佛蒙特州怀特河交汇处:切尔西格林出版社,[2020] | 包括参考书目和索引。
标识符:LCCN 2020026302(印刷本)| LCCN 2020026303(电子书)| ISBN 9781603589901(平装本)| ISBN 9781603589918
(电子书)
主题:MESH:纳曲酮 治疗用途 | 纳曲酮 药理学 | 剂量‑反应关系,药物 | 麻醉药
拮抗剂 治疗用途 | 阿片肽 代谢分类:LCC RM328(印刷版)| LCC RM328(电
子书)| NLM QV 89 | DDC 615.1/9dc23 LC 记录可在https://lccn.loc.gov/2020026302上找到LC 电子书记录可在https://
lccn.loc.gov/2020026303上找到
切尔西格林出版公司
北大街 85 号,120 室
美国佛蒙特州怀特河交汇处
萨默塞特宫
英国伦敦
www.chelseagreen.com
献给我已故的母亲,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内容
前言:Phil Boyle 博士序言:
Linda Elsegood
第一章 LDN 的历史和药理
学作者:J. Stephen Dickson
第二章《慢性疼痛》作
者:Sarah J.
Zielsdorf 和 Neel D. Mehta
第三章 肠道健康作者:Leonard
B. Weinstock
和 Kristen Blasingame
第四章
Apple Bodemer 的皮肤病学
第五章
克尔斯滕·辛格勒 (Kirsten
Singler) 的《帕金森病》
第六章 儿科作者:Vivian
F. DeNise
第七章 女性健康作者:奥尔
加·L·科尔特斯
第八章 创伤性脑损伤作
者:Sarah J. Zielsdorf
第九章
Wiebke Pape 的《解离性障碍》
第十章
乌尔里希·拉尼乌斯 (Ulrich Lanius) 和盖琳·福
斯特 (Galyn Forster) 著《创伤后应激障碍》
第十一章
莱姆病和其他蜱传疾病作者:Darin Ingels
吉尔·科特尔
(Jill Cottel) 的结语
致谢
附录 给药方案
(Sarah J. Zielsdorf
著)
笔记
贡献者
前言
生育医生(或任何医生)是如何成为低剂量纳曲酮处方者的?至少对我来说,这完全是偶然。2002 年,
我姐夫被诊断出患有进行性多发性硬化症 (MS)。纽约神经病学家 Bernard Bihari 博士因发现 LDN
的免疫调节作用而为他开了 LDN,他的 MS 仅在几周后就稳定了下来。大约九个月后,我参加了在爱尔
兰戈尔韦举行的一次小型会议,由 MS 患者 Robert 主持,他对 LDN 治疗也有类似的“奇迹”反应。他
的证词令人震惊。他行动不便、极度疲劳、脑雾,病情逐渐恶化 直到他开始使用 LDN。他的故事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很高兴听到这种治疗对自身免疫有如此有效的效果。我决定,如果我有一位患有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不孕症患者,我会推荐 LDN。但首先,我需要了解更多有关这种有趣药物的信息。当
时,LDN 研究信托还不存在,在同行评审的出版物中也几乎找不到相关内容。
对我来说关键点是:
路易斯·巴斯德 (1822–1895)
在观察领域,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3至4.5毫克的推荐剂量不到许可剂量的十分之一,因此显然是安全的。
LDN 是一种获得许可的药物,50 毫克时安全且耐受性良好,并且在此剂量下使用时间
没有限制。
重要的是避免与阿片类药物、可待因或酒精混合使用。
睡眠障碍和生动的梦境是常见的副作用,但在使用后一到两周内就会消失。
一个月内,我接诊了一位新发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不孕症患者。她去看了一位风湿病专家,医生给
她推荐了甲氨蝶呤,因为她对非甾体抗炎药 (NSAID) 没有反应。甲氨蝶呤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服用甲
氨蝶呤时无法怀孕。我建议我们可以尝试 LDN,这可能会改善她的症状,同时仍允许她怀孕。我解释
说,这是标签外使用,虽然没有出版物支持这种治疗方法,但美国越来越多的临床观察结果令人鼓
舞。怀孕是她的首要任务,所以她同意尝试 LDN,因为它不太可能有害,如果 LDN 没有帮助,她总是
可以尝试常规治疗。她的反应令人惊叹。她的疲劳感大大减轻,关节疼痛和肿胀明显改善,她在开始治
疗后两个月内怀孕了。尽管她的反应令人难以置信,但她的神经科医生对 LDN 治疗的想法持反对态
度,拒绝接受或进一步探索。这令人惊讶和不安
大部头书。
自 2004 年以来,我的实践不断发展和变化,如今我为接受生育治疗的夫妇中超过 50% 的人开
具 LDN 处方,过去 10 年中约有 2,000 名患者。LDN 对我的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改善和更好的生育
结果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一个基于临床经验和接受治疗的患者的直接反馈而逐渐演变的过程。最
初,我阻止我的患者在怀孕期间服用 LDN,因为我不确定它的安全性,但现在我让他们继续服用到
37 周,并且看到母亲和婴儿的结果都得到了改善。
LDN 并非对所有不孕症患者都有益。我将其用于临床内啡肽缺乏症患者。当患者情绪低落、疲劳、
焦虑、睡眠障碍、经前综合症、痛经、子宫内膜异位症或自身免疫性疾病(内啡肽缺乏症的症状)时,他
们更有可能对 LDN 产生良好反应。当内啡肽水平正常时,LDN 可能会过度刺激并导致不愉快的副作
用
这种影响会持续超过典型的两周过渡期。
持续的副作用表明 LDN 会导致内啡肽分泌过量,阻碍而不是改善健康和幸福感。这些
副作用包括持续的逼真梦境、睡眠障碍、恶心、头痛和口干。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会尝试降
低 LDN 的剂量或完全停止使用。
与绝大多数已获许可的免疫调节疗法不同,LDN 不会抑制免疫系统及其许多重要功
能,从而减轻激活无症状结核病 (TB) 或引发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或癌症的可能性。
LDN 不会导致任何这些并发症。值得注意的是,LDN 通过刺激内啡肽的产生来平衡免
疫系统,内啡肽具有多种免疫调节作用,有助于控制多种自身免疫和炎症疾病。此外,
LDN 价格低廉,副作用或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很少。作为医生,我们的治疗指导原则
始终是“Primum non nocere” 首先,不要伤害。
LDN 是目前最安全的免疫调节治疗方法。
临床上我发现大约 70% 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对 LDN 有良好反应,而安慰剂只有 30% 的时间有效。患者避免食用
小麦和奶制品并补充维生素D3和 omega‑3 时反应更好。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并非每个人都会对 LDN 有反应。我见过
对 LDN 无反应的患者,他们绝对需要接受专科医生的免疫抑制治疗。当 LDN 治疗无效时,重要的是鼓励患者接受这
种可能性。
在当前循证医学和法医学的环境下,LDN 的标签外处方代表了一种有消失危险的医
疗治疗方法。医生们担心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法会伤害患者,这是理所当然的,诉讼是一个
非常现实的问题。然而,医学思维正变得过于狭隘、缺乏整体性和恐惧。许多医生认为,如
果它没有发表,我们就不应该冒险尝试它 除非是在严格的临床试验的背景下。这种方
法最终会导致对患者的护理质量下降,并阻碍新医疗治疗方法的发展。许多生育医生通
常使用糖尿病药物二甲双胍来治疗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
卵巢,并且经常改善患者的健康和生育结果。口服避孕药未获准用于治疗痛经,但这种标外使用被广
泛推荐。来曲唑获准用于帮助防止乳腺癌扩散,但被广泛用于刺激排卵。目前有 100 多种药物通常用
于与它们获准治疗的疾病完全不同的疾病。当医生在使用获准用于其他疾病的药物时发现一种疾病
有意外改善时,这些偶然发现有利于有准备的头脑。如果医生必须等待发表的研究才能开出合理的
标外用药,那么医学治疗的进展将非常缓慢。最重要的是医生要让患者知道一种治疗方法是新的还是
标外的,并让患者决定是否愿意尝试。我的大多数患者在充分了解情况后都很乐意尝试一种安全、新
颖和“实验性”的治疗方法。
许多医生喜欢循规蹈矩,只有当一大群其他医生推荐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时,他们才会建⽴信心。
然而,当一个负责任的医学意见团体支持医生的治疗策略时,即使其他医生采取不同的做法,Bolam
原则也能为医生提供法律保护。这让那些不敢第一个尝试新事物的医生感到安心。值得庆幸的是,许
多医生现在使用 LDN 作为免疫调节治疗。
这本 LDN 研究基金会出版的第二本书涵盖了具有多年成功临床经验的执业医生治疗的各种疾
病。他们的积极经验有望激励更多医生考虑为合适的患者使用 LDN。这本书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指
南,适合那些有兴趣学习如何使用最安全的免疫调节疗法正确治疗患者的医生。
菲尔·博伊尔博士
前言
2003 年 12 月,威尔士的全科医生鲍勃·劳伦斯医生给我开了低剂量的纳曲酮。我患有多发性硬化
症,当时病情迅速恶化。12 月 3 日,我开始服用 LDN,效果惊人。仅仅三周后,我长期身陷其中的可
怕迷雾终于消散了。我又能清晰思考,连贯地说话了。我 15 岁的女儿一直在喂我、给我穿衣服、给
我洗澡;现在,照顾我的角色又回到了自然的位置。到 2004 年圣诞节,我的肝功能测试恢复正常,我
又恢复了正常功能。LDN 让我重获新生。
在 LDN 取得成功后,我于 2004 年成⽴了 LDN 研究信托基金,这是一家英国注册的非营利性
慈善机构。LDN 研究信托基金完全由志愿者运营;我们不接受任何资金,而是依靠捐款。我们与处
方人员、药剂师和患者密切联系,提供支持和教育。我们的网站是www.ldnresearchtrust.org,包
含涉及 LDN 的临床试验和研究列表、LDN 的适用条件、全球 LDN 处方者和药剂师、处方者/患者
指南等。我们有自己的LDN 广播节目,听众可以在 Mixcloud、Apple Podcast、iTunes 和 Spotify
上收听。这些节目现在正在转录并与视频一起播放,您可以在我们的 Vimeo 和 YouTube 频道上
找到。我们制作了五部纪录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外,我们还安排大大小小的 LDN 会议,并与药
房联合举办研讨会。简而言之,LDN 研究信托基金致力于传播有关 LDN 的信息,并鼓励和支持对
该药物的持续研究。
《LDN 手册》第 1 卷涵盖了有关 LDN 的最新研究、试验和调查。其各章讨论了以下情况,这些情况
已证明 LDN 具有积极益处:
多发性硬化症和狼疮
炎症性肠病
慢性疲劳综合征和纤维肌痛
甲状腺疾病
不安腿综合征
沮丧
自闭症谱系障碍
癌症
自 2016 年《LDN 手册》第 1 卷出版以来,人们对 LDN 的认识呈指数级增长。有许多新的试验、研
究和论文探讨了其在治疗上述疾病以及其他许多疾病方面的用途。因此,本卷是第 1卷的后续,展示了新
信息,并为医疗专业人员和患有创伤性脑损伤、莱姆病、子宫内膜异位症、慢性疼痛等疾病的患者提供了
更多资源,
更多的。
《LDN 书》第 1 卷的读者会注意到,第 1章“LDN 的历史和药理学”已根据第一卷进行了更新和改
编。我们选择重新收录由 J. 撰写的这一章。
Stephen Dickson,因其对 LDN 的背景和机制进行了全面且通俗易懂的讨论。
LDN 研究基金会的实力不断增强。我们拥有出色的顾问,他们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还有出色的志愿者,
他们无偿奉献时间帮助他人。如果没有这些帮助,我们就无法开展我们的工作。非常感谢本书的所有作者
以及支持我们的所有人。
如果没有 LDN,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我对博士充满感激。
劳伦斯,感谢他给予我的所有支持,帮助我恢复生活:这是你能给予任何人的最
珍贵的礼物!
琳达·埃尔斯古德
LDN 研究信托创始人
‑一‑
历史和药理学
低密度脂蛋白
J. STEPHEN DICKSON,BSC(荣誉学士),MRPHARMS
纳曲酮属于阿片类拮抗剂,这是一类相对较新的药物,于 20 世纪 40 年代首次正式理论化。
拮抗剂(包括阿片类拮抗剂)可阻断其他药物以及天然存在的激素、儿茶酚胺、肽和神经递质的生理活
性。
最早被开发的拮抗剂是 1964 年詹姆斯·布莱克爵士发现的 β 受体阻滞剂。β 受体阻滞剂(如普
萘洛尔)是一种肾上腺素能阻断药物,用于控制人类的战斗或逃跑反应。普萘洛尔的发现被广泛誉为
20 世纪药理学最重要的贡献。
1
能够以临床相关的方式改变内源性生物机制对医学如此重要,以至于 1988 年决定授予布莱克爵
士诺贝尔医学奖,不仅因为他开发了拮抗剂,还因为他的后续工作,这些工作展示了如何阻断受体位点
(在这种情况下是肾上腺素受体)可用于治疗衰弱性疾病,包括高血压、心绞痛和心力衰竭。至今,β 受
体阻滞剂仍是治疗心脏病患者的主要手段,自开发以来,它在全球范围内防止了数百万人的死亡,使其
成为最有效的药物之一
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类药物。受体治疗疾病的潜力引起了科学界的兴奋,促使研究人员密切
关注阿片类止痛药实际上是如何与人体内阿片类受体相关的。
以罂粟(Papaver somniferum)为基础的止痛药已存在数千年,荷马的《奥德赛》 (约 3000 年前) 的文献中就有记
载:“她将一种药放入酒中,他们喝下这种药,以缓解所有痛苦和愤怒,忘记一切悲伤。”3尽管公元前300 年的泰奥弗拉斯
托斯和公元60 年的狄奥斯库里德斯都认为,这种酒实际上是天仙子植物的提取物,其中含有几种活性莨菪烷生物碱(特
别是东莨菪碱、莨菪碱和阿托品,后者将在本章后面讨论),但这一观点在现代已被驳斥,药理学家 Schmiedeberg
(1918) 和 Lewin (1931) 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据,证明《奥德赛》中海伦娜的饮料是由天仙子提取物制成的罂粟。
4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许多关于用罂粟制成的止痛药的记载。六千年前的苏美尔文献和两千
年前的埃及象形文字中都有类似的符号,指代“gil” ,翻译成现代语言,代表“快乐”,源
于“ hul gil”,而“hul gil ”的象形文字无疑是罂粟。
5
历史上有许多参考资料支持阿片类药物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大约公元前 1500 年的埃伯
斯纸莎草书推荐了一种特殊的药物来“防止儿童过度哭闹”,并附上了制作方法:“Spenn,
罂粟的谷粒,加上墙上发现的苍蝇的排泄物,过滤成浆状,通过筛子,连续四天服用。哭闹会
⽴即停止。”6
古希腊罗马人对鸦片的迷恋在许多历史记录中都有所体现。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 (公元
前 460 年)用草药进行了许多药物治疗,包括罂粟籽。7鸦片滥用在有记录的每个时期都很普
遍。值得注意的是,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雷利乌斯表现出许多鸦片成瘾的症状和副作用。8罗马
帝国的衰落始于公元500 年左右,随之而来的是许多贸易路线和广泛的知识
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罂粟似乎已经撤退到阿拉伯世界。
罂粟自古以来就在阿拉伯世界持续种植。种植记录通常指向现在的伊拉克,即以前的苏美尔,有充
分证据表明,后罗马帝国时期的罂粟及其提取物贸易网络于公元800 年开往印度和中国,到公元1500
年则传播到现在的欧洲。9鸦片作为一种消遣性药物(最常见的是吸食)的传播,通常归因于公元500
年至公元1000 年阿拉伯影响的迅猛增长和推进。随着伊斯兰教的建⽴和兴起,由于《古兰经》禁止饮
酒,阿拉伯人民普遍使用鸦片和大麻来消遣。10从公元1500 年起,在历史记录中开始更频繁地出现提
到广泛使用鸦片(包括药用和消遣)的手稿。11帕拉塞尔苏斯是一位瑞士医生,常被誉为现代医学之
父,他首次将鸦片罂粟的酒精提取物(称为鸦片酊)标准化, 1527.12这种标准化鸦片酊一直使用到
现代,第一种品牌鸦片酊早在 1680 年就出现在英国。13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纳曲酮的发展非常重要的
是,鸦片提取物的使用通常会导致上瘾以及因过量服用而死亡。外科医生经常使用阿片类药物提取物
来缓解疼痛或进行手术,但由于药物中阿片类药物的强度不可预测,手术中因过量服用而死亡的情况
经常发生。直到现代,使用催眠海绵(一种浸泡在鸦片中的海绵,在手术期间局部使用,被认为是大剂
量口服鸦片的更安全替代品)很常见,但由于吸收不足而经常无效,或者效果太强,导致并发症。14
直到格鲁吉亚时期(1714‑1830 年),现代化学科学才发展到足以进行分馏以及活性成分的提
取和鉴定。1806 年,德国药剂师弗里德里希·塞特纳首次从一种名为罂粟碱的提取物中分离出鸦片的
活性成分,并将其命名为吗啡,以希腊神话中的梦之神莫菲斯命名。15吗啡属于一类被称为生物碱的物
质。瑞士植物学家卡尔·迈斯纳于 1819 年首次使用生物碱一词,当时他指的是一种名为 al‑qali 的植
物。
16
碳酸钠最早是从这种植物中提取出来的,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al‑kali 。该术语后来被用来
指代化学物质的 pH 值,因此,生物碱呈弱碱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发现一种可以提取和纯化的天然活性成分引起了科学界的极大兴奋。但在当时,受
体科学尚不存在,对当时的科学家来说,了解药物的作用原理并不比生产出更强效、副作
用更少的药物更重要。
吗啡在 19 世纪上半叶继续被提取和广泛使用。此外,在法国生理学家 Claude
Bernard 推广使用吗啡作为麻醉氯仿的辅助剂后,吗啡在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广泛使
用。17 Bernard 的动物实验通过经验证明,在动物麻醉前注射吗啡,需要的氯仿更少。
18然而,在接下来的 50 年里,医生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吗啡有几个缺点,包括呼吸
抑制、便秘、成瘾,甚至过量服用导致死亡。随着吗啡的问题越来越广为人知和理解,人们
开始积极寻找更安全的替代品。
英国科学家查尔斯·罗姆利·阿尔德·赖特于 1874 年首次合成二乙酰吗啡,即通过化
学方法在吗啡分子上添加两个乙酰基,现在俗称二乙酰吗啡,滥用时则称为海洛因。19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人们制造出了许多原始吗啡的化学类似物,每一种都被称为没有
副作用或缺点的“新吗啡”。这些新化合物都被发现没有副作用,现在人们知道吗啡类
似物的有益作用与通过相同受体产生的副作用直接相关。
研究仍在继续,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1918) 期间,由于贸易中断,许多发达国
家发现很难获得吗啡。吗啡供应的减少加剧了科学界对合成该药物方法的探索。在整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清楚地记得上一次战争期间获得吗啡的困难,但此时另一种
化学物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阿托品。
阿托品是从颠茄植物(Atropa belladonna)中提取的,颠茄是一种多年生植物,原产
于欧洲和西亚部分地区。从历史上看,它在中世纪被用来增大女性的瞳孔,因此得名(bella:
美丽, donna:女人),但后来事实证明它有更重要的用途。在战争时期,阿托品是医务人
员用来抵抗神经毒气袭击的唯一抗胆碱能药物。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阿托品将对任何军队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因此战争双方都投入了大量资源来寻找植物衍生阿托品的替代品。
正是通过这种艰苦的科学努力,德国科学家 Dr.
1939 年,奥托·艾斯莱布 (Otto Eisleb) 首次合成了一种他称之为哌替啶的分子。
哌替啶未能成功取代阿托品,但很快被奥托·舒曼博士(当时就职于德国化学公司 IG
Farben)认可为一种强效镇痛药,作用类似于吗啡。20哌替啶,也称为哌替啶,至今仍在分娩
时使用。
哌替啶是第一种化学结构与吗啡完全不同的阿片类药物(见图1.1)。
现在,化学合成新药化合物的大门已经真正打开,科学实验室正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下一个最广为人知的非
吗啡类阿片是 1,1‑二苯基‑1(二甲氨基异丙基)丁酮‑2,现在通常称为美沙酮,在短短几年后(1940 年至 1946
年)合成。21在默克公司的研究实验室工作中,两位科学家 Weijlard 和 Erickson 合成了一种让所有人都困惑
的化合物。22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化合物似乎发挥与吗啡相反的作用,逆转后者的负面影响。他们将这种化合物
称为纳洛啡(化学名称为 N‑烯丙基去甲吗啡)。韦拉德和埃里克森发现,这种化合物实际上具有混合作用:它对
动物有轻微的镇
痛作用,有点像吗啡,但当给预先用过量吗啡治疗过的动物服用时,吗啡的作用(如呼吸抑制)就会逆转。这
一发现有点令人困惑,因为医学界当时还不了解受体的概念。
图 1.1.吗啡的结构。
图 1.2.哌替啶的结构。
然而,许多实验室和公司不受这种化合物令人困惑的作用的困扰,并认识到一
种能够完全阻断吗啡负面影响的药物将非常有用,因此继续合成不同的分子。
1963 年,英国申请了第一个纯吗啡阻断药物的专利,1966 年,美国申请了专利。
23发现的化合物是纳洛酮。
纳洛酮是治疗阿片类药物过量的一种灵丹妙药。静脉注射后,它似乎能⽴即
阻断吗啡的所有作用。更多
50 多年后,纳洛酮仍然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基本药物清单上。24对低剂量纳曲酮 (LDN) 的背景而言更重要的
是,纳洛酮的发现促使其他研究人员在 1967 年发现一种可
以口服的类似物,名为 Endo 1639A。25 Endo 1639A 现在通常称为纳曲酮。
纳曲酮的历史使用
阿片类药物成瘾长期以来都是社会问题。人们对阿片类药物成瘾的原因有很多:它们可以麻痹身体和心理上的痛
苦;长期使用会导致生物变化,导致停药时出现副作用;它们会产生药物耐受性,需要更大的剂量才能产生类似的
效果。
为了理解纳曲酮分子的重要性,了解阿片类药物作用的一些潜在生物学机制非常重要。阿片类药物以及具有
相同效果但结构不同的阿片类药物(例如上述的哌替啶)模仿天然神经肽。这些天然神经肽被称为内啡肽,在阿
片类镇痛作用的情况下,具体称为β‑内啡肽。它们是在脑垂体前叶合成的,并在对各种刺激作出反应时释放。
大多数内啡肽的前体蛋白是阿片黑素皮质素原 (POMC)。在正常的生理功能中,下丘脑会分泌促皮质素释放
激素 (CRH) 来应对生理系统的压力。这反过来又刺激垂体产生 POMC,作为一种大型复合分子,POMC 可以通
过酶分解成神经肽,例如内啡肽。然后发生负反馈回路,当 POMC 分解的副产物达到一定水平时,它会抑制 CRH
的释放。几乎身体的每个生理系统都含有将 POMC 分解为组成神经肽所需的酶。
在讨论内啡肽如何发挥作用时,最简单的方法可能是关注其止痛(镇痛)特性。这些特性通常很好
了解并有可靠的科学文献。它们可能具有更复杂的生物学作用,但了解得较少,但这将在后面讨论。
镇痛的主要作用领域有两个,天然内源性神经肽,如β‑内啡肽,可以发挥止痛作用:第一,周围神经
系统(PNS);第二,中枢神经系统(CNS)。
可以将 PNS 比喻为连接人体各个部位(从传感器到大脑)的电线。这些电线通过接头连接在一
起。然而,与电线相互接触的电气系统不同,神经接头通过释放化学物质相互交流。这些化学物质称为
神经递质。
神经可以描述为从突触后末端开始,接收来自前一个神经的信息,并以突触前末端结束,与下一个神经
进行通信。传递疼痛感觉的神经通过释放一种名为 P 物质的神经递质来实现这一点。
在周围神经系统(PNS)中,阿片类药物主要与突触前末梢结合,通过级联反应阻止P物质的释放,如果
P物质不能释放到神经接头处,疼痛信号就无法传递。
从图表上看,这很难以简单的方式表示。
然而,回到简化的大学讲义,反应可以如图 1.3 所示表示。
在图 1.3中,我们可以看到疼痛信号的传递是如何被自然产生的内啡肽所阻断的,内啡肽作用于阿
片受体,以与阿片类药物类似的方式抑制疼痛。这样,来自外周感知系统的疼痛信号在传回大脑时就不
会太强烈,甚至根本无法传到大脑。
该系统远比这里所介绍的要复杂得多;有一系列称为速激肽的神经递质,其作用方式与 P 物质相
似,还有几种不同类型的阿片类受体,每种受体的作用略有不同,并且都参与了化学级联,将疼痛完全
传递到 PNS 中的不同神经纤维。然而,一种称为 mu 受体的阿片类受体子类在 PNS 中无处不在,是
阿片类止痛药的主要靶点。
在中枢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中,阿片类受体分布非常广泛,参与多种不同的神经化学作用。与周
围神经系统不同,阿片类受体通过改变强效神经递质多巴胺的释放来集中抑制疼痛。
多巴胺通常被称为人体天然的“快乐化学物质”,主要受另一种神经递质 γ‑氨基丁酸 (GABA) 的
释放控制。当阿片类药物与 μ‑阿片受体结合时,它们会导致 GABA 释放减少,从而降低 GABA 激活对
突触前神经释放多巴胺的抑制作用。
通俗地说,激活 μ‑阿片类受体会中枢干扰对多巴胺基线释放的正常控制,这意味着释放的多巴胺
比正常情况多得多。这通过抑制疼痛信息的传导和对过量多巴胺的欣快作用引起的疼痛的反应而产生
镇痛作用。过量的多巴胺是滥用阿片类药物的人渴望的“兴奋”的主要原因,但它完全属于一种自然系
统,该系统的存在是为了维持体内平衡,并由自然产生的内啡肽激活,如前所述。
图 1.3.内啡肽中断了疼痛信号的传递。
显示此工作过程的图表将有助于使此过程更加清晰。
图1.4左侧描绘的是正常的体内平衡。右侧,海洛因(二乙酰吗啡)分解为吗啡,然后附着于 μ‑阿片
受体,抑制 GABA 释放,增加多巴胺释放。
这些神经上的 μ‑阿片类受体被生物内啡肽激活。
受体是现代医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尽管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就已广泛提出了理论,但第一个阿片受体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放射性
同位素标记技术问世后才被发现的。26有趣的是,被广泛认为是第一个描述和鉴定阿片受体的科学家
是使用纳洛酮来实现的,如前所述,这直接导致了纳曲酮的开发。
图 1.4。左图为 GABA 和 μ‑阿片受体的正常功能。右图为海洛因对 GABA 和 μ‑阿片受体的影响。
此后人们发现,许多受体的性质相似,事实上,阿片类受体属于 G 蛋白偶联受体家族,
这些受体在激活时通常都具有抑制作用。从结构上讲,阿片类受体类似于生长抑素受体
和另一类受体(稍后讨论),称为 Toll 样受体 (TLR),它们参与炎症过程。27
回到阿片类受体,科学家很快发现许多不同的化学物质可以与它们结合。虽然有些化
学物质可以与受体结合,并通过放射学研究观察到它们附着在这些受体上,但它们并不
都具有相同的效果。事实上,观察到的活动范围很广,从受体的极度激活到轻微激活,直至
阻止任何其他物质附着在受体上。
在药理学中,产生这些作用的化学物质分别称为激动剂、部分激动剂和拮抗剂。
传统上,受体被认为是锁。想象一把标准的门锁,不同的钥匙可以插入同一个钥匙孔。
激动剂是适合锁并完全打开门的钥匙(受体的极度激活);部分激动剂适合锁但只能部
分打开门(轻微
激活);而对抗者虽然安装了锁,但打不开门,而是主动阻止任何其他钥匙试图打开门
(阻断)。
图 1.5显示,虽然锁(受体)和钥匙(配体)的类比很容易理解,但受体位点的实际结
构是三维的,并且受体的不同部分可以根据与其相互作用的配体的物理结构被激活或阻
断。内源性内啡肽,例如前面讨论过的 β‑内啡肽,是激动剂;它们被阿片类药物(例如吗
啡和二乙酰吗啡)模仿。纳曲酮和纳洛酮是拮抗剂:钥匙可以打开同一扇门,但可以阻止受
体被激动剂激活。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受体是流动的,对激动剂的敏感度可以增加或减
少,并且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减少活性数量。
基于这一认识,纳曲酮于 1984 年首次获批用于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28科学家们了
解到,阻断阿片类药物受体将阻止成瘾患者获得服用海洛因等药物所获得的快感。因此,
纳曲酮非常有效;当对高剂量阿片类药物成瘾的患者服用纳曲酮时,阿片类药物的所有作
用都会⽴即被阻断数小时。然而,这种疗效被证明是非常危险的,导致大量对阿片类药物
有耐受性的患者死亡,因此在不知不觉中被迫⽴即戒除阿片类药物。
然而,有几个问题导致纳曲酮未能成为阿片类药物成瘾治疗的主要药物。首先,尽管该药
物有效地阻断了阿片类药物,但患者对阿片类药物欣快感的潜在心理依赖并没有减少。
事实上,据报道,在纳曲酮治疗期间,患者的渴望会更强烈。
这是一种可逆反应,纳曲酮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被广泛用于帮助戒除阿片类药
物,但只有在患者逐渐从常规剂量减少剂量并恢复体内平衡水平后才会使用。纳曲酮以片剂
形式口服,每日剂量从 50 毫克 (mg) 到 300 毫克不等。阿片类受体阻断作用强且可预测;如
果患者在服用纳曲酮的同时服用任何阿片类药物,则不会产生欣快感。
尝试使用拮抗剂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的问题在于,当一个人成为阿片类药物的常规使用
者时,受体对阿片类药物(包括天然内啡肽)的反应性会大大降低,受体的物理数量也会减
少。这是一种自然的生物现象,由生理学总是试图回到基线状态(体内平衡)引起。在药理学
中,这种效应被称为脱敏和下调。
其次,服用纳曲酮的患者接受阿片类药物阻断后,体内自然产生的内啡肽会减弱,而内啡
肽是维持基本体内平衡所必需的。当大脑对愉悦刺激作出反应时,这种反应是由内啡肽介导
的,因此当完全阻断阿片类药物时,大脑
二月
图 1.5.脑啡肽受体位点。改编自 Fred Senese 的《花生四烯乙醇胺》,《General Chemistry Online!》,最新修订版 2018 年, http://
antoine.frostburg.edu/chem/senese/101/features/anandamide.shtml。 23,
理论上,它会干扰患者感受或体验幸福和愉悦的能力。服用纳曲酮的阿片类药物成瘾患者经常会
描述一种“平淡无味”,技术上称之为烦躁不安,据报道,这会导致严重的抑郁。纳曲酮和烦躁不
安之间的联系已被研究,但结果相互矛盾,尽管烦躁不安仍然被列在产品特性摘要中作为副作用。
研究表明,抑郁症的初始症状可能会改善,临床报告的副作用与停用阿片类药物或伴随疾病有关。
29
最后,由于生活节奏混乱,或上述副作用(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心身的),治疗依从性通常很差;
患者通常不会每天服用药物,因此很容易重新上瘾。许多制药公司试图通过开发缓释注射剂来避
免这个问题,其中一些至今仍在市场上销售,但由于给药的复杂性、注射剂的价格以及国际上普遍
采用以证据为基础的替代和缓慢减量疗法(如美沙酮),这种药物的接受度一直很低。
在纳曲酮用于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期间,它在另一个领域也获得了青睐:酒精中毒。临床医生
推测,如果患者在过量饮酒时服用纳曲酮,就像酒精中毒的情况一样,他们的大脑可以通过与上述
相同的过程重新训练,不再从酒精中获得快感,从而阻止内啡肽的作用。
当医生在患者身上尝试这种疗法时,他们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纳曲酮在过去 25 年里一直作为
减少酒精依赖患者酗酒的治疗方法而受到广泛欢迎。2006 年的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70% 的该
领域临床试验都证明了其具有重要的临床益处。
20 世纪 90 年代末,约翰·大卫·辛克莱 (John David Sinclair) 在芬兰国家健康与福利研究
所工作时,为广泛使用纳曲酮治疗酒精中毒制定了基本的科学基础和标准化。他证明了一种被描
述为药物消退的过程,表明在服用纳曲酮的同时饮酒可以逐渐减少对酒精的渴望。从统计学上讲,
这遵循一条消退曲线,这是可重复和可预测的。这
这种方法被命名为辛克莱方法,如今已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辛克莱的开创性工
作最近使纳曲酮类似物纳美芬正式获得许可,可用于治疗酒精依赖患者。
免疫学效应
纳曲酮因其阿片类受体和内啡肽调节特性,长期以来一直被安全用于患者。在过
去的二十年里,人们认识到纳曲酮还具有免疫学作用,据报道,纳曲酮对自身免疫
性疾病有益。此外,临床医生报告称,纳曲酮可用于治疗各种类型的癌症。这让很
多人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种具有明确和可理解的药理作用的药物怎么会有
如此广泛的其他可能适应症?
制药公司在获得许可之前会竭尽全力修改其产品,以确保活性分子尽可能选
择性地针对目标。然而,尽管这些公司尽了最大努力,但目前市场上大多数获得许
可的药物都无法 100% 选择性地针对目标。
许多生物活性化学物质会与人体的多个部位相互作用。药理学术语称之为“脏
药”,即尽管药物确实发挥了其声称的功效,但还会产生其他作用。这些作用被解
释为“副作用”,因为副作用通常是不受欢迎的。
在过去的 55 年里,随着对生物手性的理解急剧增加,对受体结构的理解也得
到了极大的改善。手性意味着受体和其他靶细胞区域通常是三维结构,可以是“左
手”或“右手”。尽管具有相同的细胞构件,但它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
起,就像我们的手有相同数量的骨头和肌腱,但彼此相反。
这一概念延伸到生理系统的分子水平,并被发现在药物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为药物也可以有左手或右手的设计。
从化学角度来看,这种“手性”被描述为 L 或 R 异构体。
毫不奇怪,药理学家现在了解到,每种不同的异构体实际上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并且每种异构体
的生物可利用药物量可能与剂量有关。然而,大多数药物在合成时,最终产品中 L 和 R 异构体的比例是
一致的。
图 1.6表明药物分子对人体的实际影响尚未完全了解,许多以前被认为可以很好解释的分子在仔
细检查其固有结构或给药方案后被发现具有不同的效果。如前所述,改变体内平衡的药物也有可能以
不同的方式改变这些固有的生物系统,这取决于它们在改变自然控制机制方面的有效性。
就纳曲酮而言,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有效的剂量明显低于(低 10 到 40 倍)用于治疗阿片类药物成
瘾或酒精中毒的剂量。这被称为低剂量纳曲酮 (LDN)。最常见的是,LDN 的每日服用剂量在 0.5 毫克至
4.5 毫克之间。
图 1.6。手性演示。图片由 NASA 提供。
不应将 LDN 与顺势疗法相混淆,顺势疗法中活性物质被神秘地稀释了这么多
倍,以至于最终产品中几乎没有原始化学分子。即使在 0.5 毫克至 4.5 毫克的低剂
量下,纳曲酮仍然具有显著的生物利用度,并可⽴即引发短期阿片类药物戒断。也就
是说,尽管剂量比该药物历史上获准的剂量低很多,但临床医生仍然可以证明该药
物在此剂量下的一些众所周知的效应。在这些剂量范围内,它仍然具有生物活性。
关于 LDN 可能如何影响免疫系统的首批线索之一来自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
对内啡肽影响的研究。1985 年发表的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得出结论:“内啡肽可
被视为免疫调节剂,并可能成为免疫治疗领域的一种工具。”30当时人们已经知道
纳曲酮能够与内啡肽受体结合,因为内啡肽是内源性阿片类⋯药物。人们还知道,通
过阻断这些受体来破坏体内平衡可能会导致身体产生更多的内啡肽来补偿。31第
一位记录 LDN 免疫学影响的临床医生是 Dr.
1985 年,伯纳德·比哈里在纽约工作。他卷入了
当时正值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的中期,现代治疗方法尚未开发出来。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是一种导致免疫系统破坏和减弱的感染;当患者免疫功能低下时,他们就被称为患有
艾滋病,这是感染的最后阶段,他们通常会死于免疫系统损伤的并发症。比哈里的诊所为这
群病人尝试了一切方法来提高存活率。
之前进行的研究表明,内啡肽在免疫系统的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尝试用 LDN 治疗是
一个巧妙的举措。32首先,Bihari 博士对一小群病情非常严重的艾滋病患者进行了测试,他
们的内啡肽水平约为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
他的诊所认为,这种内啡肽缺乏症可以用小剂量的纳曲酮治疗,因此他们开始了为期 12 周
的试验。在安慰剂组中,16 名患者中有 5 名出现了机会性感染,但 LDN 组的 22 名患者中无
一人出现机会性感染。这些结果虽然规模较小,但却非常令人鼓舞。Bihari 的诊所随后开始
研究治疗更多 LDN 患者。33
Bihari 博士在一个相当规模的 HIV/AIDS 患者群体中证明,定期服用 LDN 在很大程度
上防止了免疫系统的逐渐破坏。他通过测量血液中一种名为 CD4 的免疫细胞的存在来做到
这一点。CD4 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观察 HIV 进展速度的标准标记。在他的实践中最有趣和最
引人注目的是,与不定期服用 LDN 的患者组相比,服用 LDN 的患者组的死亡人数要低得
多。它的成功似乎也与治疗期间出现的新型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产生了协同作用,这意味着无
论患者是否服用新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LDN 都能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34在接下来的几
年里,大量研究了内啡肽和阿片类药物/阿片类拮抗剂对调节免疫系统的重要性。其中最重
要的发现之一发表于 1986 年,由 Drs 发表。 Zagon 和 McLaughlin 证明阿片类受体存
在于多种类型的免疫细胞中,并且
横向研究发现,这些细胞内的信使 RNA (mRNA) 编码了内啡肽受体。35在接下来的 29 年里,Ian
Zagon 博士倡导了内啡肽和
LDN 的基础研究,发表了近 300 篇有关该主题的论文。研究范围太广,无法在此介绍;然而,它毫无
疑问地证实了内啡肽/阿片类受体系统参与了几乎所有调节免疫反应的生物系统。
这些研究提出的 LDN 作用机制可以
总结如下:
1. 许多外在疾病都是免疫系统功能失调的表现。
2. 免疫系统受内啡肽调节,内啡肽具有
主要作用于阿片受体。
3. 使用纳曲酮短暂阻断阿片类受体会导致
内啡肽的产生上调,可以通过免疫调节的方式纠正免疫系统功能障碍。
4. 此外,细胞生长(增殖)也由一种亚型内啡肽介导;细胞增殖可以被内啡肽抑制,这适
用于某些形式的癌症。
三十六
当然,这只是对 30 年详细工作的粗略简化,要完全理解已发表论文中的概念,需要获得免疫学学位
并投入大量时间。然而,多发性硬化症、伤口愈合、胰腺癌、结肠癌、脑癌、头颈癌、肝癌、乳腺癌和卵巢癌、
眼表疾病、克罗恩病以及许多其他途径的实验模型已被证明对体外内啡肽有反应。似乎对内啡肽系统
改变有反应的疾病范围之广令人震惊,其中最突出的是晚期癌症和多发性硬化症等使人衰弱的自身免
疫性疾病。
在过去的 30 年里,LDN 的临床应用一直在增加。
然而,目前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内啡肽并不是全部。科学家早就知道,纳曲酮不仅与阿片类受体结合,还与
一组称为 Toll 样受体的受体有显著联系。
41
40
当细菌或病毒等异物入侵时,不同亚类的 TLR 受体(人类的 TLR‑1 至 TLR‑10)会对入侵生物体的不同部
分作出反应,包括表面蛋白、细菌/病毒细胞代谢的副产物、细菌细胞表面或内部的物理结构、DNA、RNA,甚至某
些细菌独有的特定糖。这并不是一份详尽的清单,因为研究至今仍在继续。例如,已知有一类 TLR 受体(TLR‑10)
存在,但目前尚不清楚其底物。
这些受体的作用似乎是识别入侵者(它们具有与此互补的结构),然后启动触发适当免疫反应的细胞间信
号通路。
Toll 样受体于 1985 年由 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 首次发现。37它们是先天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抵御微生物入侵提供第一道防线,存在于白细胞 (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中性粒细胞、B 淋巴细胞、肥
大细胞和单核细胞等细胞上,也直接存在于肾脏和肠道等各种人体器官的细胞上。
和所有生物系统一样,TLR 似乎有多种激活方式。如前所述,纳曲酮是 TLR 通路的强效拮抗剂。
一般来说,TLR 的激活会导致促炎细胞因子(一类松散的小蛋白)的产生,然后这些细胞因子会调动先天
免疫系统,例如,将白细胞送到受影响的区域吞噬入侵者 或者在病毒的情况下,指示受感染的细胞死亡。有趣
的是,许多类型的 TLR 的激活已被证明还会产生一种名为核因子 κB (NF‑kB)(发音为enn‑eff‑kappa‑bee)
的强效分子,作为信号传导机制的一部分。38 NF‑kB 目前正在接受深入研究,并已被证明是治疗自身免疫性疾
病和癌症的有力靶点。39 NF‑kB 甚至与癌症致癌基因的表达有关,癌症致癌基因会关闭自然细胞死亡机制,导
致癌症不受控制地生长。
研究表明,该途径在体内具有临床相关性,纳曲酮可以抑
制 TLR‑4 并逆转神经性疼痛的症状,体外研究也表明
抑制 TLR‑7、8 和 9 可改善自身炎症疾病模型。42最近的一篇专门讨论神经性疼痛的论文是首批证明纳曲酮作
用具有手性的
论文之一。回到之前的讨论,左旋和右旋分子可以有不同的结合位点,Hutchinson 及其同事在 2008 年进
行的一项研究有效地证明了阿片类药物结合受体被左旋纳曲酮拮抗,而 TLR‑4 受体被右旋纳曲酮拮抗。43 此
外,2017 年,Cant、Dalgleish 和 Allen 在纳曲酮的外消旋混合物中发现了 TLR‑7、8 和 9 的拮抗作用。44
纳曲酮之所以在不同的生理系统中具有如此广泛的活性,完全有可能,事实上很有可能是因为它的行为方式
类似于两种不同的药物,具体取决于异构体的结构。
临床医生和科学家推测,在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多发性硬化症)中,天然哺乳
动物细胞副产物可能会不适当地激活 TLR 受体,直接导致不当炎症。45此外,最近在临床上用于治疗皮肤癌的
药物咪喹莫特已被证明可以激活而不是拮抗 TLR‑7,从而引起该区域大量炎症,因此它可非常有效地杀死皮肤
基底细胞癌。46总结迄今为止的数据:
当生产用于人类消费时,纳曲酮由左旋和右旋异构体以 50:50 的比例混合而成。
左旋纳曲酮是阿片类/内啡肽受体的拮抗剂,具有以下作用: – 增加内啡肽释放 –
免疫调节 – 通过内啡肽减少细胞增殖右旋纳
曲酮是至少一种 TLR 的拮抗剂,甚至多种,据报道具
有以下作用:
– 拮抗 TLR,抑制细胞因子调节的免疫系统
– 拮抗 TLR 介导的 NF‑kB 产生,减少炎症,并可能下调致癌基因
这样,很容易看出 LDN 的大量作用是可行的。目前缺乏足够的体内双盲临床
研究,以证明在培养皿和试管中证实的效果可以可靠地扩展到对人类的作用。
结论纳曲酮在改善
和治疗人类疾病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国际上对 LDN 在免疫、自身免疫和肿瘤疾
病方面的相对较新的用途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偶尔也用于治疗各种看似不相关的
疾病。当标准疗法无效时,临床医生有充分的理由考虑使用 LDN 作为标准疗法的
辅助手段。截至 2020 年,有几项临床试验正在设计或进行中,并且很有可能在五
年内获得 LDN 的许可。在此之前,患者和临床医生应在考虑治疗之前,通过查看
目前可用的证据(包括已发表的和轶事的)来做出最适合他们的明智决定。
注意:标准
剂量和低剂量的纳曲酮通常都是非法制造的,制造质量不合格,并在互联网上销
售。没有信誉良好的药房会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纳曲酮。任何试图寻找 LDN
处方者或供应商的患者都应参考信誉良好的来源。
英国唯一一家致力于推动 LDN 研究、并与国际资源、处方人员和供应商有广泛联
系的慈善机构是 LDN 研究信托基金会。
SARAH J. ZIELSDORF 医学博士、理科硕士和 NEEL D. MEHTA 医学博士
最
腰骶部和颈部疼痛是国际上主要的原因。
在量化残疾寿命(最常用的指标是 DALY,即伤残调整生命年)时,研究人员发现
多项流行病学研究,包括《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6 年)已证实,慢性疼痛和
疼痛相关疾病是全球致残和疾病负担的主要原因。这些慢性疾病中最常见的一
种是复发性紧张型头痛,影响着 19 亿人。这种痛苦的患病率只会增
加,因为全球每年有十分之一的人患有慢性疼痛。
此外,其他慢性疼痛疾病也位列十大致残原因之列。
据估计,慢性疼痛的患病率在世界人口的 10% 到 50% 之间。这种差异是由
于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特定地区内的患病率存在差异造成的。全球慢性
疼痛负担分布不均 中低收入国家比高收入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大,社会经济水
平最低和最年长的人群也是如此。这些人群承受着最严重的持续性疼痛负担,治
疗选择也较少。3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疼痛学会和全球健康界在 2004 年得出结
论:“全世界都认为,不治疗疼痛是一种糟糕的
慢性疼痛
‑二‑
2
1
医学、不道德的实践和对基本人权的废除。”4此外,慢性疼痛被视为健康危机,因为它在
不同人
群中普遍存在,并且对身体和情感生活质量都有影响。慢性疼痛的流行病学研究通过
对持续时间和疾病状态的不一致分类放大了其复杂性。国际疼痛研究协会 (IASP) 将这
种多维状况定义为持续六个月以上的疼痛。关于慢性疼痛在症状学(例如焦虑、抑郁、易
怒)或程度方面的定义是否合适存在争议。慢性疼痛的另一种分类是,它是一种与持续的
中枢或周围神经系统变化有关的疾病状态或损伤,从而导致敏感化。敏感的神经导致疼
痛反应的幅度(强度)和频率(持续时间)增加。5
在一项巴西人口研究中,近 50% 的参与者对慢性疼痛管理不满意。此外,在巴西,与
世界上许多治疗模式一样,治疗并不针对性别。然而,在疼痛强度的感知和疼痛对日常生
活活动的干扰方面,发现了显著的性别相关差异。女性表示疼痛危机的频率和持续时间都
比男性高,而且疼痛在自我护理、工作、性生活和睡眠中断等方面的干扰也更大。6
低剂量纳曲酮 (LDN) 代表了一种与慢性疼痛标准治疗完全不同的治疗策略。对抗疗
法、自然疗法和相关健康行业都存在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态度。对纳曲酮的下意识反应是
“这是用来治疗瘾君子的。”显然,在教育临床医生对酒精或阿片类药物依赖(或过量
服用)患者更加敏感,并了解纳曲酮和纳洛酮的治疗益处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几乎普
遍来说,很少有人意识到,如果我们使用低剂量的纳曲酮,我们可以通过短暂的阿片类受
体阻滞来缓解疼痛。在这里,我们将回顾目前支持使用 LDN 治疗神经病变、复杂区域疼
痛综合征、骨关节炎、自身免疫和
风湿病、多发性硬化症、肌筋膜疼痛、纤维肌痛和腹痛。
慢性疼痛管理的一般考虑临床经验表明,在没有阿片类药物的情况下,使用 LDN 可与其他抗炎药物产生协同作用,
包括非甾体抗炎药 (NSAID;应谨慎使
用)、局部止痛化合物、治疗性 omega‑3 脂肪酸补充剂、镁(尤其是口服甘氨酸盐或苹果酸盐,以及局部氯化镁制剂)、
姜黄素、白藜芦醇、谷胱甘肽、山金车和许多其他草药化合物(有关将 LDN 与阿片类药物一起使用的 ULDN 注意事项,
请参阅附录)。就像水桶旅可以灭火一样,这些化合物可以多方协作以减少全身炎症。在过去几年中,许多 LDN 临床医
生和研究人员对大麻二酚 (CBD) 产生了兴趣,它是另一种通过调节内源性大麻素和内啡肽通路与 LDN 产生协同作用
的化合物。
对于所有炎症情况,需要注意的是:任何治疗计划的基础都应该是寡抗原(消除)
和抗炎饮食,强调未加工食品、绿色和非淀粉类蔬菜、低血糖水果、野生捕获的鱼和橄
榄油,同时最常见的是消除谷物、乳制品、糖,有时还包括茄属植物种子和香料。存在各
种抗炎饮食方案,但最重要的是患者与临床医生合作,个性化他们自己的最佳饮食,强
调营养密度,而不是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开始限制性饮食计划,原因如下所述。
由于限制饮食疗法在治疗慢性病方面越来越受欢迎,新的研究令人担忧。许多临
床医生,包括 Dr.
Zielsdorf 等研究人员发现,长期(通常是几年)限制饮食的患者口服耐受性会下降。
我们的胃肠道不断受到潜在威胁的攻击,一般来说,口服耐受性这个术语代表身体识
别先前摄入的抗原的能力。
口服耐受性丧失有多种可能的原因。限制性饮食会导致微生物多样性下降。如果同时存在机会
性或致病性细菌、酵母、原生动物甚至寄生虫感染造成的不平衡,那么个体对食物蛋白质的耐受性
可能会降低。7口服耐受性丧失和随后的食物敏感的另一个原因似乎是树突状细胞过度活跃。这些
细胞被称为抗原呈递细胞 (APC),它们会对小肠腔内正在分解的蛋白质进行取样。APC 是诱导口
服耐受性所必需的,并有助于
产生调节性 T 细胞 (Treg),后者充当免疫系统的警察。它们的目的是维持和平 在识别良性或
潜在危险抗原时保持平衡。
然而,当树突状细胞受到过度刺激时,它们更有可能不适当地激活我们的免疫系统,从而可能将自
身蛋白质视为外来入侵者,并增加自身免疫的风险。我们可以通过改善蛋白质的消化(有时解决
胃酸和其他消化酶不足的问题)以及改善肠道的第一反应者(称为分泌性 IgA (sIgA) 的抗体)来帮
助这些过度活跃的树突状细胞做出反应。8
如上所述,在临床医生的指导下,抗炎饮食可以对慢性疼痛管理产生深远的益处。由于慢性疼
痛在细胞水平和症状上都消耗大量能量,因此高收益策略是优先采用抗炎饮食,包括各种色彩鲜
艳的水果和蔬菜。
“吃彩虹”是确保摄入各种植物营养素(包括多酚和类黄酮)的最佳方式,这些营养素可最大限度
地提高线粒体的能量输出、抗氧化支持和解毒。除了吃五颜六色的食物外,保持最佳维生素 D 水平
对于减少炎症也很重要。Zielsdorf 博士建议自身免疫或免疫系统功能障碍患者服用 60‑80 ng/
mL 25‑羟基维生素 D。她对钙、维生素 D、镁的稳态生理反应以及达到这些最佳水平可能需要的高
剂量维生素 D 补充剂的潜在禁忌症很敏感。
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补充维生素D3 时,应监测离子钙、红细胞 (RBC) 镁和 1,25‑
二羟基维生素 D 水平,必要时还应进一步检测甲状旁腺激素。人们对较高治疗剂量维生
素 D 的担忧主要在于钙的置换,从而导致潜在的血管钙化和骨密度降低。然而,许多临床
医生正在使用维生素 K2 ( MK4 和 MK7)来帮助减轻这种可能的影响。维生素 K 促进成
骨细胞(骨骼形成)成熟,并参与成骨细胞中特定基因的上调。
增加维生素 K 还会激活骨相关的维生素 K 依赖性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在细胞外骨基质矿
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9 维生素 D 及其代谢物是一种激素,可通过维生素 D 受体 (VDR)
的表达激活数百种基因。10总体而言,维生素 D 对免疫系统和细胞代谢的影响不可低估。
目前尚不清楚 LDN 与任何矿物质、补充剂、维生素或激素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辅
助性疼痛疗法很少得到如此广泛的考虑。例如,许多患者无法服用传统的 NSAID 或对乙
酰氨基酚。NSAID 类药物因破坏胃肠道而臭名昭著,可导致危及生命的胃肠道出血,以及
通过改变肠道微生物群破坏免疫系统。11 对乙酰氨基酚会消耗谷胱甘肽,而谷胱甘肽是
人体的主要抗氧化剂。12这些药物虽然有时需要短期使用,但不应在不了解可能毒性的更
大影响的情况下使用。低剂量纳曲酮是一种重要的替代药物,对于慢性疼痛管理而言,其
安全性要高得多。
为了取得最佳效果,必须采用多学科、多模式的方法治疗慢性疼痛。这种方法可能包括
药物治疗、针灸、局部电刺激 (e‑stim)、必要时针对结构性缺陷的手术,以及心理治疗/行
为矫正、放松技巧、神经反馈和生物反馈等疗法。瑜伽和健身 包括按摩、肌筋膜松解和针
对特定情况的物理治疗 有助于缓解因肌肉骨骼系统老化和慢性炎症而导致的疼痛,这
些疼痛会加速细胞退化和线粒体功能不全。最后,
14 在许多 LDN 临床医生的实践中,来自各种病因的其他周围神经性疼痛病例
均显示患者疼痛评分和生活质量有所改善。15
复杂性局部疼痛综合征复杂性局部疼痛综合征 (CRPS) 是一种神
经病变,其特征是疼痛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通常与初始损伤不成比例。I 型 CRPS 没有
已知的神经损伤病因,而 II 型 CRPS 是在损伤导致神经病变后发生的。其症状包括感觉
障碍(异常性疼痛和/或感觉过敏)、血管舒缩障碍(温度或肤色变化或不对称)、水
肿或出汗、运动功能障碍(虚弱、肌张力障碍、震颤)和营养变化(头发、皮肤、指甲)。16
CRPS 与炎症状态有关。患有 CRPS 的患者的脑脊液、血浆和受影响组织中的促炎细胞
因子水平升高。17此外,对 CRPS 患者的尸检分析表明,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活化
与该病症有关。18因此,从理论上讲,LDN 可以通过对抗炎症反应和小胶质细胞活化使
CRPS 患者受益。
一份病例报告描述了 LDN 用于治疗糖尿病神经病变的标签外使用。该患者因双下肢糖
尿病神经病变而出现难治性疼痛已有 7 年,多种止痛药和介入治疗均无效。每日 4 毫克
的 LDN 使患者的疼痛在 0‑100 分的视觉模拟量表 (VAS) 上从 90 分降至 5 分。13虽然
该案例研究首次证明了 LDN 缓解糖尿病神经病变疼痛的潜力,但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
确定其安全性、机制和有效性。
许多慢性疼痛患者都有潜在的生活创伤经历。治疗这些深层伤害的新疗法包括眼动脱敏
和再处理 (EMDR) 和边缘系统调节疗法。
有限的证据表明 LDN 可能对治疗 CRPS 有效。文献中有一例病例报告,描述了两名
患有
神经病
CRPS,在常规医疗治疗失败后通过 LDN 成功治疗。第一位患者是一名 48 岁的男性,其右
下肢有 6 年 CRPS 症状病史。在每晚以 4.5 毫克的剂量开始服用 LDN 后,患者的肌张力
障碍性痉挛得到缓解,疼痛也得到缓解。第二位患者是一名 12 岁的女孩,患有 Ehlers‑
Danlos 综合征,她在右踝关节半脱位后出现右下肢 CRPS 症状。患者在每天服用 4.5 毫
克的 LDN 后,所有 CRPS 症状(包括右小腿肌张力障碍)都得到缓解。使用 LDN 的
CRPS 患者的急性和慢性炎症生物标志物 红细胞沉降率 (ESR) 和 C 反应蛋白 (CRP)
均有所下降。
19
骨关节炎
在联合治疗中,人们已经研究了使用纳曲酮治疗骨关节炎疼痛。Oxytrex 是一种试验药物,
它将治疗剂量的羟考酮与微克剂量的纳曲酮结合在一起。20一项 II 期随机临床试验涉及
360 名患有中度至重度髋关节或膝关节骨关节炎疼痛的患者,结果发现与单独使用羟考
酮相比,Oxytrex 可以显著缓解疼痛。21然而,由于退出率高,后续阶段无法获得有效结果。
22
自身免疫/风湿病LDN 与少数自身免疫疾病(包括炎症性肠病 (IBD) 和类风湿
性关节炎)的关联研究已开展。纳曲酮被认为在治疗与阿片类生长因子‑阿片类生长因子受
体 (OGF‑OGFr) 轴功能障碍相关的某些慢性炎症状态方面发挥有益作用,因为已证实它
可以调节该通路。
23
新出现的证据可能支持使用 LDN 治疗 IBD,这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包括克罗恩病
和溃疡性结肠炎。虽然初步研究很有希望,但 2014 年的一项荟萃分析分析了两项小型随
机对照试验,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在克罗恩病中使用 LDN
疾病。24然而,最近的研究取得了积极成果。一项准实验性药物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开
始 LDN 治疗与治疗 IBD 的药物分配减少有关。25一项针对 47 名 IBD 患者的前瞻性
队列研究发现,LDN 可使大多数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内窥镜检查显示缓解和粘膜愈
合。26尽管取得了这些成果,但 2018 年的 Cochrane 系统评价得出结论,目前缺乏足
够的高质量证据证明 LDN 在治疗克罗恩病方面的疗效和安全性。27由于约 30% 的炎
症性肠病患者对目前的 IBD 药物有抵抗力或复发,并且目前的治疗具有明显的副作用,
因此 LDN 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提供了一种低风险的替代方案。更激进的建议是,
如果病情较轻或处于早期阶段,那么就可以问,既然越来越多的证据和案例研究证明了
LDN 方案联合抗炎饮食的益处,为什么不应在其他治疗方案之前尝试呢?
迄今为止,探索 LDN 在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RA) 和其他风湿病中的作用的研究有
限。
文献中有一项最近的准实验研究。研究发现,LDN 疗法与减少使用其他药物(包括止痛
药)治疗类风湿和血清阳性关节炎有关。28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评估 LDN 对炎性关节炎
的疗效。RA 患者的临床经验表明,抗炎饮食和 LDN 的结合使一部分患者能够减少或停
止使用甲氨蝶呤等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物 (DMARD)。
《甲状腺》杂志于 2018 年发表的一篇期刊文章通过对超过 12,000 名受访者进行
的在线调查表明,大多数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对目前的治疗方法或医生并不满意。29
Zielsdorf 博士的诊所专注于甲状腺治疗,并以通过使用低剂量纳曲酮和个性化的甲状
腺激素处方和管理方法改善生活质量而闻名。
甲状腺疾病通常是自身免疫介导的,可能导致格雷夫斯病引起的临床甲状腺功能亢进
或桥本甲状腺炎引起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亢进。症状和由此产生的疾病状态取决于针对
特定抗原产生的自身抗体,
随后细胞发炎,目标器官和组织遭到破坏(桥本甲状腺炎最终导致甲状腺萎缩和功能丧失)。通过电子邮
件和社交媒体向诊所患者以及社交媒体网站上的甲状腺和 LDN 宣传小组发送了在线调查问卷。2019 年
2 月 19 日至 3 月 7 日期间,1108 名受访者完成了包含 24 个问题的调查问卷(1610 次独⽴访问,完成率
为 68.8%)。
参与者被问及扩大的治疗方案,包括合成 T4、合成 T3、NDT、复合 T4、复合 T3、合成 T4/T4 组合、腺体
甲状腺补充剂和碘,以及他们是否曾使用 LDN 作为辅助甲状腺治疗。
总体而言,479 名受访者(43.4%)使用了 LDN,其中 53.6% 的人每天使用 3.6 至 4.5 毫克,53.2% 的人
服用 LDN 超过 12 个月。此外,20.4% 的人将他们的症状评为 10 分,即“显著改善”(1 至 10 分制)。在
服用 LDN 的甲状腺患者中,56.9% 的人疼痛减轻,55% 的人精力充沛、疲劳减轻,41.7% 的人情绪改善。
30这项调查的结果强调,甲状腺患者在用药方案中添加 LDN 后,疼痛通常会得到缓解。LDN 是减轻炎症
和改善甲状腺功能的重要辅助手段,并可能逆转桥本甲状腺炎/格雷夫斯病的自身免疫过程。临床医生应
采取个性化的甲状腺治疗方法;没有一种药物或方案适合所有人。
多发性硬化症
多发性硬化症 (MS) 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涉及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31 2017 年,美国有近 100 万人
患有 MS。32 临床前研究表明 OGF‑OGFr 轴失调是 MS 病理生理学的一个特征,表明 LDN 可作为潜在的
治疗剂。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 (EAE) 诱发的小鼠是公认的 MS 动物
模型,在出现疾病临床症状之前,OGF 水平就会降低。33在同一动物模型中,用 LDN 或 OGF 治疗可
抑制 EAE 的进展。34引入 LDN 疗法可恢复
肌筋膜疼痛
关于使用 LDN 治疗肌筋膜疼痛的数据很少。文献中只有一例病例报告描述了使用 LDN 治疗慢性背痛的情况。
患者有两年椎旁腰痛病史,对非甾体抗炎药、抗惊厥药、三环类抗抑郁药、物理治疗和介入治疗均无效。在接受每
日 4 毫克剂量的 LDN 治疗后,患者的疼痛在 0‑100 分视觉模拟量表上从 90‑100 分降至 35 分。41需要更多
研究来跟进这一份可用的病例报告。
后续研究也提供了证据,表明 LDN
耐受性良好,并显著改善了 MS 患者的生活质量。38然而,一些研究并未发现太多益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
LDN 对 MS 患者是安全的,但疗效未知,一项准实验性前后研究报告称,LDN 治疗后并没有减少用于治疗 MS
的药物。39然而,后一项研究还表明,持续使用 LDN 的使用者的阿片类药物使用量显著减少。这包括累计剂量
减少 42%,使用者数量减少 9%。此外,NSAID 使用者数量减少了 8%。40总体而言,研究表明 LDN 对 MS 患者
的生活质量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在疼痛和疲劳管理方面。
OGF 在 EAE 小鼠和 MS 患者中均有效。35此外,用 LDN 或 OGF 治疗的 EAE 小鼠的干扰素‑γ 和肿瘤坏死因
子 α 水平降低。36在临床环境中,LDN 在 MS 治疗中的应用已显示出一些有希望的结果,尽管尚无定论。一项试
点试验表明,LDN 对原发性进展型 MS 患者安全且耐受性良好,并可显著减
少痉挛。
文献中还有一项 III 期临床试验,研究了 Oxytrex 在慢性腰痛患者中的应用。42其研究结果是,在羟可酮中
添加超低剂量纳曲酮 (ULDN) 可提供更好的镇痛效果并减少阿片类药物的副作用。然而,这项研究
三十七
纤维肌痛
腹痛/盆腔痛
患者还报告有慢性疲劳、认知障碍、头痛和胃肠道症状。46不幸的是,这种疾病主要折磨女性,通常被视
为心身疾病。
LDN 的抗炎特性可能有助于治疗纤维肌痛。纤维肌痛的病理生理学涉及神经胶质激活和促炎分子
的产生。这些促炎分子会引起神经刺激,从而产生过敏性疼痛反应。47一项研究 LDN 对纤维肌痛影响
的初步研究发现,个体的基线红细胞沉降率可预测其对 LDN 治疗的反应。
纤维肌痛是一种知之甚少的疾病,其特征是与多个压痛点相关的慢性、弥漫性肌肉骨骼疼痛。44患病率
约为人口的 2% 至 8%。45纤维肌痛的特点包括睡眠障碍、疼痛和压力反应。
因其高退出率和其他限制因素而受到批评,这可能会损害其临床意义。43
初步临床研究支持了 LDN 疗法在治疗纤维肌痛中的作用。两项小型临床试验发现 LDN 耐受性良
好,并能有效减轻纤维肌痛症状。50最近的一项小型前瞻性研究证实了这些发现。51需要进行更大规
模的对照试验,以充分评估 LDN 在治疗纤维肌痛方面的疗效。
此外,LDN 治疗与炎症生物标
志物减少有关,同时疼痛和其他症状也得到改善。49 Ginevra Liptan 博士本人也是一名纤维肌痛内科医生,她在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创⽴了 Frida 纤维肌痛中心。她表示,“对于纤维肌痛,我发现 CBD 和 LDN 的组合比单独使用
任何一种治疗更能有效减轻疼痛。CBD 还可以缓解 LDN 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焦虑。”
四十八
“功能性”腹痛可以说是用药过度和治疗单一的疾病之一。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肠易激综合征这个
术语是一种垃圾诊断,包括“特发性”分类。临床医生很少能恰当地找出 IBS 疼痛的根本原因。为了让
临床医生相信,传统的生物标志物测试(如完整的代谢组或全血细胞计数)很少出现异常,患者很难描
述疼痛的位置或性质。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方法才能找到疼痛、便秘、腹泻和其他 IBS 症状的根本原因。
疼痛受体可能在浅表或深层组织中被激活。这些可能包括躯体受体(包括肌肉骨骼系统)或胸部、腹
部或骨盆器官内的内脏受体。这些受体中的任何一个,无论是单独还是组合,都会发出身体受损的警
报。此外,治疗往往比症状更难忍受。如果突然停止服用解痉药、抗抑郁药、苯二氮卓类药物或阿片类药
物等药物,患者可能会面临严重的戒断症状,统称为停药综合征。LDN 使用者不会面临这种困境。
2006 年的一项试点研究首次研究了 LDN 对 IBS 的影响。以色列的一个研究小组招募了 42 名
IBS 患者参与一项开放标签研究,每天服用 0.5 毫克 LDN,持续四周。没有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76%
的患者通过整体评估做出反应,该评估测量了无痛天数和症状缓解情况。患者记录了腹痛程度和排便
紧迫性、稠度和频率。该研究具有统计学意义,并得出结论,大规模、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是合理
的。
十多年过去了,仍未开展过此类研究。52
慢性腹部和重叠盆腔疼痛病症的其他例子包括子宫内膜异位症、间质性膀胱炎和外阴痛。
患者可能同时出现一种或多种问题。上述每种情况的病理生理学尚不明确。有理论认为,免疫系统激活
和微生物群失调如何使身体转向促炎状态,从而导致慢性疼痛。
在子宫内膜异位症(尚未归类为自身免疫性疾病,但经常在患有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女性中
表现)中,子宫内膜组织会根据月经周期变厚并分解,但由于该组织位于子宫外部,因此被困在盆腔
中,导致月经逆行。
子宫内膜组织非常有趣 它可以在子宫内形成(先天性子宫内膜异位症),也可以由医源性形
成。例如,在剖腹产的情况下,当外科医生冲洗盆腔时,这些子宫内膜迁移细胞可能会散布在整个腹
腔内。这进一步加速了组织生长、炎症和症状严重程度的过程。此外,在女性中,卵巢附近腹膜上的一
个小开口是细胞迁移到任何胃肠道器官的机会,无论是否进行手术干预。一个案例研究涉及一名子
宫切除术后患者,由于医源性子宫内膜异位症而需要切除阴道穹窿。子宫切除术后 13 个月,她突然
出现下盆腔不适和阴道出血。
53如
果影响到卵巢,就会形成囊肿,即子宫内膜异位症,结果就是慢性刺激和瘢痕形成和粘连,导致剧烈疼
痛和不孕。瘢痕形成还会导致性交疼痛(性交困难)、泌尿道症状和其他症状。
Jennifer Mercier 博士是女性健康专家,也是女性内脏推拿疗法(即 Mercier 疗法)的创始人,
她讨论了子宫内膜组织的侵袭性以及子宫内膜异位症如此具有破坏性的原因:“这些迁移细胞粘附
在腹部和盆腔的结构上,随着月经的到来,这些迁移的子宫内膜细胞会将液体渗入腹腔和盆腔,导致
疼痛和疤痕组织的形成,这些疤痕组织会将任何物体粘住。任何被粘住的物体都会血流不足。从本
质上讲,器官需要自由地相互移动才能正常运作。”54在饱受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和 IV 期子宫内
膜异位症的折磨多年后,Mercier 博士偶然发现了这种新疗法。在经历了三次腹腔镜手术后,她躺在
床上,通过自我操纵内脏并观察自身症状随时间的变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疗方法。最终,她发现自
己的月经会自然来潮,而且没有明显的盆腔和阴道疼痛。
通常会导致她的月经周期加速,并延伸到她的腿部或腰痛。
使用 Mercier 博士的治疗方案六小时(每周一小时,持续六周)的患者自然受孕率提
高了 83%。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建议进行维持治疗。
尽管 Mercier 疗法具有明显的优势,但目前尚无正式认可的替代疗法,无需使用阿
片类药物/止痛药、激素避孕药或手术即可治疗长期疼痛。深部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定
义为深度超过 5 毫米的腹膜下侵袭)的黄金标准是腹腔镜手术。由于这些深部子宫内
膜异位病变遍布整个腹腔内,并经常扩散到腹膜外,因此这些病变引起的剧烈疼痛很难
定位。55转诊至胃肠科通常无济于事,因为内窥镜检查只能检查内部,而腹腔镜评估只
能让医生看到盆腔器官,但无法物理检查肠道的所有环路。尸体研究表明,子宫内膜异
位症可能存在于活体女性的鼻腔和脑部物质中。
子宫内膜粘连是导致周期性头痛和流鼻血的原因,而此前人们认为这些症状与子宫内
膜粘连无关,且女性的病因不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一个案例中,一名女性的鼻腔
结节自青春期以来就一直导致周期性出血 手术切除和病理分析证实了子宫内膜异位
症。56
正在进行临床试验,以评估 LDN 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引起的慢性腹痛的治疗潜力。由
于子宫内膜异位症本质上是炎症,并且可能是自身免疫介导的,因此 LDN 可用作疼痛
管理的辅助疗法。57
来自临床实践的见解
在临床实践中,患者报告了使用 LDN 治疗慢性疼痛的一系列体验。虽然有些患者报告
疼痛程度没有变化,但其他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所改善,有时甚至完全缓解了疼痛。除了
改善疼痛管理外,使用 LDN 的好处还包括减少疲劳、改善情绪、减少睡眠障碍和增强
认知功能。我们发现患者可能会经历
结论
虽然目前关于该主题的临床数据很少,但 LDN 也可能对患有 Ehlers‑Danlos 综合征的患者有所
帮助。EDS 包括一组影响结缔组织的异质性遗传性疾病,其特征是关节过度活动、组织脆弱和皮肤过
度伸展。
临床实践中使用的 LDN 剂量范围比文献报道的要广。虽然现有研究的标准剂量约为 4.5 毫克,但
有些患者最初服用的剂量低至 0.5 毫克,随后在门诊时增加剂量以达到效果。服用较高剂量出现副作用
的患者通常会将剂量减少到 3 毫克或更低。
EDS 患者最初可能表现为伤害性关节疼痛,随后可能导致神经病变的发
展。59开始接受 LDN 治疗的 EDS 相关慢性疼痛患者报告称,活动能力得到改善、发作频率减少、胃肠
蠕动增强以及疼痛耐受性提高。
尽管关于该主题的信息有限,LDN 疗法在美国和国外都越来越受欢迎。美国有 250 多家药店提供
LDN。60在挪威,一部关于 LDN 的电视纪录片导致其处方量大幅增加;据报道,该国 0.3% 的人口使用
过该药物。61
服用 LDN 的患者报告的罕见副作用包括短暂失眠、梦境逼真、头痛、恶心和焦虑。我们尚未在患者群体
中观察到任何严重不良事件。
临床文献显示,LDN 的说明书外使用在治疗慢性疼痛方面已显示出一些积极的(尽管是初步的)结果。
根据我们的经验,LDN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
开始服药时,LDN 可能会产生安慰剂效应。因此,患者可能需要连续服用 LDN 数周甚至数月,才能确定
药物的真正效果。一般来说,对于慢性疼痛患者,建议进行六个月至一年的试验,然后再确定药物是否
有效。最重要的是,必须强调的是,LDN 很少是缓解慢性疼痛的灵丹妙药。
58
仍然需要进行适当的大规模研究来调查 LDN 对慢性疼痛状况的用途。此外,最佳
给药方案尚未阐明。尽管需要进行高质量的试验,但开展这项研究仍存在障碍。
纳曲酮已过专利保护期,价格低廉;因此,开展这些试验的经济激励很少。62临床医生
没有接受有关这种治疗方案的教育,入院患者在使用 LDN 时会遇到不了解甚至歧视
的反应。与此同时,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提供低风险疗法(而不仅仅是缓解症
状),以治疗严重影响快速增长的老龄化人口的慢性疼痛疾病。LDN 是一种重要的辅
助疗法,填补了传统对抗疗法和补充疗法综合治疗工具箱中的空白。
‑三‑
肠道健康
LEONARD B. WEINSTOCK 医学博士、FACG 和 KRISTEN
BLASINGAME 马萨诸塞州
有几种胃肠道 (GI) 疾病和病症可使用低剂量纳曲酮作为治疗剂。允许使用 LDN 治疗肠道疾病和病症的病理因
素包括不受控制的炎症、异常免疫、肠道通透性增加、内脏过敏增加、异常运动和不受控制的细胞生长。在本章中,
我们回顾了医学文献中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说明了 LDN 在 GI 疾病和肠道健康途径中的作用。这些疾病包括
炎症性肠病、便秘、胃轻瘫、肠易激综合征 (IBS)、肥大细胞活化综合征 (MCAS)、结节病和肠系膜脂膜炎。本章最
后将简要讨论 LDN 在 GI 癌症中的应用。
对于大多数此类疾病,我们将回顾我们的经验和/或提供尚未发表的病例系列的数据。
本书第一章详细描述了 LDN 减轻炎症的作用机制,该机制适用于本章中的一些胃肠道疾病。临床医生并不
了解 LDN 或内啡肽在治疗运动障碍方面的潜在用途。如果 LDN 确实能改善运动能力,那么它可以用来治疗便
秘、小肠运动异常、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和胃轻瘫。通过减少 T 细胞来降低过度活跃的免疫系统可以帮助治疗
MCAS、结节病和肠系膜脂膜炎。直接的类似收费
纳曲酮受体阻断有助于减少肠易激综合征(IBS)中的内脏高敏感性等神经炎症过程。
正常和异常的肠道结构
上述许多疾病会扰乱健康肠道的平衡结构。在健康肠道中,健康的细菌会附着在杯状细胞产生的粘液
上。粘膜有隐窝(内翻),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吸收表面积。肠嗜铬细胞散布在上皮细胞中,调节肠道蠕
动和分泌。它们还通过分泌血清素和其他肽来调节肠神经系统中的神经信号。连蛋白和闭合蛋白是形成
桥梁的蛋白质,可维持上皮细胞之间的紧密连接。粘膜下丛中有神经、血管和树突状细胞。神经与其他神
经连接,穿过肌肉层,最终连接到中枢神经系统。
当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IBO)或菌群失调(细菌群落不平衡)时,附着的细菌会引起炎症。
因此,杯状细胞产生的保护性粘液减少,使细菌得以附着在上皮上。随着肠道通透性的增加,革兰氏阴性
细菌(称为脂多糖)通过粘膜屏障进入。这会扰乱下丘脑‑肾上腺‑垂体轴。连蛋白和闭合蛋白产生的细
胞因子会破坏紧密连接。树突状细胞通过募集肥大细胞和 T 细胞和 B 细胞淋巴细胞来应对这种炎症。
肥大细胞会分泌许多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既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损害,也有助于介导炎症过程,具
体取决于它们的遗传状态。T 细胞淋巴细胞会分泌细胞因子,包括白细胞介素和肿瘤坏死因子 α,它们
是强效的炎症化学物质。它们会进一步破坏肠道通透性,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种炎症风暴会激活神经
并导致异常的疼痛感和运动性。 B 细胞淋巴细胞制造抗体,其中一些可能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根源。
4
2
在环境触发事件的背景下,异常基因组和改变的微生物组可能是炎症性肠病发展的条件。炎症和溃疡
的深度增加会导致瘘管,进而形成脓肿。肠壁炎症会导致纤维化、疤痕组织和狭窄。内质网(决定细胞
结构)的损伤可能在狭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克罗恩病极难治疗。尽管使用了昂贵的药物,但没有人能
找到完美的治疗方法。此外,一旦患者使用生物疗法后病情有所改善,这些药物的疗效就会降低 13%
至 24%。据认为,30% 至 60% 的炎症性肠病患者将出现治疗抵抗,需要他们转而接受手术或使用类
固醇。3自 2016 年 2 月《LDN 书》出版以来,已经发表了多篇关于 LDN 在炎症性肠病中的应用的文
章。 2018 年的一项评论审查了克罗恩病领域高质量研究的文章和摘要,其中两篇研究成果在《LDN
书籍》炎症性肠病章节中进行了讨论。
它们都涉及异常免疫和炎症,并且通常对相同的药物有反应。它们在几个方面也有所不同。阅读该章节,
详细讨论 LDN 如何降低异常免疫和炎症,从而降低炎症性肠病的疾病活动性。克罗恩病是一种肠道
炎症性疾病,可从口腔开始,一直延伸到肛门,可能导致肛周疾病。它是一种溃疡性疾病,始于粘膜,由
淋巴细胞的异常作用、过量细胞因子和血管通透性改变引起。
炎症性肠病在《LDN 书》第一卷中,第 3 章描述了 LDN 疗法对
炎症性肠病 (IBD) 的影响。1两种主要的慢性炎症性肠病是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
该评论的作者表示,所审查的研究
样本量较小,但表明 LDN 可改善成人的临床和内窥镜反应。他们警告说,需要进一步进行随机研究来
评估 LDN 对克罗恩病的疗效。5
2018 年评论中提到的一项较新的研究是动物模型研究。对于炎症性肠病,这类研究很重要,原因有很多。它们可
以控制情况并进行精确测量,而且通常不用担心安慰剂效应。可以更有效地建⽴确定因果关系的框架。在上述研究中,
给大鼠注射非甾体抗炎药吲哚美辛,以诱发小肠炎症。6 研究表明,皮下注射或口服吲哚美辛会导致大鼠小肠溃疡。将
此用作实验模型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非甾体药物通常会加重人类的克罗恩病。尽管如此,动物的 NSAID 损伤本身并不
是克罗恩病。
注射吲哚美辛后,大鼠接受安慰剂(柳氮磺吡啶)、纳曲酮或两种药物治疗。测量两种炎症标志物(C 反应蛋白
和肿瘤坏死因子)以确定疾病活动性。用吲哚美辛治疗后,仅用纳曲酮治疗的大鼠的肿瘤坏死因子水平为 73 pg/ml,而
仅用吲哚美辛治疗的动物的肿瘤坏死因子水平为 599 pg/ml。纳曲酮治疗动物的组织病理学也有显著改善。7
以人类为对象的研究也证明了 LDN 在治疗 IBD 方面的功效。一项针对 40 名炎症性肠病患者的研究检查了每天
服用 0.5 毫克纳曲酮的效果。他们检查了 7 名患者接受 LDN 治疗前后的血液和活检组织。23 名患者有临床反应,其
中 13 名患有克罗恩病,10 名患有溃疡性结肠炎。一项针对这些患者活检组织的体外研究检查了应激对细胞内质网的
影响。内质网是细胞膜网络,在蛋白质和膜脂质的合成和运输中起重要作用。研究人员证明,与对照组相比,接受 LDN
治疗的患者细胞向伤口的迁移有所改善。内质网应激在炎症性肠病的疤痕组织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纳曲酮可以改善
内质网应激。在这项小型研究中,患者血液中的肿瘤坏死因子或白细胞介素 8 并未改善。
8
2013 年,挪威 LDN 的使用量显著增加,据信这要归因于一部有关该药物的电视
纪录片被广泛观看。9随后,挪威的一项研究调查了 LDN 是否能改变炎症性肠病患
者的用药情况。作者研究了 582 名患者在开始 LDN 治疗前两年和治疗后一年的用药
情况。在这些患者中,有 256 名成为该药物的常规使用者。在继续使用 LDN 的患者
中,处方肠道类固醇的使用量显著减少,其中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减少了
50%。这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因为类固醇会引起许多严重的副作用,甚至会增加炎症
性肠病患者的死亡风险。10
荷兰开展了一项关于纳曲酮治疗炎症性肠病的最新研究。11这项研究评估了
LDN 诱导炎症性肠病缓解的潜力。LDN 被用作对常规疗法无反应的患者的附加或补
充治疗。在这项为期 12 周的研究中招募的 47 名患者中,75% 的患者临床症状有所
改善,26% 的患者病情缓解。这项研究还表明,LDN 通过改善伤口愈合和减少内质网
应激来改善上皮屏障功能。作者表示,他们的缓解率低于 Smith 等人在 2011 年的
一项研究中报告的缓解率,尽管他们认为很难进行比较,因为他们自己的患者病情更
严重,而且另一项研究的样本量较小。12自 2005 年以来,我在自己的实践中看到了
LDN 对炎症性肠病的显著效果。我在 2014 年发表的有关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
中的 LDN 的出版物中概述了其中一些结果。13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经常为 IBD 患者提供 LDN,其中 50% 以上患者获得了显
著的益处。我曾将 LDN 与生物制剂联合使用和/或代替硫唑嘌呤,硫唑嘌呤有患淋巴
瘤的风险。我甚至还遇到过几位患者,LDN 单一疗法对他们有益。
肠道健康和动力
胃肠道最重要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将食物从食道运送到胃中,在那里肌肉活动和胃酸开始消化过程。
然后蠕动将食物带入小肠,在那里胰腺酶进一步消化过程并帮助吸收营养物质、电解质和水。剩余
的液体和碎屑随后迁移到结肠,在那里水被吸收并形成粪便。微生物群在粪便形成中起着重要作
用,因为粪便重量的 50% 由细菌组成。
蠕动活动使粪便向下移动以便排出。禁食状态会触发周期性移行运动复合体,这对于保持小肠清
洁、无碎屑和细菌非常重要。14上述过程是精心策划的,涉及神经、肌肉、神经递质、激素和内啡肽。
15蠕动反射由胆碱能运动神经元与速激肽(如 P 物质)以及其他运动神
经元和化学物质(包括血管活性肠肽和内源性阿片类药物)协同调节。阿片类药物的释放似乎
对蠕动有抑制作用。内源性阿片类药物对环形平滑肌有直接的紧张作用,从而减少蠕动。因此,由于
肠溶阿片类药物调节蠕动,使用阿片类拮抗剂(如纳曲酮)治疗可以改变这种调节并减少对蠕动的
抑制。内源性内啡肽在运动生理学中的参与表明,当出现运动障碍时,LDN 可能发挥作用。
肌肉和肠道内壁中存在内啡肽受体。当使用麻醉剂时,这些受体会导致便秘,因为持续的非推进
性肌肉收缩会导致分泌减少和蠕动丧失。人们会认为通过 LDN 增加天然内啡肽会产生同样的作
用。正常的肠道功能主要是协调的神经肌肉功能和平衡的液体和电解质分泌和吸收的结果。肠道激
素控制氯化物以及随后的钠和水分泌,从而保持粪便水分充足。正常运动的两个主要驱动因素是
(1) 正常的血清素水平和 (2) 平衡的副交感神经和交感神经系统。血清素 (5‑羟色胺 [5‑HT]) 是肠
神经系统 (ENS) 的主要神经递质。16血清素是脑肠轴中的一种分子,其中 95% 存在于
20
另一项研究表明,在正常运动中,生长抑素、阿片类药物、GABA 和血管活性蛋
白神经元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
已经有一些关于蛋氨酸脑啡肽(一种内源性阿片肽)和纳曲酮对蠕动和移行性运动复合体影响的研
究。三十年前,生理学家研究了阿片神经在调节肠道蠕动中的作用。他们的研究表明,阿片拮抗剂会增加蠕
动收缩的频率和幅度。阿片拮抗剂还增加了下行松弛并减少了上行收缩。17
胃肠道内壁的肠内分泌细胞以及胃肠道中间神经元。5‑HT 对胃肠道血清素受体的作用会触发粘膜下内在
初级传入神经元表现出蠕动和分泌反射。迷走神经释放乙酰胆碱,导致蠕动运动,而 5‑HT4 会进一步增强
这种运动。ENS 向大脑发出的信号由 5‑HT3 介导。
有人提出,内源性阿片肽通过激活 mu 和 kappa 受体抑制
蠕动性能,从而参与蠕动的神经控制。
由于肠道伸展而导致的生长抑素增加,导致阿片类神经元活动受到抑制,从而导致甲硫氨酸脑啡肽减少。通
过减少阿片类神经活动,血管活性肠肽 (VIP) 和一氧化二氮的产生有助于激活蠕动。18一项研究检查了静
脉注射甲硫氨酸脑啡肽对 17 名人类志愿者的食管运动和移行性运动复合体的影响。这种内啡肽类似物降
低了下食管括约肌的完全松弛,并且由于扩张而降低了胃底调节能力。这
项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甲硫氨酸脑啡肽增加了移行性运动复合体,这是小肠细菌过度生长患者出现的
问题之一。人们怀疑甲硫氨酸脑啡肽类似物通过抑制抑制性神经系统而诱发了这些影响。19在另一项研究
中,小鼠实验性炎症导致 μ‑阿片类受体增加,其方式类似于人类腹部手术后观察到的过程。
此外,人们认为阿片类受体拮抗剂可以使因阿片类药物上调和/或过度活跃而导致的肠道功能病理抑制正
常化。Holzer 团队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
22
另一项研究涉及静脉注射甲氧苄啶的鸡。
随后,Weinstock 博士在实践中发现,几名患者每天或每天两次服用 2.5 毫克 LDN,
便秘症状有所缓解。在接受其他药物治疗特发性便秘的 LDN 患者中,约有 25% 的患
者获得了显著益处。
移行性运动复合体第三阶段被触发,它始于远端十二指肠并传播至
回肠。这一现象对于本章后面讨论的一种疾病 小肠细菌过度生长 很重要。
阻断结肠中的 Toll 样受体 4 (TLR‑4) 在阿片类药物引起的便秘中发挥作用。21合成的
TLR‑4 拮抗剂不会改变吗啡诱导的豚鼠小肠蠕动抑制,但吗啡诱导的结肠蠕动抑制可
被 TLR‑4 拮抗剂减轻。
一项小型研究发表显示,LDN 对特发性便秘患者是一种有益的药物。23在这项报告
中,12 名慢性便秘患者每天两次服用 2.5 毫克 LDN。七名患者明显好转,一名患者中度
好转,三名患者轻度好转,一名患者无变化。Weinstock 博士参与了这项非安慰剂对照
研究。这些患者对其他治疗无效,尽管在 2010 年,FDA 批准的更先进的氯离子通道激
活药物尚未上市。
胃轻瘫网上有一个关于特
发性胃轻瘫成功使用 LDN 治疗的病例介绍。24医生写道,患者对 LDN 有积极的反应,
尽管很难分离出 LDN 的效果。
便秘的定义是每周排便少于三次、排便费力且大便坚硬。至少有 20% 的美国人患有这
种疾病。相关的病理生理学可归因于蠕动不良、液体和电解质分泌减少和/或盆底功能
异常。
便秘
LDN 是因为它与针灸、内脏按摩和医用大麻一起开具。一项随机、安慰剂对照研究正在启动,以检查高剂量
纳洛昔康(一种外周活性 μ‑阿片受体拮抗剂)对阿片类药物相关胃轻瘫的影响。25 鼓励开具处方的临床医
生报告 LDN 对特发性胃轻瘫的影响。
肠易激综合症
肠易激综合征(IBS)是一种胃肠道疾病,其特征是腹痛和肠道功能改变,并常伴有腹胀和排便紧迫感。26与
肠易激综合征相关的异常排便习惯可能是便秘为主 (IBS‑C)、腹泻为主 (IBS‑D),或者它们可能涉及交替或
疾病在女性中比男性 混合时期 (IBS‑M)。27据估计,北美的肠易激综合征患病率为 10% 到 15%。28这种
更为普遍,但这种偏见可能没有医生通常认为的那么明显,因为平均而言,女性在看医生时感觉更舒服。在一
项家庭电话调查中,女性和男性的 IBS 患病率之比为 6:4。29尽管 IBS 是胃肠病学家最常见的诊断,但这种
疾病往往得不到诊断或治疗,只有 25% 的 IBS 患者寻求临床治疗。30 IBS 是一种复杂的疾病。它是一种
“综合症”,意味着有多种疾病和因素会导致同一组症状。
因此,在临床研究中,没有一种特定的治疗方法能够 100% 有效。只要有可能,就必须确定可以进行特定治
疗的潜在机制。IBS 的诊断主要基于排除其他可能的诊断(例如炎症性肠病、乳糜泻、结直肠癌、乳糖不耐
症、胰腺功能不全、肥大细胞活化综合征和蔗糖酶‑异麦芽糖酶缺乏症)。31历史上,人们往往将 IBS 简单地
视为特发性过敏综合征或非特异性“功能性”应激障碍。32
已经出现了两种生物标记物来识别 IBS 亚型。一种生物标记物是抗黏着斑
蛋白抗体。对患有以下疾病的 IBS 患者进行运动测试
SIBO 的证据确定了移行性复合运动受损。33一项动物研究表明,接种弯曲杆菌后患上
感染后肠易激综合征的大鼠会失去健康的移行性复合运动所需的神经细胞(卡哈尔间
质细胞)。34经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抗黏着斑蛋白是造成这种神经损伤的自身抗体。35移
行性复合运动受损后,从胃部开始并流经小肠的夜间清洁波会消失,从而导致小肠细菌
过度生长。SIBO 的后续结果包括 (1) 碳水化合物发酵导致胀气和腹胀,以及 (2) 炎症和
肠道通透性增加(“肠漏”)。
另一种生物标记物是氢气和甲烷气体,可通过呼吸测试测量。36 2000 年的一项研究
评估了乳果糖呼吸测试作为 SIBO 诊断方法以及衡量患者对抗生素治疗的后续反应的
方法。该研究表明,在符合罗马 IBS 诊断标准的 202 名患者中,157 名(78%)也患有
SIBO。37在接受口服抗生素治疗(例如新霉素、环丙沙星、甲硝唑、强力霉素)10 天后,
47 名患者接受了后续呼吸测试。与 SIBO 持续存在的患者相比,25 名 SIBO 已根除的患
者的腹泻和腹痛症状明显改善(P < 0.05)。其中 12 名患者(48%)不再符合罗马 IBS
标准(P < 0.001)。随后进行的一项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表明,111 名 IBS 患者中 93
名(84%)在基线时乳果糖呼气测试结果异常。38经过 10 天的新霉素或安慰剂治疗后,
接受新霉素治疗的基线时呼气测试结果异常的患者的便秘、腹泻和腹痛症状改善了
35%,而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仅改善了 4% (P < 0.01)。
此外,新霉素治疗后乳果糖呼气试验的正常化与患者报告的肠道功能正常化相关。
在呼吸测试表明新霉素根除 SIBO 的患者中,肠道正常化程度提高了 75%,而新霉素未
根除 SIBO 的患者肠道正常化程度提高了 37%,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肠道正常化程
度提高了 11%
(P < 0.001)。39因此,这些研究结果不仅支持在 IBS 诊断中使用乳果糖呼气试验,而且还强调了抗
生素根除 SIBO 与 IBS 缓解之间的联系
症状。
随后,几项大型研究证实了利福昔明(一种非吸收性肠道导向抗生素)治疗 IBS‑D 的疗效。这些出
版物最终促使 FDA 在 2015 年批准了抗生素治疗 IBS‑D。40一项后续研究表明,呼吸测试异常预示着
利福昔明疗效良好。41最后,在与 SIBO 相关的 IBS 病例中,需要解决 SIBO 的根本原因,因为通常需要
重复抗生素治疗。42多种促动力药物已被证明可以减少 SIBO 的复发。43以色列的研究人员进行了第
一项评估 LDN 在 IBS 患者中的使用情况的已发表研究。44他们的理论是,当内在内啡肽延长动作电
位持续时间、增加钙内流并促进神经递质释放时,可能会发生内脏过敏或内脏疼痛感增强。
他们假设内脏高敏感性可通过 LDN 得到缓解。他们招募了 42 名患者参与一项开放标签研究。患者每
天服用 0.5 毫克纳曲酮,持续一个月,并在基线、治疗期间和四周后的随访中进行评估。评估的症状包括
腹痛、尿急、排便的稠度和频率。研究确定,这些患者中有 76% 的总体症状得到缓解。无痛天数从 0.5
天增加到 1.25 天,这具有统计学意义。
然而,这项研究存在问题,因为样本量太小,持续时间太短,并且采用开放标签设计。此外,IBS 患者
的安慰剂效应发生率也显著较高(约 30% 至 35%)。在接受治疗的 42 名患者中,有 18 例不良事件,
包括口腔炎、各种感染、头痛、过敏性皮炎和偏头痛。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这些副作用并不严重,而且该
药物总体耐受性良好。LDN 治疗后无痛天数在 70% 至 86% 之间。IBS‑C 患者的反应最好。这项研究
设计的独特之处在于,IBS 受试者可能患有腹泻为主的类型、便秘为主的类型
类型或混合类型。一般来说,药物研究每次只针对一种亚型,并采用特定的药物疗法。
Weinstock 博士在使用 LDN 治疗 IBS 方面的经验涉及两类人群:(1) SIBO 阳性
患者,可能有或可能没有疲劳或肠外疾病;(2) SIBO 阴性患者,使用 FDA 批准的药物治
疗无效。他关于该主题的第一份报告研究了使用纳曲酮作为第二种药物的患有 SIBO
的 IBS 患者。45
随后,Weinstock 博士又对其他患者接受 LDN 治疗 IBS 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回顾,
这些患者中有些患有 SIBO,有些则没有。患者被要求评估他们对 LDN 的临床反应,说
明他们是明显改善、中度改善、轻微改善、不变还是恶化。在 68 名服用抗生素后服用
LDN 的 SIBO 阳性患者中,15 名患者(17.6%)明显改善,32 名患者(37.6%)中度改
善,11 名患者(12.9%)轻度改善。在 13 名 SIBO 阴性患者中,2 名(15.3%)明显改善,
5 名(38.5%)中度改善,2 名(15.3%)不变,3 名(23.1%)明显恶化。
一篇较新的、未发表的评论对 Weinstock 博士接受 LDN 治疗的 IBS 患者进行了
回顾,其中有以下观察结果。在接受抗生素治疗的 33 名 IBS 便秘患者中,19 名患者病
情明显好转,7 名患者病情略有好转,7 名患者病情无变化。这些患者随后平均使用 LDN
10 个月。有 30 名患者的随访数据。
18 名患者(47%)的治疗反应显著改善,6 名(15.7%)的治疗反应轻微改善,11 名
(28.9%)的治疗反应无改善。5 名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导致 LDN 治疗提前终止。
在 22 名 IBS 腹泻患者中,有 20 名接受了抗生素治疗。其中 13 名(65%)患者综合
表现为明显和中度改善,1 名(5%)患者表现为轻度改善,6 名(30%)患者没有获益。在
对所有 22 名患者使用 LDN 后,12 名患者(55%)综合表现为明显和中度改善,1 名
(5%)患者表现为轻度改善,6 名患者(27%)没有获益。
三名(13%)患者由于副作用而退出治疗。
目前尚无 FDA 批准的治疗混合便型肠易激综合征 (IBS‑M) 的药物。在接受抗生素
治疗的 24 名 IBS‑M 患者中,16 名 (66%) 患者
抗生素治疗后,18 名患者出现明显反应,4 名 (17%) 出现轻微反应,4 名 (17%) 未出现反应。18 名患者在抗生
素治疗后接受 LDN 治疗。临床反应如下:7 名 (39%) 出现明显和中度改善,4 名 (22.2%) 出现轻微改善,5 名
未出现任何改善。两名患者因副作用而不得不停止使用 LDN。
LDN 为治疗 IBS 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 FDA 批准的 IBS 药物通
常疗效不到 40% 至 50%,而安慰剂的疗效率为 30% 至 35%。最后,炎症和肠道通透
性增加在 IBS 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医生的认可,这表明 LDN 在 IBS 治疗中发挥着作
用。
肥大细胞活化综合征
肥大细胞活化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疾病,涉及不受控制的肥大细胞 (MC) 活化,伴有多系
统炎症和过敏症状。46一项针对德国对照组的研究估计,该人群中 MCAS 的患病率为
17%。47在该研究中的患者中,74% 报告一个或多个一级亲属有类似症状。
美国人的 MCAS 间接患病率估计为 1%。48尽管 MCAS 在技术上是一种免疫疾病,MC
控制基因发生突变,但胃肠道是 MC 沉积的常见部位,这些细胞的激活会在肠道和全身
产生症状。413 名患者中有 50% 或更多报告的最常见症状是疲劳、肌痛、结膜炎、鼻炎、
耳鸣、荨麻疹、瘙痒、恶心、胃灼热、呼吸困难、近乎晕厥、头痛、发冷和水肿。49几乎所有器
官系统都可能受 MCAS 影响。50
MCAS 患者通常报告有胃肠道症状,医生经常将其误认为是功能性综合征的症状,
尤其是在患者被诊断为IBS的情况下。51 在 IBS 患者中,MC 释放的介质的局部和全身
影响可导致便秘、腹泻和疼痛。52在一项针对 IBS 患者结肠组织的研究中,组胺和类胰
蛋白酶水平与疼痛相关,MC 与粘膜下神经的距离也是如此。53有趣的是,便秘与神经胶
质细胞附近局部释放 MC 介质有关,
由于 MCAS 患者的病理生理异质性、众多全身症状和诱因、合并症以及对治
疗的不同反应,MCAS 患者的管理面临相当大的挑战。MC 激活的诱因包括压力、食物、酒精、
药物中的赋形剂、感染、微生物群改变、环境刺激(包括热量、化学物质、大气变化、电变化和
气味)以及霉菌暴露。63第一篇证明 LDN 对 MCAS 疗效的出版物研究了一位同时患有
POTS 和 SIBO 的患者。除了接受针对 SIBO 的抗生素治疗外,患者还接受了 LDN 和静脉注
射免疫球蛋白 (IVIg) 免疫治疗。记录显示,POTS、MCAS 和 SIBO 的 40 多种严重症状均有
显著且持续
的反应。IVIg 在自身免疫性神经肌肉疾病中的效用已得到证实,但 POTS 的临床经验相对
较少,而且之前尚未报告过关于 IVIg 在 POTS 和 MCAS 中的数据。在本案例研究中,患者发
现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和利福昔明有显著的益处,但直到她将 LDN 的剂量从 2 毫克增加到
4.5 毫克,她的病情才得到完全改善。其他早期
细丝。54因此,MC 诱发的神经病变可能解释大肠蠕动减弱。胃肠道症状包括麻刺感或烧灼
感、口疮性溃疡、癔球症、胃灼热、吞咽困难、胸痛、恶心、肠道改变、腹胀和腹痛。55消化不良可
能是由于介质引起的伤害感受。56在没有幽门螺杆菌和/或非甾体抗炎药的情况下,胃炎可以
用 MC 介质引起的炎症来解释。57据报道,在肠外阑尾炎的情况下,会出现慢性和急性腹膜
痛,此时可发现局部 MC 沉积增加。58研究表明,在一些被诊断为 IBS 的患者中,MC 导向疗
法取得了成功,这提示了异常 MC 的病理生理作用。59最近有研究表明,SIBO 在 MCAS 中很
常见。60经异常呼气测试确定,139 名 MCAS 受试者中有 30.9% 出现细菌过度生长,而30
个控件中的 10.0%。
MCAS 通常与过度活动型埃勒斯‑丹洛斯综合征 (hEDS) 和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
(POTS) 有关,这两种疾病也都广泛累及胃肠道系统。61 MCAS 无论是单独发生还是与这些
其他疾病同时发生,都会导致严重的胃肠道发病率。
62
本出版物还讨论了我们诊所的经验。我们研究了 27 名 POTS 患者,其中 11 名
接受了 LDN 治疗。这 11 名患者中有 7 名胃肠道症状有所改善,5 名 MCAS 和
POTS 有所改善。在 15 名接受抗生素治疗 SIBO 的患者中,这种疗法帮助 10 名
患者缓解了胃肠道症状,帮助 4 名患者缓解了 POTS 症状。我们没有使用改善量
表。64我们诊所的其他 POTS 患者也观察到了这种情况。
由于 MC 介质和受体众多,目前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控制 MCAS 的所有症状。一种常见的方法是提供
一线治疗,努力识别和避免触发因素,然后开出抗组胺药、维生素 C、维生素 D 和孟鲁司特。许多 MCAS
医生发现 LDN 对他们的一些患者有帮助。在对我自己的一组 MCAS 患者进行审查时,我发现了 LDN
在治疗该病症方面的临床证据。在每天服用 4.5 毫克 LDN 的 116 名 MCAS 患者中,60% 报告有改善,
28% 没有看到任何好处,22% 不得不因副作用停止服用 LDN。
虽然很有价值,但这些数据很难被接受发表,因为涉及的患者同时改变了饮食习惯并使用了几种药
物。这一系列患者可以判断 LDN 治疗是有效的,因为他们在将剂量增加到 4.5 毫克时注意到了临床反
应。其他人在用完 LDN 后,或在停止服药然后重新开始服药后注意到了治疗效果。
服用 LDN 的 MCAS 患者症状得到缓解
沮丧
脑雾
焦虑
恶心
失眠
麻疹
皮疹
痒
过敏
呼吸困难
浮肿
红斑性肢痛症
疲劳
头痛
头晕
腹痛
腹泻
便秘
腹胀
疼痛(关节、神经和肌肉)
结节病结节病是一种特发
性肉芽肿性疾病,最常累及肺部,其特征是 T 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积聚。65这最终会导致肺功能不佳
和66疾病很少局限于肠腔内,如胃,但在系统性结节病病例中,肝脏和脾脏经常受到影响。67泼尼松通常
需要连续使用数月,有多种副作用的风险。英夫利昔单抗会增加感染风险,而免疫调节剂(如类固醇减
些问题,替代治疗方案是可取的。 量剂)不仅有感染和恶性肿瘤的风险,而且起效时间也较晚。鉴于这
一名患者因严重疲劳、结节性皮疹和明显的脾脏和肝脏受累的放射学证据来到我们诊所。我们将结
节病和克罗恩病进行了比较,因为这两种疾病都以淋巴细胞活动不受控制为特征 这是非干酪性肉芽
肿的常见病理特征 并且这两种疾病通常都用类固醇和免疫调节剂治疗。因此,我们给这名患者使用了
LDN,随后她的症状和放射学异常完全消失。68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另外三名患者使用了 LDN,他们
的肺部疾病随后得到改善。
肠系膜脂膜炎
肠系膜是腹腔内的组织,支持小肠和大肠并将其连接到腹部、脾脏和肝脏的后壁。血管和淋巴管也可以
穿过肠系膜。肠系膜脂膜炎 (MP) 是一种非特异性炎症过程,影响肠系膜炎根部的脂肪组织,这是一种
更高级的形式,称为硬化性肠系膜。肠系膜炎,即腹腔内肠系膜增厚,脂肪组织和周围肠系膜血管均发生
退化、炎症和瘢痕形成。70 回缩性肠系膜炎是晚期硬化性肠系膜炎的专有术语,当出现纤维化和 CT 成
像显示“拉入”或束缚现象时。
69
放射科医生在对慢性疼痛进行 CT 扫描时经常会看到非特异性脂膜炎,这种症状可能有临床意义,也
可能没有。
患有脂膜炎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腹痛、恶心和体重减轻。当硬化性肠系膜炎进展到包括肠系膜钙化和纤
维化时,小肠受阻并导致小肠梗阻的风险很大。与非特异性脂膜炎相比,严重的放射学硬化性肠系膜炎
很少见。这是一种排除性诊断;因此,临床医生必须首先排除类癌、转移瘤、纤维瘤、淋巴瘤、慢性感染和
自身免疫性疾病。71
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肠系膜疾病研究回顾了肠系膜脂膜炎患者的 CT 扫描和随访临床数据。72研
究人员回顾了近 150,000 次 CT 扫描作为恶性肿瘤分期评估的一部分,这可能使研究结果产生偏差,
因为这些扫描没有包括患有特发性腹痛的患者。359 名患者患有肠系膜脂膜炎:22.6% 有已知的癌症
病史,5.3% 新诊断出癌症。淋巴瘤是 CT 上与肠系膜脂膜炎相关的最常见癌症 这种关联发生的概率
为 36%。与该病症相关的其他癌症包括前列腺癌和肾癌。359 名患者中有 56 名接受了 CT 随访。80%
的患者肠系膜没有变化,11% 的患者病情恶化,9% 的患者病情好转。 CT 检查结果提示有脂膜炎的
患者中,新诊断为癌症的情况并不常见,但患有相关恶性肿瘤的患者的放射学变化通常保持稳定。
相比之下,另一项对 3,820 名腹痛患者进行的研究发现,94 名患者(2.5%)患有肠系
膜脂膜炎。在这 94 名患者中,48.9% 的患者肠系膜脂膜炎与恶性肿瘤(最常见的是前列
腺癌)共存。73对于每位 MP 患者,都会从整个研究人群数据库中选择两名对照患者,这
些对照患者在第一次 CT 扫描时没有 MP。这些对照患者的年龄和性别相匹配。MP 患者
的共存癌症率略高于对照组患者(n = 188,46.3%)。在 94 名 MP 患者中,MP 被推测
为特发性。在这些患者中,14.6% 的患者在接下来的五年内患上了恶性肿瘤,而对照组的
比例为 6.9%。在存在慢性腹痛的情况下,特发性脂膜炎或肠系膜炎的发生率尚不清楚。
特发性脂膜炎和肠系膜炎的常用治疗方法包括泼尼松、秋水仙碱和免疫抑制剂。74一
例回缩性肠系膜炎病例报告使用黄体酮成功治愈。75手术风险很高。迄今为止,关于硬化
性肠系膜炎的最大规模研究由 Sharma 等人进行,他们回顾了 192 例病例。76这项研究
的并发症包括肠梗阻/肠梗阻/缺血(n = 10,23.8%)和阻塞性尿路病/肾衰竭(n = 10,
23.8%)。
其中 12 名(6.3%)患者因硬化性肠系膜炎相关并发症死亡。
在一项开放标签研究中,Roginsky 等人报告称,三名肠系膜脂膜炎患者中有两名在接受 4.5 毫克纳曲酮治疗
12 周后出现了长期症状反应。77这些患者有炎性肿块,活检显示有炎症、纤维化、脂肪坏死和钙化。这三名患者在 4
周时均有临床改善,但只有两名患者在 8 周时继续显示出益处。使用一种称为肠系膜脂膜炎主观评分的临床评分方
法跟踪改善情况。在研究期间,平均评分从 53 分下降到第 8 周的 21 分。
2020 年,David Kaufman 博士在与 Weinstock 博士的私人交流中指出,他的一位
患有硬化性肠系膜炎的 MCAS 患者在接受肥大细胞定向治疗和 LDN 联合治疗后症状
得到缓解。Weinstock 博士目前有一位腹痛患者,出现全系统症状,经检查发现患有肠系
膜脂膜炎。他的检查结果显示类胰蛋白酶水平较高。LDN 治疗
胃肠道恶性肿瘤
Bihari 博士关于纳曲酮的正式出版物涉及酗酒和艾滋病。
然而,Dalgleish 博士和 Liu 博士很好地描述了已发表的支持使用 LDN 的基础科学的信息79
基本作用机制涉及暂时阻断阿片类受体,导致 OGF(也称为甲硫氨酸脑啡肽、MENK)的反弹产生,
从而调节细胞生长。80已证明纳曲酮诱导的 OGF 产生可降低体外结肠癌细胞的活性。81
甲硫氨酸脑啡肽还通过抑制调节性 T 细胞来增强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的免疫力。82这是 LDN 可能
使癌症患者受益的另一种方式。在其他体外胃肠道癌症研究中,原发性
在网站www.lowdosenaltrexone .org 上,有一篇关于
Bernard Bihari 博士用 LDN 治疗 450 名癌症患者经验的评论。不幸的是,他的经验不是使用 LDN 作为单一疗法或
作为联合疗法一部分的安慰剂对照试验,因此没有发表在同行评议的医学期刊上。
评估了肝细胞癌细胞对外源性OGF的反应。
在《LDN 书》第一卷中, Angus G. Dalgleish 博士和 Wai M.
刘讨论了当时关于使用 LDN 治疗癌症的有限的已发表信息。
需要进一步研究使用 LDN 和检测 MCAS。理论上,LDN 可以减少引起炎症和纤维化的 MC 介
质释放(在肠系膜或远处)。
抗组胺药减轻了他的许多症状,包括腹痛。
观察到它对细胞增殖具有剂量依赖性受体介导的抑制作用。OGF 和 OGF 受体相互作用对细胞数量
的机制与抑制 DNA 合成有关,而不是与凋亡或坏死途径有关。最近的一项研究检查了 MENK 处理
的胃癌细胞以及这种内啡肽对动物胃癌的抗肿瘤作用。84 MENK 通过阻止细胞周期和诱导细胞
癌症。
83
78
关于人类胃肠道恶性肿瘤,支持 LDN 疗效的临床研究包括一名胰腺癌患者,该患者对 LDN
联合静脉注射 α‑硫辛酸 (ALA) 有反应。85其中一名患者在被告知患有晚期癌症后存活了四年
多。在对该病例报告的后续报道中,作者描述了另外三例以相同方式治疗患者的病例研究。最初
的患者两年半后还活着,另外三名患者情况良好,其中一名患者出现肝脏转移性疾病,在最初诊
断后三年还活着。86 ALA 的作用包括减少氧化应激、稳定 NF‑kB 和刺激细胞死亡活性。
直接施用甲硫氨酸脑啡肽为 LDN 对胰腺癌的益处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宾夕法尼亚州⽴
大学的研究人员对 24 名晚期胰腺癌标准化疗失败的患者进行了一项前瞻性开放标签试验。患
者每周接受 250 μg/kg OGF 静脉输注治疗。对照组为 166 名年龄相仿、化疗失败并出院接受
临终关怀的患者。与对照组相比,接受 OGF 治疗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增加了三倍。接受 OGF 治
疗的患者中,62% 的肿瘤大小稳定或缩小。
死亡。LDN 增加 MENK 的能力代表了抑制癌症的一种潜在重要作用机制。
87 癌症。
在 Schwartz 等人的一项前瞻性研究中,LDN 与 ALA 和羟基柠檬酸联合用于 10 名晚期
癌症患者,其中 4 名患有胃肠道癌症(结肠癌、食道癌和胆管癌)。88在这 10 名患者中,2 名如
预期在两个月内死亡,2 名需要常规化疗,6 名癌症稳定或进展缓慢。一名出现肝转移的患者对
化疗没有反应。添加 LDN 后,患者的肝病变稳定了 9 个月。之后病变进展。一名结肠癌患者的肝
转移在化疗后进展,随后两个月的 LDN Rx 治疗失败。一名转移性食道癌患者在化疗后复发。使
用 LDN Rx 作为单一疗法最初失败,但添加新的化疗导致肿瘤缩小。最后,一名胆管癌患者
尽管积极化疗,癌症仍旧进展。添加了 LDN Rx,CT 扫描显示接下来的三个月内没有进一步进展。
在一项以色列的研究中,两名患有肝母细胞瘤的儿童因手术切除不完整而接受 OGF/LDN 治疗,
而不是化疗,因为化疗是禁忌的或不能耐受的。89在病例报告时,每名儿童分别在 10 年后和 5 年后均
无病且无症状。
作为一名胃肠病学家,Weinstock 博士在癌症和 LDN 治疗方面的经验有限,因为一旦患者被转诊
给肿瘤学家,他就不再担任主要角色。他亲自为四名癌症患者开出了 LDN。一名结肠癌患者需要切除肝
转移灶,然后进行化疗,而另一名患者由于淋巴结阳性而接受了术后化疗。到目前为止(手术后两年),
两人的病情都得到了缓解。一名患有长期克罗恩病的患者,其淋巴瘤被认为是由于之前接触硫唑嘌呤
所致,由于 LDN 作为单一疗法,她的克罗恩病得到了完全控制;过去 10 年,她一直处于深度缓解状态
(她接受了 1 年的化疗)。最后,一名患有瓦尔登斯特伦淋巴瘤的女性在常规化疗后预防性地服用
LDN,过去四年一直处于完全缓解状态,情况良好。这种恶性肿瘤的复发率很高 90% 的患者会复发。
尽管令人鼓舞的是,科学家和临床医生越来越多地评估 LDN 在癌症治疗中的应用,但该领域仍需要
进一步研究。90
结论
LDN 有可能恢复多种胃肠道疾病的肠道健康。使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的高质量研究是理想的
选择。然而,在获得此类试验的资金之前,持续的临床使用和病例系列报告将使许多患者受益。
皮肤病
有人提出 LDN 可有助于治疗多种皮肤病,包括斑秃及其变体、特应性皮炎、自身免疫相关皮肤病(硬化症/硬斑病、
狼疮、皮肌炎等)、天疱疮、类天疱疮、银屑病、扁平苔藓、硬化性苔藓、瘙痒症、结节性痒疹、Hailey‑Hailey 病、自身免
疫性瘢痕性脱发、白癜风和坏疽性脓皮病等。目前,文献中很少有报告证明 LDN 对皮肤病患者有效。现有的报告包括
案例研究、病例系列和评论。本章将介绍有证据表明 LDN 有益的疾病,包括瘙痒、Hailey‑Hailey 病、毛发扁平苔藓和
银屑病。它将回顾已知的与皮肤相关的阿片类受体的知识以及已知的 LDN 作用机制如何改善皮肤病。
所有慢性皮肤病都与炎症和/或免疫系统功能障碍有关。与皮肤、头发和指甲相关的疾病的炎症和免疫失调的具体模
式不同,但许多疾病有相似的途径。低剂量纳曲酮 (LDN) 已被证明可以在多个层面影响炎症和免疫失调。这一点,加
上非常低的副作用,使其成为各种皮肤病患者的理想选择。
苹果博德默,马里兰州
四
虽然我们通常认为阿片类受体主要存在于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但它们在免疫系统、皮肤和其他各种器
官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阿片类受体的主要三种类型是 mu、delta 和 κ,它们都是跨膜受体,与多种调节酶有
关,包括腺苷酸环化酶(一种普遍存在的细胞调节酶)和钙通道,而钙通道对于维持所有细胞内的钙梯度以
控制多种细胞过程至关重要。1 Mu、delta 和 κ 阿片类受体以不同的浓度存在于表皮角质形成细胞、表皮黑
素细胞、成纤维细胞和周围神经纤维中。2在皮肤中,阿片类受体主要集中在基底层和基底层上方,但可在整
个表皮中找到。3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在几种皮肤病中表皮 mu 受体的表达发生了改变。这些包括牛皮癣、基
底细胞癌和慢性伤口。4这支持了阿片受体和阿片类药物在表皮细胞增殖和分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数据。5
阿片类受体存在于角质形成细胞表面,有助于调节细胞间粘附和角质形成细胞迁移。6它们还被证明参与
维持对角质层完整性至关重要的蛋白质(包括外皮蛋白、兜甲蛋白和丝聚蛋白)。7阿片类药物和阿片类受
体在皮肤中发挥的其他重要作用包括调节疼痛和瘙痒(尤其是在慢性皮肤病中)、黑色素生成和皮脂生成。
特别是,μ 受体似乎也参与了黑素细胞增殖。8此外,阿片类药物及其受体调节参与免疫反应的多种细胞的功
能,包括树突
状细胞、巨噬细胞、肥大细胞、淋巴细胞和多形核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
9 纳曲酮的一个特别有趣的特点是它也可以与其他受体相互作用。 Toll 样受体 (TLR) 家族是植物和动物
中发现的一组蛋白质,在免疫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受体帮助身体识别致病微生物,启动适当的免疫反应,并
在细菌、酵母、真菌和
12 然而,持续使用可能会导致皮肤永久性变薄和脆弱。
瘙痒感在许多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中很常见。此外,瘙痒还有许多系统性原因,包括甲
状腺异常、肝病、肾病、癌症、血液学异常和神经系统疾病。基本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
大大缓解瘙痒,应尽早评估和解决。无论原因如何,通过适当的沐浴和保湿保持良好
的皮肤水分、尽量减少接触刺激物和适当的压力管理对于缓解瘙痒感至关重要。当瘙
痒是局部的,局部治疗通常就足够了。一旦解决了适当的皮肤水分问题,局部类固醇
是皮肤炎症的主要一线治疗方法。长期使用外用类固醇会导致皮肤萎缩 皮肤表面
出现细小的皱纹。如果及早发现并停止使用类固醇,表皮通常会自我再生并恢复。
病毒。10免疫系统与炎症密切相关,因此通过与这些重要的免疫系统受体相互作用,受体配体可以影响炎症途
径。研究表明,纳曲酮可通过与 TLR‑4 相互作用降低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a) 以及其他炎症化合物,包括白细胞
介素 (IL) 6、一氧化氮和核因子 κB (NF‑kB)。11纳曲酮很可能也会与其他 TLR 相互作用。鉴于我们对纳曲酮和
LDN 作用机制的了解,很明显它可以在多个点影响炎症和免疫系统功能,使其在皮肤病的治疗和管理中具有极
强的潜力。
外用辣椒素是一种从辣椒中提取的物质,也已被证明能有效缓解瘙痒。经常使用
时,它会消耗神经末梢中的 P 物质 一种已知能传递瘙痒感的神经肽。因为辣椒素最
初会促进神经元释放
局部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他克莫司和吡美莫司)、局部抗组胺药和局部麻醉药
也有助于控制瘙痒,且不会产生萎缩的潜在副作用。
痒
光疗法通常用于治疗特应性皮炎和牛皮癣等炎症性皮肤病,但即使在没有炎症的情况下也可以有效缓解
瘙痒。光疗法缓解瘙痒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但据认为会影响内源性阿片类药物系统、改变表皮细胞因子
并调节皮肤肥大细胞和神经的活性。广泛而严重的瘙痒可能需要全身
用药。口服抗组胺药经常使用,但除了荨麻疹和肥大细胞疾病外,其益处尚不清楚。然而,当瘙痒在夜间
最明显和/或干扰睡眠时,镇静抗组胺药可能非常有用。16 抗抑郁药,如米氮平、多塞平和选择性血清素再
摄取抑制剂(SSRI:帕罗西汀、氟伏沙明和舍曲林)也可用于控制瘙痒。这种影响可能是由于血清素和组胺
水平的改变。17抗惊厥药加巴喷丁和普瑞巴林通常用于治疗全身性瘙痒,对神经病变相关的瘙痒尤其有
用。18沙利度胺具有免疫调节和神经调节特性以及抗炎作用,使其成为患有慢性顽固性瘙痒患者的一种选
择。这是一种具有显著潜在副作用的药物,只有在其他选择都用尽时才应使用。
19
纳曲酮和瘙痒
研究发现,与瘙痒相关的慢性皮肤病(包括特应性皮炎、结节性痒疹和慢性单纯性苔藓)患者的 μ‑阿片受
体减少,这表明纳曲酮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具有潜在益处。20口服纳曲酮 50 毫克/天或以上剂量传统上
用于治疗各种不同类型的瘙痒。21一篇文献综述发现,在治疗与特应性皮炎、牛皮癣、慢性单纯性苔藓、结
节性痒疹、蕈样肉芽肿、皮肤 B 细胞淋巴瘤、尿毒症性瘙痒、胆汁淤积性瘙痒、水源性瘙痒和原因不明的瘙
痒相关的瘙痒方面,这种较高剂量的纳曲酮具有不同的效果。
起源。22这种高剂量方案的好处是,保险通常会覆盖这些剂量,但不涵盖低剂量胶囊的配制。当成本是一个
问题时,尝试每天 50 毫克至 100 毫克的纳曲酮是合理的。在这些剂量下,应监测肝功能测试。
局部纳曲酮和瘙痒
外用 1% 纳曲酮已被证明对特应性皮炎和严重瘙痒患者有效。一项包括 40 名患者的安慰剂对照交叉研究
发现,接受外用纳曲酮治疗的患者中 70% 的瘙痒显著减少,而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中 40% 的瘙痒减
少。安慰剂组的高反应率表明皮肤补水对瘙痒有显著影响。这项研究涉及 40 名患者中的 11 名在使用外用
纳曲酮之前和之后的皮肤活检。使用外用纳曲酮后,皮肤中 μ‑阿片受体的染色增加。
虽然样本量不足以得出任何具体结论,但似乎 μ‑阿片受体染色强度与瘙痒感减弱相关。23
低剂量纳曲酮和瘙痒LDN 对控制瘙痒非常有用。此外,当甲状腺异常导
致瘙痒时,LDN 可用于治疗潜在的甲状腺疾病(参见LDN书第一卷第 5 章)。24有两篇已发表的病例系
列研究了 LDN 对特定皮肤病相关瘙痒的有效性。一个病例系列包括三名患有系统性硬化症和疾病相关瘙
痒的患者。这三人均在睡前服用 2 毫克纳曲酮,持续一个月。
然后每周增加 1 毫克剂量,最高可达 4.5 毫克(最后一周剂量增加 0.5 毫克)。三名患者中,一名维持 2 毫
克剂量,而另外两名达到目标剂量 4.5 毫克/天。三名患者的瘙痒感均显著减少,皮肤柔软感增强,生活质量
改善。25另一系列研究描述了两名皮肌炎相关瘙痒患者,他们每天接受 5 毫克纳曲酮治疗。两名患者的症状
均完全缓解,其中一名在六周内缓解。26
此外,已证明 LDN 可以改善与扁平苔藓和牛皮癣相关的瘙痒,以及这些疾病的其他症状
(有关详细信息和参考资料,请参阅后续章节“低剂量纳曲酮和扁平苔藓”和“低剂量纳
曲酮和牛皮癣”)。
在我的个人临床经验中,我已看到使用局部 1% 纳曲酮治疗局部神经性瘙痒(包括与
结节性痒疹和背部感觉异常相关的瘙痒)的明显益处。我使用 LDN 治疗病因不明的全身性
瘙痒的经验好坏参半。我通常从每天 50 毫克开始,如果四个月后没有看到效果,我会改用
低剂量方案。当我使用 LDN 治疗特定的炎症性皮肤病(特别是牛皮癣、扁平苔藓和特应性
皮炎)时,我确实看到瘙痒症状有所改善。
Hailey‑Hailey 病
海利‑海利病(又称家族性良性天疱疮)是一种罕见的水疱性疾病,由于钙水平改变,表皮
角质形成细胞无法维持细胞间连接。海利‑海利病已知是由 ATP2C1 基因的多种突变引起
的。
该基因编码一种蛋白质,负责维持适当的细胞内钙水平,这对于调节细胞生长和迁移以及
细胞间粘附至关重要。虽然 Hailey‑Hailey 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但经常发生新的
突变。
海莉‑海莉病通常在青春期前后出现临床显著症状,但也有罕见的青春期前儿童患病报
告。27患有此病的人会出现松弛性水疱,导致疼痛性糜烂和浸渍,最常见于腋窝、腹股沟、乳
房下区域和颈部侧面。患处细菌、真菌和酵母菌感染很常见,往往会加重病情。加剧海莉‑海
莉病的其他因素包括摩擦、高温、汗水和紫外线辐射。28
由于 Hailey‑Hailey 非常罕见,因此关于治疗的文献有限。患者和医护人员应强调尽量
减少加重因素、控制炎症以及预防和适当治疗继发感染。减肥、穿宽松的衣服、避免过热和
避免晒伤可以大大有助于
预防爆发。稀释漂白剂浴(½ 杯/120 毫升 6% 次氯酸钠)或冲洗(1 茶匙漂白剂兑 1 加仑/4 升水)和抗菌清
洁剂(4% 洗必泰)对于减少患处的微生物定植以防止继发感染非常重要。局部类固醇和局部钙调磷酸酶抑制
剂可以帮助控制炎症,但需要谨慎使用以避免增加微生物定植。局部抗生素和抗真菌药物通常也是必要的。一
旦发生感染,可能需要口服抗生素和/或抗真菌药物。
已使用且效果不一的全身性药物包括环孢菌素、甲氨蝶呤、阿维A和口服他克莫司。有趣的是,一个病例系
列描述了三名患有 Hailey‑Hailey 的人,他们在开始每天口服 300 毫克氯化镁治疗后,四周内病情迅速好转。
人们认为这可能有助于调节角质形成细胞的细胞内钙水平,从而改善细胞间粘附。29控制出汗的程序选项包括
局部肉毒杆菌毒素、受影响的间擦区域的手术切除、受影响区域的 CO2激光消融以及用于消融汗腺的电子束
辐射。这些程序很痛苦,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疤痕。30
低剂量纳曲酮和 Hailey‑Hailey 病Hailey‑Hailey 病患者已成功使用低剂量纳曲酮进行治疗。
LDN 对这种疾病
的有效性被认为是由于其抗炎活性以及其通过 TLR 通路稳定细胞内钙的能力。31有四例 Hailey‑Hailey 病
患者病例系列,均使用 LDN 进行治疗。第一例病例系列包括三名患有顽固性 Hailey‑Hailey 病的患者。所有药
物均已停止,患者每天服用 1.5 至 3 毫克纳曲酮。经过三至四个月的治疗,每位患者的临床和症状改善率均达
到 80% 至 90%,且无明显不良反应。32第二例病例系列包
括三名患有长期 Hailey‑Hailey 病的患者,他们每天服用 3 毫克至 4.5 毫克纳曲酮。所有
三位患者在接受治疗两个月内皮肤病变明显消失。随后停止治疗,所有患者均复发。
重新开始使用 LDN,患者再次痊愈。33第三个病例系列包括三名患有长期疾病的患者。有趣的是,在
这个系列中,只有一名患者接受了低剂量方案治疗。该患者每天服用 4.5 毫克,并在 18 个月时痊愈。
第二名患者在两个月时完全痊愈,每天服用 12.5 毫克(较高剂量是由于保险覆盖)。痊愈后,她停止
服用纳曲酮,病情再次复发。她重新开始服用纳曲酮,每天服用 4.5 毫克,再次取得好转。第三名患者因
同时出现臂桡侧瘙痒症,每天服用 50 毫克,但无反应。34
最大的病例系列包括 14 名 Hailey‑Hailey 患者,他们在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1 月期间接受了纳曲酮治
疗。
他们的起始剂量从 1.5 毫克到 6 毫克不等。5 名患者维持在低剂量范围内,另外 9 名则增加到每天
25 毫克到 50 毫克之间。14 名患者中只有 2 名持续好转。有趣的是,这些患者维持在每天 3 毫克和
4.5 毫克的剂量。6 名患者最初有所好转,但随后复发。其中,只有一名患者维持在每天 3 毫克的最佳
剂量范围内,没有增加剂量。其他五名患者的剂量增加到每天 6 毫克到 12 毫克之间。在没有好转的
6 名患者中,两名患者从一开始就以每天 6 毫克的剂量开始,一名患者的日剂量增加到 50 毫克,另一
名患者的日剂量增加到 12 毫克。其中一名无反应患者以 1.5 毫克开始并保持此剂量,该剂量处于炎
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有效剂量的低端。其余三名无反应患者以每天 3 毫克的剂量开始。一名患者维持
该剂量,一名患者增加至每天 12 毫克,另一名患者增加至每天 50 毫克。四人出现恶心和头晕的副作
用,两人因这些副作用停止使用纳曲酮。本系列的随访时间为 15 至 54 周不等。35论文中没有明确说
明每位患者服药时间、剂量调整如何确定以及每种特定剂量在增加之前维持了多长时间。虽然很难从
这篇论文中得出确切的结论,但它确实支持了以下假设:更高的剂量
纳曲酮对这种病症的效果不如低剂量方案。
除了这四个病例系列,还有一些病例报告支持在 Hailey‑Hailey 中使用 LDN。一份报告描述了
一名患有 20 年顽固性 Hailey‑Hailey 病史的女性,她在每天服用 1.5 毫克纳曲酮仅 26 天后就获
得了临床清除。36另一份报告证明了 LDN 联合口服镁的有效性,37最后一份报告描述了一名患者
使用 LDN 清除,然后使用氯胺酮和苯海拉明的局部组合维持清除。38
虽然我没有使用 LDN 治疗 Hailey‑Hailey 病的临床经验,但考虑到这种疾病的发病率高、缺乏
一致有效和安全的治疗方法、令人鼓舞的益处支持以及 LDN 的安全性,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对
Hailey‑Hailey 病患者进行早期治疗,剂量为每天 1.5 毫克至 4.5 毫克。
扁平苔藓 (LPP)
毛发扁平苔藓 (LPP) 是一种瘢痕性脱发疾病,最常见于绝经后女性。39在这种情况下,毛囊炎症会
导致受影响的毛囊永久性瘢痕化。临床上,炎症阶段会出现毛囊周围丘疹和红斑。
这通常与灼热、瘙痒或刺痛的症状有关。
随着病情的进展,毛囊会留下疤痕,导致头发永久脱落。此时症状通常会消退,患处会因疤痕组织的
形成而变得光滑凹陷。
扁平苔藓有几种典型表现。典型表现为不规则形状的受累区域,主要在头顶,但也可能延伸到头皮的
其他区域。在晚期阶段,疤痕区域可能融合成一个有趣的头皮脱发模式网络。在额纤维化脱发 (FFA)
中,受影响的毛囊沿额发际线形成一条带。在晚期阶段,这种类型可能导致额发际线损失多达几英
寸。眉毛受累很常见,睫毛也可能受累,但相对少见。最后一种表现称为 Graham‑Little‑Piccardi‑
Lasseur 综合征。这包括斑块状疤痕性脱发
头皮上的扁平苔藓、腋窝和腹股沟的非瘢痕性脱发以及身体和/或头皮上的毛囊性扁平苔藓。毛囊性扁平
苔藓由角化过度的毛囊性丘疹组成,通常伴有紫色至褐色的色素沉着。无论临床类型如何,扁平苔藓的病
程都非常难以预测。虽然扁平苔藓不会导致完全秃顶,但脱发可能非常严重,并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和情
感困扰。40扁平苔藓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它似乎是一种自身免疫相关的炎症性疾病,专门针对毛囊中存
在毛囊干细胞的区域。激素似乎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它们如何影响这种情况尚不清楚。 LPP 最常发生在
绝经后女性身上,在某些情况下,抗雄激素药物治疗可能会有所帮助。41 LPP 患者患甲状腺疾病的风险
明显较高,甲
状腺功能减退症是最常见的甲状腺疾病。42对 LPP 患者进行甲状腺疾病筛查并进行适当治疗非常
重要。不幸的是,甲状腺功能的正常化不会影响这种疾病的进程。
治疗 LPP 可能相当具有挑战性。LPP 往往会在数月或数年内自行消失。然而,该病的病程往往不稳
定,最终结果难以预测。
此外,患者需要了解,一旦出现毛囊瘢痕,就无法让受影响区域的头发重新长出来。
治疗的目标应集中于控制症状和减缓或停止炎症过程,以尽量减少永久性疤痕的进展。
LPP 的初始治疗通常包括使用类固醇,可以局部涂抹、注射到患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高效类固醇通常每
天使用两次 (BID),持续长达四个月。根据有限的数据,这似乎对 50% 到 60% 的人有帮助。43病灶内注射类固
醇也可能有帮助。曲安奈德每四到六周皮内注射到患处,浓度为 5 mg/ml 或 10 mg/ml。皮肤萎缩是使用类固
醇的主要风险,也是坚持使用较低浓度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尤其是在前额发际线。44
如果这些措施在三到四个月内没有效果,通常会考虑口服药物。口服类固醇可用于控制快速进展
的疾病。病例报告显示结果好坏参半,在考虑此选项时,需要与患者仔细权衡其利弊。45羟氯喹因其免
疫调节活性而常用于 LPP 治疗,剂量为每天两次,每次 200 毫克。似乎大约 15% 到 25% 的人在四
个月内有良好的反应。46其他使用效果有限的全身药物包括环孢菌素、霉酚酸酯、甲氨蝶呤、维甲酸、利
妥昔单抗、吡格列酮和抗雄激素,包括非那雄胺、度他雄胺和米诺地尔。
低剂量纳曲酮和地衣
浮毛虫
有一个病例系列研究了 LDN 和 LPP,其中包括四名患有难治性 LPP 的患者。这些患者每天服用 3 毫
克纳曲酮。四人均出现瘙痒减轻、活动性疾病临床证据减少和病情进展减缓的情况。在头两个月内就
出现了疗效,药物耐受性良好,没有不良事件。47
我曾为几位 LPP 患者使用过 LDN,大多与局部或病灶内注射类固醇和/或羟氯喹联合使用。我并
没有看到活动性炎症临床证据消退方面的显著效果,但许多患者报告称,使用 LDN 后,瘙痒、灼热和
刺痛症状有所减少。这表明 LDN 对炎症过程有影响。LDN 需要几个月才能起效,而且这种疾病具有
自限性,因此很难评估包括 LDN 在内的任何治疗的效果。
牛皮癣牛皮癣是一
种全身炎症性疾病,影响约 3% 的美国人。它可能与银屑病关节炎、代谢综合征、肥胖、糖尿病、心血管
疾病和抑郁症有关。48牛皮癣的发病机制是多因素的,包括遗传和环境因素。多达 40% 的牛皮癣患
者患有
家族有牛皮癣病史,并且已确定有几种基因在该病的发展中发挥作用。49环境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吸烟、饮酒、肥胖和压力都与牛皮癣和牛皮癣发作有关。药物(包括锂、β受体阻滞剂、抗疟药和 TNF‑
alpha 抑制剂)可引发牛皮癣。最后,已知感染在牛皮癣中发挥作用。链球菌感染是点滴状牛皮癣的常
见诱因,而 HIV 已知可引发和/或加剧牛皮癣。
目前对该病发病机制的认识是:银屑病是一种免疫调节紊乱和异常炎症。
可见表皮角质形成细胞分化改变,角质形成细胞过度增殖,表皮转运时间减少(从基底层到最顶层的
正常转运时间从约 27 天减少到 3 或 4 天)。这些异常可归因于细胞内钙波动异常。细胞内钙水平正
常化是可能影响此病症的一种方式。50此外,已知银屑病中多种炎性细胞因子升高,包括 TNF α、干扰
素 α、白细胞介素 1、6、17 和 23 等。51临床上,银屑病可表现为几种模式。最常见的是慢性斑块性银屑
病(也称为寻常型银屑病)和点滴状银屑病。脓疱性银屑病和红皮病型银屑病更严重,但表现较少。慢
性斑块性银屑病和点状银屑病均表现为边界清晰的红斑,表面有银色鳞屑。慢性斑块性银屑病的斑块
往往较大且较厚。
它们通常影响头皮、肘部、膝盖、脐部和臀沟,但可以影响任何皮肤表面。反向银屑病是一种亚型,其中擦
擦区域优先受到影响。点滴状银屑病有类似的表现,但斑块往往较小且分布更分散。这种类型通常发
生在上呼吸道疾病之后,尤其是链球菌性咽喉炎。脓疱性银屑病表现为浅表脓疱和鳞屑,基部为红斑。
红皮病型银屑病包括大面积红斑和鳞屑,覆盖大部分体表面积。
这两种变体都可能突然发病,并可能与全身表现有关,包括不适;发烧;发冷;肾脏、肝脏、呼吸和心血管
功能障碍;电解质异常;体液
损失、蛋白尿和感染。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及时处理,患者可能需要住院治疗以控制全身
并发症。
银屑病关节炎最常见于皮肤银屑病,但可以单独发生。与许多其他形式的自身免疫
性关节炎不同,银屑病关节炎是一种进行性破坏性疾病,可能导致永久性关节损伤,需
要更积极的治疗。由于关节炎有很多种类型,因此对受影响关节进行适当的影像学检查
和风湿病专家的参与可能会有所帮助。52银屑病是一种慢性疾病,其特点是病程波动。
重要的是要让患者知道银屑病无法治愈,并帮助他们设定现实的期望。在制定治疗计划
时,需要考虑患者的偏好和每个患者可以接受的皮肤受累程度。银屑病有多种治疗选
择,包括局
部治疗和全身治疗。重要的是让患者明白,即使他们确实痊愈了,他们也可能会经历
突破性的发作,他们可能需要调整治疗方案。
优化皮肤补水是治疗牛皮癣的第一步。这对于减少瘙痒尤为重要,并且有助于预防/
限制牛皮癣的发作。
局部类固醇是治疗局部性牛皮癣的一线药物。具体类固醇和浓度取决于治疗部位和斑
块厚度。快速耐受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药物的反应性降低,在牛皮癣环境中使用局部
类固醇时常见。间歇性用药假期和/或将类固醇与其他局部药物结合使用有助于避免这
种现象。维生素 D 类似物卡泊三烯对角质形成细胞具有抗增殖作用,常用于治疗牛皮
癣。53其他非类固醇选择包括焦油和类视黄醇。局部钙调磷酸酶抑制剂(如他克莫司和
吡美莫司)对面部或间擦部位的病变尤其有帮助。
光疗法是一种有效的非药物治疗牛皮癣的方法。窄带 UVB 治疗对皮肤具有抗增殖
和抗炎作用,通常对治疗牛皮癣非常有效。54治疗需要每周进行两到三次
每周一次,耐受性非常好。主要缺点包括寻找光疗装置和安排时间的挑战。
严重或广泛分布的银屑病可能需要全身免疫调节药物,包括甲氨蝶呤、口服维甲酸或环
孢菌素。此外,越来越多的生物免疫调节剂被开发出来,以解决银屑病患者中某些特定炎症细
胞因子升高的问题。这些包括 TNF‑alpha 抑制剂(依那西普、英夫利昔单抗、阿达木单抗、赛
妥珠单抗)、白介素 17 (IL‑17) 抑制剂(secukinumab、ixekizumab、brodalumab)和
IL‑23 抑制剂(ustekinumab、guselkumab、tildrakizumab、risankizumab)。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情绪问题在银屑病患者中很常见,其中最常见的是抑郁症。许多患有
银屑病的人的生活质量通常很差,因此,让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或治疗师参与进来,帮助
患者应对这种疾病的社会心理方面是很重要的。55
低剂量纳曲酮和牛皮癣
虽然 LDN 在治疗牛皮癣方面的有效性证据有限,但 LDN 是一种合理的治疗方法,因为它具
有抗炎活性,并有可能调节角质形成细胞迁移和分化。目前文献中有三份病例报告。一份报告
涉及一名 60 岁的女性,患有中度弥漫性斑块状牛皮癣,涉及其体表面积的 10%。她每晚接
受 4.5 毫克 LDN 治疗。在此期间未使用任何其他药物。三个月后,她的牛皮癣病变明显改善。
六个月后,她的体表面积受累减少到 1%,牛皮癣面积严重程度指数 (PASI) 从 7.2 降至 0.9。
LDN 耐受性良好,没有副作用。56在另一份报告中,一名 75 岁的男性患有点滴状牛皮癣,每
天服用 4.5 毫克 LDN 成功治愈。
四周后,他的病变数量和严重程度均有所减少,瘙痒感也明显减轻。LDN 耐受性良好,唯一报
告的副作用是皮肤干燥。57最后,有一份报告称,一名 38 岁的女性使用甲氨蝶呤后牛皮癣得
到了充分控制。由于副作用,她停止服用该药物,
病情迅速发展为红皮病型银屑病。她出现大面积银屑病斑块,伴有水肿、渗出、发冷和严重瘙痒。她不想服用传
统药物,所以开始每天服用 4.5 毫克的 LDN,同时每 12 小时服用一次羟嗪,以帮助控制瘙痒,并使用胶体燕
麦保湿剂。第 9 天停用羟嗪。到第 10 天,她的水肿有所改善,瘙痒也减轻了。
到第 20 天,她的水肿和红斑持续改善。三个月后,她的病情完全好转,六个月后病情仍处于缓解期。58
我个人使用 LDN 治疗牛皮癣的经验非常积极。我最显著的例子是一位老年妇女,她的 75% 体表面积被
厚厚的牛皮癣斑块覆盖。她曾患过两种不同的实体器官癌症,因此不适合接受全身免疫抑制治疗或较新的生
物免疫调节药物。由于皮肤受累严重,外用药物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而光疗法在过去对她的帮助也不够。她
开始服用 1.5 毫克 LDN,每晚服用,我们在三周内将剂量增加到 4.5 毫克。四个月内斑块消失,她只剩下黄斑
红斑,六个月内完全消退。她已经保持干净超过两年,并且对 LDN 的耐受性良好,没有副作用。这位患者的故
事很特别。根据我的经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看到这种程度的清除并不常见。通常,需要仔细调整剂量并管理
预期。我确实发现 LDN 对我的大多数牛皮癣患者都有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病情完全好转。有时人们
会注意到他们在冬天不会那么频繁地发作,即使发作也没有那么严重,或者他们的皮肤更容易通过局部疗法
进行治疗。我的许多患者都表示他们感觉好多了,他们的压力、焦虑和/或抑郁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一个严重的
问题。这种压力的减轻对他们的皮肤病肯定也有积极的影响。我告诉患者 LDN 是一种慢作用药物,建议他们
承诺使用一年后再判断其有效性。我还告诉他们,可能需要仔细调整剂量才能从这种药物中获得最大益处。
博德默博士剂量珍珠
对于患有自身免疫性和炎症性皮肤病的患者:
睡前服用 1.5 毫克,持续一周。
睡前服用 3 毫克,持续一周。
之后睡前服用 4.5 毫克。
六个月后评估进展。如果未达到预期控制效果,则将剂量减至每天 3 毫
克,然后每两到四个月缓慢增加 0.5 毫克,直至达到 4.5 毫克。
对于患有焦虑和/或抑郁症的患者:
每晚 0.5 毫克,持续一至两周。 每天
两次 0.5 毫克,持续一至两周。 早
上 0.5 毫克,晚上 1 毫克,持续一至两周。 此后每天两次 1 毫
克。
如果同时出现炎症性皮肤病,则让患者的剂量保持在 1 毫克 BID 持续
四个月,然后慢慢增加 0.5 毫克的增量,使总剂量接近 3 至 4.5 毫克。
对于甲状腺异常患者或正在服用甲状腺替代药物的患者:
睡前服用 0.5 毫克,持续一周。 睡
前服用 1.0 毫克,持续一周。 睡
前服用 1.5 毫克,持续一周。
三个月后重新检查甲状腺功能,然后每两周继续增加 0.5 毫克,直至每
天 3 至 4.5 毫克。
每三个月重新检查一次促甲状腺激素 (TSH),直到达到稳定的剂量。
建议患者注意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症状,包括心悸、焦虑、睡眠困难、出
汗增多、呼吸急促、体重减轻和震颤。
结论显然,关于 LDN
治疗皮肤病的有效性的数据有限。鉴于已知的作用机制,
局部或全身性 LDN 应该有助于治疗多种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皮肤病。除了上面讨论的皮肤病外,我还成功地使
用 LDN 治疗了斑秃、白癜风和局限性硬斑病。我还对有黑色素瘤病史的人使用 LDN,以潜在地预防新黑色素
瘤的发展并限制复发/转移。此外,有令人鼓舞的数据表明 LDN 可能对治疗慢性伤口和糖尿病相关皮肤病有
效。59由于安全性和低副作用,LDN 可以被视为初始选择 尤其是对于那些不能使用标准药物或想避免一些
常用于治疗慢性皮肤病的药物毒性的人。
在决定包含 LDN 的治疗计划时,筛查甲状腺疾病和阿片类药物的使用情况(处方药和消遣性药物)非常
重要。还必须考虑患者的其他健康问题 如果他们患有纤维肌痛、炎症性肠病、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或抑郁/焦
虑,LDN 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希望随着 LDN 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接受,将会收集更多更好的数据关于其在治疗皮肤病方面的应用。
‑五‑
帕金森病
克里斯汀·辛格勒(Kirsten Singler), NMD
帕金森病 (PD) 是最常见的神经肌肉疾病之一,这一大类疾病的共同点是身体的神经和
肌肉系统功能障碍。这一类别包括多发性硬化症 (MS)、多发性肌炎、遗传性痉挛性截瘫、
兰伯特‑伊顿综合征、肌营养不良症、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ALS) 等疾病,以及病因和机制
各异的其他疾病过程。这一类别中的大多数疾病尚未得到充分了解,其病因仍不清楚。一
些疾病具有遗传因素,而另一些则被认为是由自身免疫反应、病毒、毒性暴露或肿瘤引起
的。虽然其中一些疾病在儿童时期出现,但许多疾病(如 ALS、MS 和帕金森病)是在成年
期发展起来的。
症状通常包括肌肉无力、运动功能减弱、麻木、疼痛、刺痛、痉挛、肌肉僵硬、肌肉萎缩和震
颤。治疗通常包括免疫抑制剂、解痉药、抗抑郁药和止痛药。虽然标准治疗可以缓解部分
症状并延缓病情进展,但大多数此类疾病被认为是不可逆的。患者及其护理人员经常寻
求替代和/或联合治疗,希望改善生活质量。
我遇到安娜时就是这样的,她当时 70 多岁,被诊断患有帕金森病并接受治疗。我们第
一次见面时,安娜坐着轮椅进来,由看护人推着,因为她无法
尽管安娜严格遵守神经科医生开的药物,但她仍无法独⽴行走。在咨询过程中,她的监护人一直在说话,因为
安娜几乎哑了。她的声音听不见 比耳语还要轻。她不能皱眉或微笑,因为她无法控制面部肌肉。简而言之,
10 年的止痛药和息宁美并没有充分控制她的症状。她的家人希望探索辅助治疗,以期改善她的众多症状。他
们一直在研究综合医学,尽管持怀疑态度,但仍想了解更多。
功能医学很复杂,涉及对整个人的治疗。它通常需要改变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以及患者愿意尝试新疗
法并积极参与治疗。治疗过程可能很艰难,尤其是在面对慢性病进展时。由于安娜身体虚弱,她需要孩子们的
帮助来适应新疗法并调整家中的习惯。我向安娜的护理人员解释说,与专注于病理的对抗疗法相比,补充医学
旨在评估和治疗整个人。理解这一点的一个很好的比喻是将一个人的健康视为一整片森林;对抗疗法只关注
一棵树,而功能医学的重点是整片森林。功能医生会盘点患者健康的每一个障碍,并在治疗计划中解决每个
方面。此外,帕金森病是一种复杂的疾病,有多种相互重叠的致病因素,如接触有毒物质、代谢障碍、解毒和线
粒体功能、炎症以及胃肠道和免疫功能障碍。这些方面都需要进行额外评估,以便在安娜的治疗中获得优势。
为了改善安娜的生活质量,她的孩子们同意参与改变家庭生活,并承诺成为她护理的积极伙伴。
帕金森病的病因和机制
帕金森病以詹姆斯·帕金森的名字命名,他于 1817 年在西方医学文献中首次发现了这种疾病。虽然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才开始了解帕金森病背后的机制,但
早在 5,000 年前,印度草药医学和中医文献就已经对这种疾病进行了详尽的记录。1帕
金森病会影响中脑黑质中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导致渐进性症状,包括震颤、动作迟缓、肢
体运动僵硬、面部表情减少、言语困难、嗅觉减退、消化和泌尿问题、疲劳、抑郁、疼痛、认
知变化、眩晕、视力变化、无法控制的重复动作、小写症和痴呆。每个人的病情进展都是
独一无二的,但大多数患者都会出现面部表情麻痹或僵硬和震颤。虽然我们可以确定
疾病的位置和基本病理表现,但我们对其发病机制和如何逆转它仍然知之甚少。帕金森
病没有单一的决定因素;相反,人们主要认为帕金森病是多种因素导致大脑黑质神经元
退化的氧化和免疫介导的结果。研究表明,帕金森病的病因有很多,从遗传基因突变到
接触有毒化学物质或病毒,再到细菌失衡。2尽管诱因各不相同,但帕金森病的根本原因
是病理性错误折叠的 α‑突触核蛋白的存在,这些蛋白构成了路易体聚集体、黑质细胞
损伤以及黑质神经元多巴胺生成受到抑制。3
1996 年,基因图谱使我们能够识别出 15 多种与帕金森病相关的基因突变,包括
SNCA、PRKN、PINK1、DJ‑1、LRRK2、G2019S、GBA、MAPT、mtDNA 和 iPD 基因突变。
这些突变会影响线粒体、抗氧化剂和免疫功能。4第一个发现的突变是 SNCA 突变,它
与 α‑突触核蛋白的增加有关,虽然这种蛋白质的功能尚不完全清楚,但发现它与路易体
形成、神经退化和痴呆症有关。另一方面,PRKN 与线粒体的维护以及不需要的蛋白质
的降解和清除有关。同样,DJ‑1 在保护线粒体的神经和细胞改善氧化应激的能力方面
发挥作用。 DJ‑1 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每个细胞中,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帕金森病患者的
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中,DJ‑1 被过度氧化。此外,DJ‑1 在酪氨酸羟化酶的调节中发
挥作用,酪氨酸羟化酶将大脑中的酪氨酸转化为左旋多巴。5
LRRK2 基因与 1% 到 2% 的帕金森病诊断有关,尽管它被认为可以预防病原体感
染,但也与免疫和炎症引起的神经元死亡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一例 LRRK2 阳性双胞胎的病例报告发现,兄弟姐妹中只有一个人患有
帕金森氏症,从而凸显了表观遗传学的重要性以及导致疾病发展的因素的复杂性。6总
体而言,多态性降低了神经元对细胞毒性的耐受性,这种细胞毒性可能是由多种机制引
起的,包括免疫功能障碍、人类白细胞抗原水平升高、脂质体损伤、过量自由基暴露、氧
化、铁和铜的积累、溶酶体功能障碍、颗粒蛋白脂肪酸代谢失调、内吞病理、神经炎症、磷
酸化问题和小胶质细胞活化。7虽然基因多态性不能预测帕金森氏症,但它们有助于评
估与环境暴露相关的风险,预测疾病发病年龄,并阐明线粒体缺陷背后的机制以及活性
氧、氧化损伤和异常蛋白质聚集的作用。
帕金森病诊断中只有 10% 到 15% 与基因突变有关,因此研究人员继续对导致这
些诊断占主导地位的可能原因进行分类。似乎任何可能抑制线粒体功能并增加炎症的
因素都可能与此有关,而毒性暴露是可能的诱因之一。患者病史和实验室动物暴露表明,
帕金森病的病理过程是由化学毒物引起的。众所周知,MPTP 是合成海洛因的副产品,据
报告称,它会导致帕金森病发作,因为非法药物过量。在研究动物和体外样本中的这种物
质时,研究人员能够确定线粒体损伤是帕金森病病理的主要因素。
8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细胞无法中和的其他有毒物质和有害物质是帕金森病的潜在诱
因。在过去的 30 年里,杀虫剂、化学溶剂、除草剂、杀鱼剂和药物中的特定物质与纹状体
细胞的神经元损伤有关。9已确定导致黑质纹状体损伤的特定神经毒素包括 1‑甲基‑4‑
苯基‑1,2,3 (MPTP)、6‑羟基多巴胺 (6‑OHDA)、2,4‑二氯苯氧乙酸 (DDT)、三氯乙烯、百
草枯、鱼藤酮、多氯联苯 (PCB)、
有机氯农药、六氯苯、全氯乙烯、有机磷酸盐、汽油燃料以及锰、铜和铁等金属。10更为复杂的是,对一名帕金
森病患者的尸检显示,黑质中谷胱甘肽含量低,据推测这与过度氧化应激有关,氧化应激可能是由于先天
性谷胱甘肽生
成不足或自由基暴露不成比例所致。11接触有毒物质时,对自由基和谷胱甘肽的需求会增加。此外,中脑
在正常功能过程中会自然产生几种氧化剂作为副产品。从生理上讲,黑质中含有高水平的铁、多巴胺和神经
黑色素,它们会转化为有害的自由基。谷胱甘肽是吸收和中和这些自由基的关键物质。谷胱甘肽还在维持神
经元活力的线粒体复合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黑质是大脑中唯一发现缺乏谷胱甘肽的
部分,而大脑其他区域的谷胱甘肽水平则相对较充足。
这表明,帕金森病可能是由于局部过量自由基氧化导致谷胱甘肽耗尽所致。12在诱发帕金森病的实验动物
中,黑质中也发现谷胱甘肽缺乏。
最后,研究人员研究了经过基因改造以抑制谷胱甘肽产生的实验动物,以了解它们是否抑制了线粒体复合
物 I 活性,以及丁硫氨酸亚砜亚胺等化学药剂的神经毒性增加。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细胞内谷胱甘肽水平升
高对神经元具有保护作用,尤其是暴露于较高氧化和自由基的神经元,例如黑质中的神经元。13
直到 2014 年,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 (CUIMC) 的研究人员确定神经元易受免疫 T 细胞攻击,人
们才知道过量自由基氧化和神经炎症的病因。14 CUIMC 的 Sulzer 博士团队继续发现可以从活体帕金森
病患者身上提取免疫细胞,并研究其特征。该团队指出,帕金森病患者的 T 细胞会攻击 α‑突触核蛋白,而非
帕金森病患者的 T 细胞对 α‑突触核蛋白没有免疫反应。15这种现象引发了帕金森病可能是 α‑突触核蛋白
沉积刺激的 T 细胞和小胶质细胞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理论。16德国埃尔朗根大学医院的研究人员同样发现
帕金森病患者
巴西和意大利的研究人员提出,肠道微生物失调是引发神经炎症的主要因素,也是 α‑突触核蛋白功能障碍的诱因;
而波兹南医科大学和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则认为,菌群失调导致的 α‑突触核蛋白病变证明 PD 可能是
一种源自肠神经系统的朊病毒疾病。20智利安德烈斯贝洛大学的动物研究表明,发炎的菌群失调胃肠道粘膜会在
肠神经系统中产生路易体,并增加从肠道开始并进展至大脑的 T 细胞介导的炎症。21密歇根州⽴大学 2018 年进
行的动物研究表明,α‑突触核蛋白病理可以在肠神经系统中受到刺激,导致肠道运动受抑制。
最近,神经科学家开始研究胃肠道健康作为导致 α‑突触核蛋白错误折叠增加和过度免疫活动的主要因素的
作用。帕金森病患者最初通常表现为胃肠道症状和功能障碍,以及肠神经系统粘膜下神经元的路易体病理。
Th17 细胞(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的 T 细胞)增加,据信它们正在攻击多巴胺能神经元。17此外,爱荷华州帕金森
病研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公布了他们 2016 年动物和人类研究的详细信息,
该研究分离了一种参与免疫活动的酶 蛋白激酶 C delta (PKCd) 及其在帕金森病中的作用。在他们的研
究中,Gordon 等人确定 PKCd 是由错误折叠的 α‑突触核蛋白上调的。PKCd 被确定为一种通过小胶质细胞和脂
多糖 (LPS) 增加炎症反应的介质。阻断 PKCd 可产生神经保护作用,避免刺激帕金森病对多巴胺神经元造成损害
的药物。18为进一步证实帕金森病的免疫病理性质,研究人员不断发现涉及神经胶质细胞、神经炎性细胞因子 NF‑
kB 和 PKCd、α‑突触核蛋白错误折叠、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a) 和脂多糖的免疫介导功能障碍,所有这些都在炎
症引起的中脑损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
2018 年发表的其他动物研究表明,降低 T 细胞炎症反应可逆转与帕金森病相关的神经退行性
病变。23
22
神经科学家推测,肠道免疫系统的过度刺激可能是蛋白质病和神经胶质细胞功能障碍的关键决定
因素。24这些发现引发了大量新的研究,旨在探索有前景的治疗方法,以帮助减少帕金森病所涉及的炎
症、免疫和氧化退化,首先从消化系统健康开始。
治疗帕金森症
在评估帕金森病症状的患者时,功能治疗师会考虑疾病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并根据个人独特的临床表
现和病史选择治疗方法。治疗方法旨在解决个人健康状况的各个方面,包括他们接触环境毒素的情况、
创伤史、慢性压力源、体质、家族倾向、消化完整性、基本器官功能、排毒途径的效率和可行性、合并症、活
力和治愈能力。治疗方法包括谷胱甘肽补充、低剂量纳曲酮 (LDN)、针灸、排毒 (净化) 方案、营养变化、
压力管理、心理情绪疗法、植物疗法和营养干预。营养支持可能包括益生菌、N‑乙酰半胱氨酸 (NAC)、
Mucuna pruriens和其他基于个人缺陷的营养补充剂。谷胱甘肽通常用于患者在接触有毒物质后出
现症状或怀疑存在线粒体功能障碍时。LDN 有助于减轻炎症、慢性疲劳、肠道蠕动受损和疼痛。针灸可
减轻疼痛并改善精力、情绪、睡眠和消化过程。在众多可供选择的功能性疗法中,谷胱甘肽和 LDN 在研
究中显示出巨大的前景。以下部分探讨了这两种疗法在治疗帕金森病中的作用。
谷胱甘肽在帕金森病治疗中的作用
谷胱甘肽是人体最重要的抗氧化剂之一。它影响帕金森病病理过程中的多种机制。它保护组织免受炎
症引起的损伤,中和羟基自由基,参与 I 期和 II 期肝脏解毒,是维持正常功能所必需的。
谷胱甘肽作为抗氧化剂的作用在中脑中尤为重要。
26如果细胞氧化应激过度、炎症或外来化合物浓度
过高,半胱氨酸就会被释放,从而增加谷胱甘肽的生成。在治疗上,谷胱甘肽通过静脉注射给药;或者,其
氨基酸前体 N‑乙酰半胱氨酸作为口服补充剂给药。NAC 和谷胱甘肽都用于减轻化学物质造成的神经
毒性损伤、改善线粒体功能、保护多巴胺神经元免受氧化损伤,以及保护 DNA 免受活性氧和衰老造成
的损伤。27谷胱甘肽系统在帕金森病研究领域引起了极大关注,因为我们早就发现黑质中的谷胱甘肽
缺乏是帕金森病发病机制的关键,尽管这种缺乏似乎是由多种破坏性因素引发的。与帕金森病相关的谷
胱甘肽缺乏的原因包括自然衰老、DNA 降解、过量自由基、抗氧化状态低、神经黑色素、过量铁以及外源
性毒素。28谷胱甘肽缺乏与帕金森病症状的严重程度有特别的相关性。
有害的活性氧 (ROS) 是细胞产生能量的天然副产品。它们发挥各种复杂的功能,例如细胞信号传导。它
们有助于抗菌过程,但也会损害细胞膜中的脂质并导致线粒体 DNA 和 RNA 蛋白受损。29虽然自由基由
于缺乏电子而不稳定,但谷胱甘肽等抗氧化剂即使在放弃电子后也能保持稳定。谷胱甘肽以高浓度存
在于细胞中,并被泵入线粒体以减轻自由基造成的损害。
谷胱甘肽由氨基酸半胱氨酸、甘氨酸和谷氨酸在细胞质中合成,然后以高浓度转移到全身的线粒体中。
线粒体有助于能量产生、激素的生物合成、营养代谢、调节Ca2+细胞稳态、自噬和基因表达。细胞能量需
求失衡、ROS 的产生和
同样地,谷胱甘肽可以保护 DNA 免受活性氧造成的损害。25谷胱甘肽含量低与慢性化学物质暴露、
慢性疾病、衰老和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
线粒体功能和 DNA 维护,并协助排出内源性和外源性细胞毒素。它还有助于保持和增强中脑多巴胺的
功效。
,
自由基清除障碍会导致线粒体 DNA 受损。这些现象构成了自然衰老过程,并构成了线粒体
衰老理论的基础。30考虑到 96% 的帕金森病诊断发生在 50 岁以后,因年龄导致的线粒体
损伤被认为是帕金森病最重要的风险因素。31此外,在较年轻的帕金森病患者中也发现了类
似的线粒体功能障碍。在这个人群中,诊断通常归因于遗传病因。
三十二
关于谷胱甘肽在 DNA 保护中的作用,有多项相关体外和体内研究详细说明了谷胱甘肽
如何减缓 DNA 的自然老化和退化。这很重要,因为 DNA 侵蚀与衰老有关,是神经退行性疾
病的主要风险因素。33当 DNA 无法修复时,多巴胺系统和 α‑突触核蛋白病理会变得更加功
能失调。34体内和人体研究表明,谷胱甘肽可保护端粒酶的活性,端粒酶可调节 DNA 免受
慢性氧化应激或其他合并症过程造成的损伤。35此外,作为细胞中的主要抗氧化剂,谷胱甘
肽进一步保护线粒体 DNA 免受自由基损伤。36服用谷胱甘肽可改善这一退化过程。然而,
结果取决于给药方式,因为口服谷胱甘肽的功效有限;舌下和静脉注射形式似乎具有更大的
治疗价值。37
就谷胱甘肽如何改善患者症状而言,人们对谷胱甘肽复合物减少运动抑制和多巴胺能
损伤的兴趣日益浓厚。小规模研究和病例报告继续充斥着 PubMed 档案的索引,记录了谷
胱甘肽对帕金森氏症运动功能的改善作用。神经病学家 David Perlmutter 博士的著名案
例研究记录了静脉注射谷胱甘肽改善运动功能的治疗用途。38其他出版物,如已发表的自然
疗法医生 Otto 和 Magerus 的病例报告,详细介绍了将谷胱甘肽静脉注射添加到标准治疗
方案中后帕金森氏症的僵硬和震颤得到缓解的情况。39在这些病例中,谷胱甘肽治疗是辅助
性的,可在标准治疗用尽后缓解仍然存在的症状。相比之下,萨萨里大学神经学家先前的研
究表明,静脉注射谷胱甘肽作为单一疗法可以逆转未经治疗的帕金森病患者的症状。40
谷胱甘肽的前体 NAC 也因其在帕金森病中的应用而受到广泛研究。它曾被用于治疗肝毒性、对乙
酰氨基酚过量、囊性纤维化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NAC 最近因其在细胞中上调谷胱甘肽的作用而受到
关注,从而增加了中枢神经系统的抗氧化反应并改善了环境和内源性污染物对线粒体的神经毒性。如前
所述,线粒体损伤和黑质纹状体多巴胺的损失与细胞内的损伤性代谢物有关,例如神经黑色素、金属、过
度氧化和外源性化学物质暴露。41在动物研究中,施用 NAC 可减轻由许多与帕金森病相关的化学物质
(例如 MPTP、6‑羟基多巴胺、鱼藤酮和其他神经毒素)引起的纹状体神经元的神经毒性损伤。42在多
项研究中,使用磁共振波谱法检测到帕金森病、戈谢病和缺氧缺血性脑病患者静脉注射 NAC 后,大脑
谷胱甘肽水平显著升高。43匹兹堡大学的研究人员证明 NAC 可以独⽴保护星形胶质细胞免受 α‑突
触核蛋白的蛋白毒性损伤。44他们的发现表明,NAC 的神经保护作用不仅仅依赖于转化为谷胱甘肽,
尽管谷胱甘肽转化可能是一个额外的好处。
此外,西班牙拉巴斯大学医院的报告表明,体外和体内使用 NAC 可减少衰老小鼠的线粒体功能障
碍和神经退行性病变。45 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的另一项动物研究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口服
NAC 可减弱 α‑突触核蛋白并保护多巴胺神经元。46托马斯·杰斐逊大学最近的研究发现,口服和静脉
注射 NAC 均可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症状和多巴胺转运蛋白功能。47 NAC 仍然是减少帕金森病
损伤剂最便宜且研究最多的补充剂之一。
最后,在评估与线粒体毒物(如重金属和有机磷酸盐)相关的帕金森病风险时,谷胱甘肽缺乏症也
与此有关。这些化学物质与线粒体中谷胱甘肽的耗竭有关。例如,2006 年发表的小鼠研究阐明了鱼藤
酮中毒如何抑制线粒体中谷胱甘肽复合物 I
线粒体中的电子传递链,从而减少谷胱甘肽并最终导致细胞死亡。48谷胱甘肽通过控制肝脏解毒途
径 II 期和 III 期的 Nrf2 蛋白发挥作用。
谷胱甘肽系统通过在 II 期和 III 期解毒途径中使用 Nrf2 蛋白,显著帮助净化和消除重金属和有机
污染物。49它已被证明可以改善肝功能、降低异常肝酶并帮助清除毒素。50
帕金森病患者可以通过血清、尿液和头发分析来评估重金属、铁积累和污染物。当暴露严重限制
患者的治愈能力时,自然疗法医师会将谷胱甘肽 IV 与其他疗法结合起来,以减轻细胞的毒性负担。
根据暴露程度和患者的体质、年龄和合并症,功能治疗师通常会添加桑拿、特定饮食方案和植物药等
疗法来进一步增强排毒效果。放血疗法可用于减少铁储存,螯合疗法可用于重金属。确定暴露的原因
并教育患者减少在家中、食物或环境中再次暴露至关重要。
LDN 在帕金森病治疗中的作用
帕金森病病理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周围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免疫和炎症活动。
大量临床、尸检和动物研究表明,帕金森病患者中脑中普遍存在的炎症细胞因子、小胶质细胞和 T 细
胞活动与多巴胺能神经元功能受损有关。这些研究确定了病毒、细菌和毒性催化剂,它们会驱动细胞
因子、α‑突触核蛋白和异常 T 细胞活动的炎症级联,这些级联会穿过血脑屏障并诱导中脑破坏性微
胶质增生。51 高水平的炎症细胞因子与疼痛、便秘和痴呆等非运动性帕金森病症状有关,而免疫小
胶质细胞和 T 细胞水平升高与中脑退化和运动系统症状有关。52
在死后患者和动物的中脑中发现的一些关键促炎因子包括 α‑突触核蛋白、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a)、脂多糖、白细胞介素 6 (IL‑6)、蛋白激酶 C
delta (PKCd)、活化的小胶质细胞和 T 细胞。此外,与非帕金森病对照组相比,帕金森病患者的脑脊液中
IL‑1B 和 IL‑6 升高。53值得注意的是,α‑突触核蛋白、TNF‑a、干扰素γ (IFN‑y)、IL‑6 和神经胶质活化标志物
(GFAP 和 Sox10) 存在于升结肠中。科学家目前假设肠道炎症可能是神经炎症级联的根源,因为 CD4+ T 细
胞、结肠细胞因子和路易体作用于中枢神经内皮细胞,导致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和渗出。54事实上,肠道炎症、
CD4+ T 细胞和便秘的早期参与是严重运动障碍出现前数年出现的标志。55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如 MS,也与
神经胶质和 T 细胞活性升高有关。在 MS 中,免疫 T 细胞会攻击少突胶质细胞,而在帕金森病中,由 a‑突触核
蛋白触发的 T 细胞活动会通过过量的 ROS 损害黑质中的神经元。56在这两种情况下,中枢神经系统中都存在
大量促炎细胞因子,例如 TGF‑B、IL‑1B、IL‑6、IFN‑γ 和 IL‑1。57研究人员在针对炎症机制时能够减缓多巴胺能
损伤的进展,减少帕金森病诱发模型中的神经胶质细胞和 T 细胞的参与。58尽管神经炎症过程很复杂,但研究
人员仍在继续扩展这些发现的细节和不可避免的治疗方法。
在动物研究中,肠道菌群的改变导致 α‑突触核蛋白增加,从而引起粘膜下肌间神经丛
和大脑的过度免疫反应。59此外,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动物口服鱼藤酮后也诱发了类似的
胃肠道反应。60其他研究领域表明,病毒或细菌暴露会引发炎症反应,导致免疫和蛋白质
功能障碍。61此外,当帕金森病动物(通过 A53T α‑突触核蛋白突变)接受 FK506(一
种 T 细胞免疫抑制药物)治疗时,多巴胺神经元得以保存。62免疫功能障碍的其他标志
物已被确定为 MHC 编码蛋白,这些蛋白会随着疾病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并导致多巴
胺神经元易受神经胶质激活的影响。63
神经胶质细胞及其炎症细胞因子尤其值得检查,因为它们在
多项研究表明,使用 NEMO 结合域 (NBD) 肽可成功治疗帕金森病动物,该肽可抑制 NF‑kB、小胶质细胞活化并
阻止炎症神经元破坏。65对小胶质细胞抑制的小鼠进行的其他动物研究显示出类似的多巴胺能保护作用,而增加
小胶质细胞增生的药物会加剧多巴胺神经元的破坏。66目前和正在进行的逆转帕金森病的新疗法研究集中于使用
免疫调节疗法减少神经毒性炎症和免疫失调。67
临床上已使用低剂量纳曲酮来减少炎症和免疫失调。有充分证据表明,LDN 的机制是调节 T 细胞功能并减少
神经胶质细胞活化和相关的神经毒性炎症级联,所有这些都是帕金森病病理生理学的标志。
帕金森病患者的中脑。64发现 α‑突触核蛋白聚集体会刺激小胶质细胞活化,导致过度炎症,然后导致神经元死亡。
其他相关的小胶质细胞激活剂包括神经黑色素、基质金属蛋白酶‑3 (MMP3)、纤维蛋白原环境脂多糖毒素、MPTP、
杀虫剂(鱼藤酮、百草枯)、蛋白酶体和重金属。值得注意的是,当小胶质细胞受到抑制时,多巴胺神经元得以保留,
帕金森病进展停止。 或者
通过降低 Toll 样受体 4 和细胞因子反应
(如 Toll‑白细胞介素受体、干扰素 β、干扰素 γ 和肿瘤坏死因子),它已显示出治疗克罗恩病、炎症性肠病、桥本甲
状腺炎、纤维肌痛、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多发性硬化症等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前景。 69与帕金森病类似,
多发性硬化症涉及病变部位小胶质细胞活化增高、过度炎症、氧化、ROS 和神经组织恶化(白质和灰质中的脱髓
鞘斑块)。70 LDN 已被反复研究作为缓解小胶质细胞炎症和减轻 MS 症状的治疗方法,表明其有望缓解相关的
帕金森病症状。71在对帕金森病诱发的大鼠的研究中,纳洛酮被证明可以减少小胶质细胞自由基和促炎剂,从而
保护多巴胺能神经元。72体外纳洛酮处理的中脑神经胶质细胞培养表明,纳洛酮与 Nox2 结合是一种防止小胶质
细胞和超氧化物神经变性的机制。73
68
关于 LDN 临床应用的小型研究和病例报告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结果。Thomas Guttuso 等人发表了研究
结果,表明 LDN 可以缓解帕金森病患者的慢性疲劳症状。74关于这种药物对帕金森病的用途的大规模研
究尚缺乏,但考虑到其神经抗炎作用,它可能是一个有前途的研究领域。
神经病学家 Bernard Bihari 博士是治疗性 LDN 的主要先驱。他报告说,他曾监督过七名帕金森病患
者,这些患者的病情在接受 LDN 治疗后停止或消退。Bihari 博士提出,LDN 影响的是慢性疾病的另一个
因素:内啡肽。
他在实践中注意到一种现象:患者在遭遇严重的压力(例如亲人去世)后会患上慢性疾病。
Bihari 博士受过神经病学、脑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培训,具有独特的背景,能够理解内啡肽的生理作用。他认
为,那些重大的压力事件会降低患者的内啡肽水平,使他们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影响。75后续研究证实了内啡
肽在减少帕金森病和许多其他慢性病的炎症和免疫功能障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假设。76研究表明,当
我们参与运动、跳舞、唱歌、大笑、冥想、禁食、亲密、瑜伽、太极和针灸等令人愉悦的活动时,内啡肽的水平会
升高。77 研究表明,内啡肽的抗炎作用能够减轻与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慢性病相关的症状。78内啡肽的下降
可能在帕金森病患者遭受的慢性疼痛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帕金森病患者的血浆和脑脊液中内啡肽
水平较低。79在影响内啡肽方面,LDN 尤其以帮助 β‑内啡肽的产生而闻名,从而减轻纤维肌痛、类风湿性
关节炎和复杂性局部疼痛综合征等疾病引起的慢性疼痛。80增加内啡肽和稳定帕金森病进展的其他治疗
方法包括瑜伽、太极拳、针灸、舞蹈和运动等活动,所有这些方法都被证明可以改善帕金森病的结果、缓解症
状和/或在一定程度上逆转脑部 MRI 的变化。81
最后,有大量研究调查了炎症性肠道在帕金森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肠道疾病被普遍认为是帕金森病
的主要症状表现之一,因为神经肌肉抑制会导致肠道运输减慢,进而加剧许多其他菌群失调后遗症。但直
到最近,研究人员才开始假设炎症和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可能是导致异常 α‑突触核蛋白复制、自身免疫样
功能障碍和神经炎症过程形成的最初因素。82 2014 年,马来亚大学的神经病学家和胃肠病学家联手评估
了 PD 患者的小肠细菌过度生长 (SIBO)。他们发现,几乎 25% 的参与者检测出 SIBO 呈阳性。这些患者的
运动功能障碍比非小肠细菌过度生长患者更严重。83同样,2016 年,新乡医学院的研究人员诊断出 30%
的帕金森病患者患有小肠细菌过度生长。此外,与非小肠细菌过度生长患者相比,小肠细菌过度生长与更严
重的运动症状相关。84这些研究引发了大量人类和动物研究,探讨肠脑连接以及通过饮食调整、促动力药、
益生菌、泻药、粪便移植和抗生素减少消化道炎症的治疗方法。85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通过调节和改善肠
道功能,疾病表现得到改善。
就 LDN 作为促动力和抗炎药物的用途而言,这可能是 LDN 介导帕金森病菌群失调及其炎症/免疫级联的
另一种方式。Mitchell 等人于 2018 年发表的一项值得注意的研究发现,LDN 改善了 74.5% 的炎症性肠
病 (IBD) 患者的临床症状。作者得出结论,LDN 是一种安全有效的 IBD 治疗方法。86
案例研究
安娜初次入院时,我记录了她的症状:“尿失禁、僵硬麻痹、声音减弱、运动迟缓、无法在家中驾驶滑板车、由
于反应迟钝导致滑板车撞坏、夜间双脚灼热、腿部肌肉紧张疼痛,导致她半夜醒来。”
夜间睡眠不足,无法进行日常生活活动,不能自己做饭或开车,大多数日子里无法行走,步
态蹒跚,无法穿过门口或转弯,走路时手臂静止不动。” 她有严重的乳腺癌和甲状腺功能
减退症病史,她的丈夫最近去世了。我们保守地评估了同型半胱氨酸、甲基四氢叶酸还原
酶 (MTHFR)、促甲状腺激素 (TSH)、全血细胞计数 (CBC)、综合代谢组 (CMP)、铁蛋白、铁、
维生素B12、 A1C、红细胞沉降率 (ESR) 和 C 反应蛋白 (CRP) 等基本实验室检查。通常,
功能医生会进行额外的基因、重金属、有机酸和化学测试,以了解环境和微生物暴露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家人希望采取极简主义的方法,要求我们尽可能少地运行实验室检查。
她的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甲状腺功能减退、缺铁性贫血和甲基四氢叶
酸还原酶多态性阳性。她的乳腺癌治疗包括 Faslodex、他莫昔芬、CHOP 和紫杉醇。这段
病史,加上 MTHFR 多态性,可能是她长期健康最显著的压力因素,因为 MTHFR 与谷胱甘
肽生成减少和药物耐受性低有关。
此外,由于疼痛,她的睡眠质量很差,经常不吃饭,而且也不锻炼。
我们开始采用一个适度的计划,每晚服用 3.0 毫克 LDN,按照神经学家 David
Perlmutter 博士的工作进行静脉注射谷胱甘肽,服用促进多巴胺的植物Mucuna
pruriens,以及基于全食物的饮食调整。87因为安娜身体虚弱,病情发展如此迅速,所以我
们谨慎行事,一次采用一种新疗法,并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谷胱甘肽静脉注射的频率和
浓度每周缓慢增加。治疗四周后,我们进行了跟踪,以评估该计划的有效性。我很高兴听到
安娜亲口报告她的病情有所好转。虽然她的声音可以听到,但她的面部表情仍然减弱,步态
还没有明显改变。但她感觉好多了,她的女儿高兴地报告说,在第一次静脉注射后,她已经
能够独⽴行走两天了。安娜和她的家人对已经发生的微小但显著的变化感到鼓舞。
我们和安娜的孩子们一起制定了计划,如果可能的话,她将谷胱甘肽静脉注射的频率增
加到每周两次,但至少每周一次,并每两周监测一次她的进展。她继续服用 Sinemet,并让
她的神经科医生知道她正在寻求辅助治疗。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看着安娜取得了显著
的进步。她的声音变得更有力,面部表情恢复了,她微笑着大笑。其他症状逐渐减轻。她的步
态改善了,精力充沛了,失禁减少了。每次看诊我都会监测她的步态流畅性。虽然她走得很
慢,在拐角处拖着脚步,但她在走廊里走得很平稳。她用助行器代替轮椅,然后在拐角处用
轻柔的手臂支撑代替助行器。三个月后,她的病情已经好转到可以和女儿一起度过一个下
午,在购物、吃午饭和做头发时无需帮助就能四处走动。当她开始感觉好转时,我们继续对
她的治疗计划做出微小但有效的改变。
在安娜的案例中,她的症状和诊断是在两个巨大的压力因素之后出现的:她丈夫的去世
和她接受乳腺癌化疗。这两个压力因素可能是严重的障碍,最终抑制了她的线粒体功能并
削弱了她身体修复损伤的能力,为不受限制的炎症退化造成损害铺平了道路。我们用谷胱
甘肽 IV 解决了有毒物质暴露可能造成的线粒体损伤,并添加了 LDN 来帮助减少神经病
变并使胃肠功能正常化。我们随后采取了针灸措施,以帮助她缓解尿失禁,增加内啡肽,改
善她的情绪和活力。当她感觉好些时,我们设定了每周的小目标来改善她的营养并培养基
本饮食。我们还为她设定了与孩子和孙辈进行社交互动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添加
了口服 NAC、铁和Mucuna pruriens。通过这项治疗,安娜逐渐恢复了在别人扶着手的情
况下行走的能力,并能从坐姿独⽴站起,自由地说话、大笑和做手势。她的尿失禁减少了,睡
眠质量提高了,疼痛感也减轻了。她能够在家为自己做一顿简单的饭,并重新驾驶她的摩托
车。安娜对治疗的反应非常显著,她恢复的开朗性格令人欣慰。
结论总之,帕金森病
是一种复杂的疾病,涉及多个重叠的功能障碍区域,很难确定单一原因。与其他
慢性疾病一样,可能没有一种简单的治疗方法,而是有多种治疗途径,必须根据
患者的病史和体质进行专门定制。帕金森病研究表明,即使这种疾病涉及中脑的
明显缺陷,但整个身体的功能都受到影响。我是一名自然疗法医生,治疗整个人
是我训练的基础。功能医生明白,如果解决了整个人的健康问题,任何疾病都有
可能得到改善。通常,彻底的摄入会揭示阻碍愈合过程的重要障碍,并且可以为
每位患者制定独特的治疗方案。
自然疗法医生很少采用千篇一律的标准化疗法。
相反,患者计划是全面而独特的;对一个患者有效的方法可能不是下一个患者所需要的。功能治疗师探索和
治疗我们生理学的复杂、动态和重叠性质。这种整体方法可能是帮助我们理解和治疗帕金森症等未解决疾病
的另一个关键。
‑六‑
儿科
维维安·F·丹尼斯,DO,ABAARM,FAARFM
虽然大多数医学分支似乎都在以超光速发展,但儿科神经认知疾病领域的进展似乎长期处于
痛苦的停滞状态。这让儿科医生和父母,也就是我们孩子值得信赖的照顾者,感到无助和绝望。
事实上,对于自闭症、焦虑症、抑郁症、儿童急性发作神经精神综合征 (PANS)、与链球菌感染相
关的儿童自身免疫性神经精神疾病 (PANDAS)、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 等疾病,治疗方
法有限或根本不存在。目前,3 至 17 岁的所有儿童(440 万名儿童)中有 7.1% 被诊断患有
焦虑症,3.2% 被诊断患有抑郁症。1从历史上看,我们唯一的解决方案是给患病儿童服用药
物,但这些药物会对他们正在发育的大脑和身体产生无数严重的副作用,而且收效甚微。然而,
LDN 提供了一种未被充分利用的工具,可以在如此具有挑战性的条件下开辟新领域。在本章
中,我将分享我在自闭症、焦虑症、PANS/PANDAS 和青少年慢性疲劳综合征 (CFS) 中使用
LDN 的经验。
自闭症谱系障碍
过去,广泛性发育障碍(现归入自闭症谱系障碍 (ASD) 范畴)被分为自闭症、未另作规定的广
泛性发育障碍 (PDD‑NOS)、
3 目前,美国每 59 名儿童
中就有 1 名被诊断患有自闭症,男孩被诊断的概率是女孩的四倍。4严重程度分为三个不同的等级:
需要支持、需要大量支持和需要非常大量的支持。5
根据 DSM‑5,“自闭症谱系障碍中个人结果的最佳预后因素是是否存在相关的智力障碍、语言
障碍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6
大脑有许多不同的部分,但最大的部分是大脑。大脑分为左右两侧或两个半球。大多数人(66%)的
言语由左侧控制。而另外 33% 的人(通常是左撇子)的言语由右侧控制。每个半球进一步分为额叶、
颞叶、顶叶和枕叶。言语主要由额叶和颞叶决定。每个叶进一步细分。左额叶大脑内有一个称为布罗
卡区的区域,它负责将思想和想法转化为实际的文字,通过向控制嘴部运动的运动皮层发送信号,形
成文字。大脑中的第二个区域是韦尼克区,位于耳朵后面的颞叶。这个区域负责理解言语并产生正
确的单词和书面语言。这两个区域是
我们如何说话的简要概述
阿斯伯格综合征、雷特综合征和儿童瓦解性障碍,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发病年龄进行分类。这种
疾病的特点是社交沟通和重复行为互动受损。根据《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 (DSM‑5)
诊断患有 ASD 的人必须符合社交沟通/互动领域的所有三个标准(社会情感互动缺陷;非言语交
流行为缺陷;发展、理解和维持关系缺陷)和限制性/重复行为领域四个标准中的至少两个(重复的
言语或动作、坚持相同、兴趣狭窄和对感官输入的异常反应)。2这些障碍不能更好地用智力障碍
或整体发育迟缓来解释。
由弓状束连接。这种结构使布罗卡区和韦尼克区之间能够进行沟通,使我们能够形成词语、清晰地说
话并理解语言。
大脑中与语言有关的另外两个区域是小脑和前面提到的位于额叶的运动皮层。这些区域负责说
话。运动皮层控制你的嘴、舌头和喉咙,而小脑控制嘴的随意运动以及语言处理。然而,如果没有被称
为神经递质的物质,这些区域都无法发挥作用。
神经递质是大脑和周围神经系统中的化学物质,使一个神经细胞能够“交谈”并将信息传递给下
一个神经细胞,最终导致动作。根据受体位点的存在,神经递质有兴奋性、抑制性,有时也有兴奋性和
抑制性。在大脑的不同区域,某些神经递质更丰富,作用更大。在大脑皮层中,主要的神经递质是:血清
素、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乙酰胆碱和 GABA。GABA、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乙酰胆碱分布在大脑
皮层的所有区域,而多巴胺仅分布在小脑的额叶和扣带回区域。
GABA 是小脑的主要神经递质。它在体内的作用是抑制或降低神经细胞的活动。它是让人感到平静和放松的
必需物质,大多数皮质神经元都会使用它。2011 年,Harada 等人的一项研究发现,患有 ASD 的儿童额叶皮质中
的 GABA 浓度降低。7人们认为,GABA 能系统中断与大多数神经发育障碍有关。术语GABA 能系统是指参与
GABA 合成或分解的突触。事实上,染色体 15q11‑13 上的 GABRA5、GABRB3 和 GABRG3 基因中断与发育迟
缓、自闭症以及这些相邻基因综合征中观察到的其他临床特征以及印记缺陷有关。8
另一种神经递质血清素存在于小脑和肠道中。它通常被称为“快乐神经递质”,调节情绪、社交
行为、食欲、消化和睡眠。
去甲肾上腺素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它负责注意力、学习能力和情绪,是战斗或逃跑反应的一部
分。
去甲肾上腺素由肾上腺和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大多数治疗 ADHD 的药物都针对去甲肾上腺素。
乙酰胆碱是所有神经递质中最丰富的。它由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产生。它在学习、记忆
形成、内分泌系统调节以及 REM 睡眠中发挥作用。
多巴胺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负责产生愉悦感和满足感,以及控制肌肉和胃肠道蠕动。它对于
舌头运动和言语的形成至关重要。利他林通常用于治疗 ADHD,其作用是促进多巴胺分泌。当多巴胺
增加时,GABA 就会减少。
我们发现自闭症儿童的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 (MTHFR) 变异体较高。9该基因负责将非活性叶酸转化为活性叶酸。
如果以甲基化(活性)形式提供叶酸,则更多的叶酸可以穿过血脑屏障,这有助于增加神经递质的形成,从而增加口头
交流。
这一切与 LDN 有什么关系?概括地说,LDN 阻断阿片类受体约四个小时。这会导致内源性阿片
类药物(内啡肽和脑啡肽)的产生增加。这反过来又会导致突触间隙中多巴胺释放增加。患有 ASD
的儿童尤其受益,因为他们获得了增强的肌肉控制能力,因此增强了言语形成能力。
案例研究 1:杰克和约翰
杰克三岁,约翰四岁。杰克被诊断患有严重的言语和发育迟缓,约翰患有自闭症,言语发育迟缓,几乎
没有语言能力。
两名儿童均被发现缺乏肉碱。他们开始每天服用 100 毫克/千克的左旋肉碱。他们
开始服用 0.5 毫克的 LDN,然后逐渐增加至 4.5 毫克。
杰克几乎⽴即做出了反应,语言能力和社交互动能力都有所提高。他的挫败感明显减少,他开始
适当地回答问题。约翰在开始治疗后大约一到两个月开始说话,说短句。他的社交互动也增加了,他
开始进行眼神交流
并能做出反应和遵循指示。他们在语言和社交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案例研究 2:理查德
理查德是一个五岁的男孩,被诊断患有自闭症。他没有语言能力。他的父母非常不愿意开始使用 LDN;然而,
当理查德五岁时,他们决定值得一试。理查德像往常一样开始服用 0.5 毫克,然后逐渐增加到 4.5 毫克。他开
始在白天变得非常焦躁不安,不再睡觉。我们决定将剂量减少到 3 毫克并重新评估。在一到两周内,他开始说
单个单词,在一个月到六周内,他开始用句子说话并提出他想要的东西。
强迫症强迫症(OCD) 是一种严重、普遍且最常见的慢性衰弱性疾病,其
特征是重复、仪式性和令人痛苦的想法、观念和行为,而患者通常对此几乎没有任何控制权。10 50%
的患者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发病,17% 的患者同时患有自闭症。
11
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 (SSRI) 作为单一疗法并不总是有效,即使剂量很高。80% 的
血清素是在肠道中产生的。自闭症儿童通常没有良好的饮食习惯,如果没有健康的肠道,产
生的血清素就会较少。12因此,如果一种药物依赖于血清素的存在,那么它怎么能指望对血
清素较少的患者起作用呢?当多巴胺拮抗剂加入 SSRI 治疗中时,治疗反应会更积极。
病历
诺亚 12 岁时来找我,他患有严重的焦虑症、强迫症和抽动症。顺便说一句,他排便稀便。抽动症是
我亲眼见过的最严重的。他刚刚被送进我们儿童精神病科住院,因为尽管服用了常规的抗焦虑药物,
他的症状仍然难以控制。如果他没有抽动,他就有强迫性思维和行为。诺亚无法上学。后来,他的母亲
不得不辞职,这给家庭带来了经济压力。我们开始
试验性 LDN 并滴定至 4.5 毫克。还发现他对 MTHFR 基因的 C677t 变体呈阳性(纯
合),并开始服用甲基化 B 族维生素。他的肠道问题通过谷氨酰胺和益生菌得到解决。我
总是建议益生菌至少含有三种不同的生物,儿童的菌落形成单位 (CFU) 为 100 亿,青少
年和成人的菌落形成单位为 200 亿。最后,几周后,诺亚能够在副反应的情况下重返学
校,抽搐几乎不存在。然而,此时他非常疲惫,无法在下午集中注意力。我早上给他开了
100 毫克的 CoQ10 和 100 毫克的磷脂酰丝氨酸。他现在积极参与学校活动,没有副反
应,也没有焦虑、抽搐或强迫性思维和行为。
焦虑
焦虑是儿童和青少年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事实上,在美国,有 7.1% 的 3 至 17 岁儿童被
诊断患有焦虑症,总数达到 440 万。13儿童表现出焦虑的方式有很多:逃避学校、攻击性、
害羞、疲劳、睡眠困难、疑病症(通常是腹痛)、抑郁、沮丧和遗尿,仅举几例。大约三分之
一的儿童患有行为问题或抑郁症等并发症。14焦虑常常伴有身体症状,如出汗、心悸、胸
痛、疲劳、头痛和呼吸急促。恐惧和焦虑是正常发育的一部分,并且具有适应性。
如果焦虑在六个月内无法解决,就会变得不健康,并引发不适当或不合理的行为。
大脑中有两个主要区域负责焦虑:位于大脑深处的杏仁核和海马体。人们认为,GABA
减少或谷氨酸增加是焦虑的原因。我们还知道,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也发挥着
重要作用。
一些可能导致焦虑的饮食因素包括:
低血糖:当血糖下降时,身体的一种补偿反应是释放皮质醇。肾上腺产生的皮质醇
会刺激胰腺释放胰岛素。当胰岛素释放出来而没有“食物”可供利用时,大脑
就会发出信号
人吃东西,因此血糖升高。此外,皮质醇也有补偿反应,释放肾上腺素和
去甲肾上腺素。当它释放时,会导致战斗或逃跑反应(焦虑)。我总是
确保年幼的孩子可以吃额外的零食,而年长的孩子则完全不吃午餐!
吃一顿含有健康脂肪的健康早餐会使饱腹感持续更长时间。此外,注意
儿童饮用的饮料中的糖摄入量也非常重要。食品标签上糖的其他常见
名称是葡萄糖、果糖、麦芽糊精、木糖和麦芽糖浆。
咖啡因:焦虑症患者对咖啡因的敏感度比不焦虑症患者更高。
15儿童通常饮用含有咖啡因的苏打水、巧克力
以及热茶和冰茶。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咖啡因对患有 ADHD 的儿童
有帮助,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谷氨酸钠 (MSG):谷氨酸是一种主要的兴奋性神经递质,是 GABA 的前体。它
对学习和记忆至关重要。谷氨酸钠是谷氨酸的衍生物,是一种添加到快
餐、罐装蔬菜、罐装汤和肉类等加工食品中的食品增强剂。
根据 FDA 的说法,摄入这种添加剂引起的症状 包括头痛、潮红、出
汗、面部压力或紧绷感、面部、颈部和其他部位麻木、刺痛或灼热感、
心悸、麻木和虚弱 被称为味精症状综合症。16
阿斯巴甜:阿斯巴甜是一种人工甜味剂,存在于全球 6,000 多种食品和饮料中。
在体内,阿斯巴甜代谢为天冬氨酸 + 苯丙氨酸 + 甲醇。
苯丙氨酸是一种神经递质调节剂,天冬氨酸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甲
醇很快代谢为甲醛,并通过尿液排出体外。17摄入阿斯巴甜后,多巴
胺和血清素的产生会减少。此外,阿斯巴甜会破坏血脑屏障,增加其通透
性并改变儿茶酚胺(如多巴胺)的浓度。阿斯巴甜代谢物会引起神经行为变
化。阿斯巴甜是
还会导致易怒、偏头痛、抑郁和空间定向能力下降。18睡眠不足也是青少年焦虑症的预
测因素。19研究表明,睡眠障碍与多种
精神疾病同时发生,包括焦虑和抑郁。20此外,三分之一患有焦虑症的儿童每周至少与他人同睡两
到四次。焦虑越严重,同睡的频率就越高。21
传统的焦虑症治疗方法通常包括抗抑郁药,这些药物可以增加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水
平。丁螺环酮可刺激血清素和多巴胺受体,而苯二氮卓类药物可增加 GABA 的利用率。
这些药物和其他抗焦虑药物的副作用包括嗜睡、镇静和思维混乱。体重增加是一种常见的副作用,
对于在社交场合已经焦虑的儿童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它们还会产生依赖性。除了肠道功能障碍(恶
心、腹泻或便秘)外,还可能出现头痛和性功能障碍。即使是儿童,也必须监测血压和心律失常。如果这
些还不够严重,还可能产生自杀念头。
焦虑的功能性治疗包括:
L‑茶氨酸200毫克,每天一至三次。
甘氨酸镁200毫克,每天两至三次。
B 族维生素复合物。由于所有 B 族维生素都处于微妙的平衡状态,因
此最好服用复合物,而不是服用单一的 B 族维生素。
叶酸。MTHFR 基因突变患者需要服用甲基化叶酸。
5‑HTP,每天 50 至 200 毫克,通常在晚上服用。
确保没有酵母菌过度生长或食物过敏。因为人们认为 80% 到 95% 的血清素是在肠道中
产生的,所以确保肠道正常运转很重要。
22
LDN 从 0.5 开始,逐渐增加至 4.5 毫克,具体取决于患者的反应。
病历
一名患有阅读障碍和整体学习障碍以及已知 MTHFR 基因突变的 13 岁年轻男子因严
重焦虑和失眠而就诊。他尝试了多种药物但均无济于事。他开始服用 LDN,从 0.5 毫克
开始逐渐增加至 4.5 毫克,并服用甲基化 B 族维生素。
一个半星期后,他的举止发生了变化。他变得更快乐、更少焦虑、更善于社交。他不再那么
叛逆、更少对抗,而且开始睡觉。此外,他的食欲得到了更好的控制。有一次,他尝试不服
用 LDN,破坏性行为再次出现。
熊猫
想象一下,某天晚上你哄孩子入睡,醒来后却发现孩子完全变了一个人。一个焦虑、好斗、
有强迫和/或强迫性想法或行为的孩子。一个突然出现严重的分离焦虑,很可能还会抽
搐。这就是患有与链球菌感染相关的儿童自身免疫性神经精神疾病的儿童通常的表现。
1998 年,Susan Swedo 博士首次发现了 PANDAS,她发现儿童突然出现行为异
常,包括抽搐和/或与近期 A 组 β 溶血性链球菌感染 (GABHS) 相关的强迫症。PANDAS
被认为是对 GABHS 的极端自身免疫反应。大约每 200 名儿童中就有 1 名患有
PANDAS 和 PANS。23 PANDAS 的平均诊断年龄在 4 至 13 岁之间,但 PANS 没有年
龄限制。两者的临床过程都是复发和缓解。PANS 可由任何感染引起。
PANS 还具有强迫症突然发作和/或严重限制食物摄入的特征。可能出现严重焦虑,通
常表现为分离焦虑。学习成绩突然急剧下降。已经接受过如厕训练的儿童可能会出现白
天遗尿。抽搐可能呈舞蹈样运动(手指伸展时,做出类似弹钢琴的精细动作)。*诊断是
排除性的。必须首先排除所有其他神经和医学原因。
儿童急性神经精神综合征 (CANS) 是一种新发现的综合征,与接触邻苯二甲酸盐、多
氯联苯和
重金属。其他原因包括自身免疫问题、创伤(脑震荡)和缺氧。
病理生理学
这种疾病过程是通过分子模拟发生的:人体产生自身抗体,攻击大脑的基底神经节。分子模拟是任
何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当人体将正常组织误认为“敌人”时,因为它与细菌或病
毒的一部分或受体之间存在某种分子相似性,并对其进行攻击。这会引起炎症,从而导致该区域功
能障碍 因此出现神经精神症状。在 PANS/PANDAS 的情况下,人体会错误地攻击大脑中的基底
神经节。基底神经节是位于大脑深处的一组神经元。它们负责协调自愿运动、习惯性学习和情绪。
习惯性学习就是重复行为,使之成为常规,无需思考。例如,如果你每天开车上班走同一条路,大多数
时候你甚至不会考虑转弯,直接到达目的地。基底神经节通常受三种神经递质的影响:GABA、多巴
胺和谷氨酸。
对于 PANDAS 患者,反复感染化脓性链球菌(A 组 β 溶血性链球菌)会激活炎症细胞因子
(IL‑6 和 TGF‑B1)。这些细胞因子反过来会激活化脓性链球菌特异性 Th17 细胞,从而增加大脑
多个区域的毛细血管通透性,从而允许自身抗体入侵。免疫球蛋白 G (IgG) 也会引起升高,导致钙调
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 II (CaMKII) 增加。24此外,有证据表明,化脓性链球菌感染引起的人类抗脑自
身抗体靶向多巴胺受体、溶血神经节苷脂和微管蛋白,以及 CaMKII 的激活。25在另一项研究中,
PANDAS 患者被分为两组,一组没有舞蹈样运动,另一组有舞蹈样运动。在没有舞蹈样运动的组中,
抗 D2R 抗体升高,但两组中 CaMKII 均升高,因此使其成为需要进
一步研究的生物标志物。26 PANDAS 的诊断依据是链球菌培养阳性或 Cunningham 组。如
果没有链球菌培养阳性,但链球菌抗体升高
怀疑指数,谨慎的做法是跟踪 ASO 和 DNase 滴度。ASO 滴度通常在感染后一至四周升高,DNase 滴度将
在感染后六至八周升高。如果随后出现爆发(症状复发或达到顶峰),链球菌不一定是罪魁祸首;任何感染
都可能导致爆发。
PANS 的诊断更具挑战性,因为任何感染都可能是病因。应检测莱姆病和莱姆病合并感染(如巴
贝斯虫病、埃⽴克体病、边虫病和巴尔通体病)的滴度。
支原体也是罪魁祸首,病毒性疾病包括单核细胞增多症、爱泼斯坦‑巴尔病毒和流感。直到今年,呼吸
道合胞病毒 (RSV) 通常只限于婴幼儿,但今年我遇到了两例青少年病例。
治疗
以下内容并非详尽的评论,而只是概述。对于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治疗方法的患者或医生,请参阅
PANDAS 医生网络(www .pandasppn.org)或 PANS 研究联盟的网站。
采用各种治疗方法取决于患者的严重程度。
有时,如果病情较轻,则需要采取观察等待的方法并提供心理支持。大多数医生会先使用抗生素,等待
血液检测结果。如果患者对治疗没有反应或复发率很高,则明智的做法是对所有家庭成员进行 A 组链
球菌检测。即使患者没有感染,通过家庭接触接触也足以引发症状。
以下建议基于 PANDAS 医师网络的建议:患者应接受全面的身体和心理评估。应包括心电图、脑
电图、血液化学和脑部 MRI
等基线研究。对患者及其家属的情感支持与医疗同样重要,必须⽴即开始。认知行为疗法似乎是对
所有相关人员最有效的方法。27
根据严重程度,强迫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攻击性行为、抑郁症、分离焦虑症
以及体重突然下降或食欲不振等症状可以且应该在必要时通过药物治疗。如果
有任何迹象
如果患者有自杀倾向,或者行为严重,则需要住院治疗。
学校的支持至关重要;然而,学校当局往往不知道这种疾病或持怀疑态度。学校的承认和理解对于学生的健康至
关重要,因为有时教师和工作人员比其他人更早目睹这种疾病的发作。必须通过 504 计划(其他健康受损)或个性化
教育计划 (IEP) 做出规定。例如,如果孩子的书写能力突然下降,使用抄写员会很有帮助,也可以让患者提交打字的作
业。有时作业可以延迟完成或根本不完成,而不会对孩子的成绩产生负面影响。患者的支持团队有责任确保满足这些
需求。
抗生素
在 PANS 和 PANDAS 病例发作时都可以使用抗生素。
最初,使用青霉素(包括 Augmentin)和头孢菌素。我认为 Augmentin 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它含有克拉维酸。最近的
文献发现,它具有极好的血脑屏障渗透性。此外,它还被发现具有抗抑郁作用,并能通过多巴胺释放减少焦虑。它还被
认为能够抑制神经毒素,从而导致神经元存活。28大多数临床医生治疗三周,然后重新评估。如果患者有反应,那么治
疗可能会持续两到四周。
如果患者过敏或在前两周内对治疗没有反应,则可以使用阿奇霉素或克拉霉素。
但是,必须注意 QT 间期延长的患者,因此需要进行初始心电图检查。对于已经服用延长 QT 间期的药物(如 SSRI、
抗精神病药物和精神活性药物)的患者,也禁用该检查。在初始治疗后,应在治疗后两到七天对患者进行再次培养。如
果培养结果呈阳性,则需要对患者进行再次治疗。
临床医生和家人必须警惕可能受到影响的家庭成员或密切接触者。
长期链球菌预防通常仅用于病情最严重的患者或复发性 A 组链球菌感染并出现多种神经精神并
发症的患者。
通过获取 IgG 和 IgM 滴度来检测肺炎支原体。
支原体感染与多种神经系统疾病有关,包括横贯性脊髓炎和图雷特氏症。IgG 滴度会持续升高,因此最
好观察 IgM 滴度。
莱姆疏螺旋体病以及合并感染(无形体、巴贝斯虫等)可用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目前的建议是,即
使是 8 岁以下的儿童也应使用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人们曾经认为,如果 8 岁之前的孩子服用大环内
酯类药物,会对牙齿产生不利影响,但现在人们不再相信这一点。
非甾体抗炎药
这些疗法适用于症状持续两周以上(尤其是症状恶化)的轻度至中度病例。治疗通常为六周或根据耐
受程度而定。
类固醇
对于轻度至中度病例,皮质类固醇可能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在前三天。治疗被认为是短暂的“爆发”,
因为只给予五天。如果患者在停止使用类固醇后复发,可以重新开始使用,然后可能再进行一次爆发或
更长的疗程,然后逐渐减少剂量。需要注意的副作用包括强迫行为恶化、焦虑、愤怒、激动、抑郁、情绪不
稳定或失眠。
中度至重度病例可静脉注射甲基泼尼松龙 3 至 5 天。如果最初反应良好,随后反应减弱,可加用静
脉注射免疫球蛋白 (IVIg)。也可单独使用 IVIg 1 至 3 天。
对于严重病例,7 至 10 天内进行 5 次单剂量 TPE(血浆置换)可提供最佳效果。29通过同时给予
IVIg 和/或短暂使用皮质类固醇,可以缓解低丙种球蛋白血症可能引起的副作用。
扁桃体切除术
PANDAS 患者的扁桃体中 Th17 物质的含量较高。动物研究表明,这种物质可以打开血脑屏障,从而使抗体穿透
大脑目标区域的血脑屏障。
血清素选择性再摄取抑制剂血清素选择性再摄取抑
制剂 (SSRI) 可能有助于治疗 PANS/PANDAS,作为强迫行为、焦虑和抑郁症的治疗方法。
A 组链球菌会在大脑中产生炎症细胞因子,而 SSRI 可以抑制这种细胞因子。SSRI 的起始剂量为常规剂量的
四分之一,然后逐渐增加。此外,如果患者的肠道不健康,SSRI 可能不起作用,因为体内 80% 的血清素是由肠道中
的有益细菌产生的。
请注意,黑框警告与 SSRI 的使用有关。
这些警告包括自杀想法和行为的风险增加。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必须⽴即但逐步停药,并仔细观察患者或住院治
疗。
抗真菌药物长
期使用抗生素的患者应谨慎监测口腔(鹅口疮)或阴道以及其他粘膜表面(如直肠和阴茎)的酵母菌感染情况。如
果出现这种情况,酵母菌感染(与任何感染一样)必须尽快处理。
抗组胺药
组胺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有助于控制睡眠‑觉醒周期以及能量和动力。抗组胺药有两种。两种都是抗炎药,也是
免疫调节剂。它们是H1阻滞剂,是典型的过敏药物,如苯海拉明、非索非那定等。H2阻滞剂在胃中起作用,名称为西
咪替丁和雷尼替丁。
抗组胺药对某些人有所谓的特殊反应。也就是说,它不会产生镇静作用(镇静作用对某些人是有益的),
患有失眠症(英语:patient expiry)的病人会因为该药物而变得焦躁不安。
低剂量纳曲酮
通常,我一开始给患者服用 0.5 毫克,睡前服用,然后每周增加 0.5 毫克,直到达到我们看到变化的
剂量,有时需要增加到 4.5 毫克才能获得理想的反应。LDN 会增加内源性脑啡肽和内啡肽,从而增
强身体的免疫功能。LDN 通过调节 T 常规细胞(一种抑制免疫反应从而维持体内平衡的 T 细胞,
以及抑制 T 细胞和细胞因子增殖)和产生 IL‑10 和 TGF‑B 来抑制促炎细胞因子,从而下调 Th17。
Th17 是一种增加脑血管通透性的物质,允许抗体穿透和攻击基底神经节。
病历
简是一名 19 岁的大学生。在她上大学的第一年,她开始出现恐慌症,尽管学习成绩很好,但
她还是想辍学。她在学校放假回家,经过全面检查后,确定她的 MTHFR 呈阳性,肺炎支原
体 IgG 和 IgM 呈阳性。医生诊断她患有 PANS,并开始服用 Augmentin 进行为期三周的疗
程。一周后,她的焦虑和恐慌症似乎减少到了可控的水平。我们决定继续服用 Augmentin
三周。假期结束后,她准备回学校,几乎兴奋不已。短短几周后,焦虑和恐慌症又复发了。她从
1 毫克的 LDN 开始,并迅速增加到 4.5 毫克。恐慌症再次消退,并且仍然非常容易控制。
青少年慢性疲劳综合症
大多数人将纤维肌痛和慢性疲劳综合征与成年患者联系起来。然而,儿童和青少
年患 CFS 的频率比预期的要高,而且其患病率正在上升。根据梅奥诊所的数据,
2% 至 6% 的学龄儿童受到影响。大多数是
这种病通常见于 13 至 15 岁之间的青春期女性,但我也曾在男孩身上诊断出这种病。30
儿童患上这种疾病的原因可能不止一个,尽管青少年慢性疲劳综合征的一个常见原因是由于欺凌、家庭
破裂、父母或兄弟姐妹死亡、学业压力、课外活动安排过多和社交媒体而导致的心理压力。另一个原因是身体
压力,如事故、脑震荡、过度训练或锻炼、线粒体功能障碍、手术或感染。
此外,MTHFR 基因变异会抑制人体处理叶酸的方式,这也是导致慢性疲劳的原因之一,因为活性叶酸是
三磷酸腺苷 (ATP) 合成的重要组成部分。ATP 是细胞产生能量所必需的,因此也是患者能量水平所必需的。
如果患者没有足够的活性叶酸,那么 ATP 就会缺乏,整体能量就会低。CFS 似乎也存在遗传倾向,因为 CFS
通常会影响多个家庭成员。
症状
青少年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会出现大面积疼痛(通常是钝痛),持续时间超过六个月,并且至少出现以下
四种症状。疼痛必须出现在横膈膜两侧以及横膈膜的上方和下方。头痛通常很严重且频繁。
患者睡眠障碍,入睡困难,难以保持睡眠。即使患者可以入睡,他们也经常会感到严重疲劳。睡眠中断时,经常
会出现睡眠呼吸暂停和不安腿综合征。此外,患者还会出现腹痛和认知障碍;还经常出现注意力缺陷多动症、
焦虑和抑郁。
诊断
1985 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和阿方斯·马西博士在《关节炎和风湿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临
床研究,该研究制定了诊断儿童纤维肌痛的标准。必须满足所有主要标准和 10 个次要标准中的
至少 3 个。31
主要标准包括至少三个部位出现持续三个月以上的全身肌肉骨骼疼痛,以及四到五个压痛点。
不存在类风湿性关节炎、莱姆病、单核细胞增多症等潜在疾病。患者的检查结果必须正常。
次要症状包括慢性焦虑或紧张、疲劳、睡眠不佳、慢性头痛、肠易激综合征、主观软组织肿胀和麻木
以及活动时疼痛、受天气影响或因压力和焦虑而加剧。
三十二
虽然没有明确的血液检查,但在综合医学中,通常会进行以下检查以排除其他疾病,例如全血细胞
计数 (CBC)、红细胞沉降率 (ESR) 和甲状腺研究:血清氨、乳酸、血清镁、肉碱、CoQ10 水平和 MTHFR。
治疗
青少年慢性疲劳综合征的治疗包括认知行为疗法和药物治疗,以控制疼痛并减轻焦虑和抑郁,具体视患者个
人需求而定。以下是针对青少年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的指南;但是,每位患者都应进行血液检查,并根据其检
查结果制定个性化计划:
如果确定缺乏,则服用甘氨酸镁 200 毫克,每天两至三次。
L‑茶氨酸 200 毫克,每天两至三次,可缓解焦虑,睡前服用可帮助
睡眠。
睡前服用 1 毫克褪黑激素以帮助睡眠。
每日 500 毫克肉碱。
每天服用 60 至 100 毫克 CoQ10。
如果氨水平高,可使用乳果糖糖浆:每天一至两次,每次一茶匙,直到大便稀软,以
减少氨。
对于存在MTHFR基因变异的患者,补充甲基化叶酸是必需的。
低剂量纳曲酮。大脑中的疼痛受体受到促炎细胞因子的刺激,而促炎细胞因子也是疲劳
的罪魁祸首。通过减少这些物质,疼痛和疲劳就会减少。33再次强调,治疗剂量
不同
对于每个病人来说,但我发现大多数都在3到4.5毫克的范围内。
病历
10 岁的保罗被诊断患有 ADHD,并且对所有药物均无效。他精疲力竭,每天七八点钟睡
觉,早上很早就醒来。即使他睡得晚一些,他仍然会在同一时间醒来。与他交谈后,他发
现这个聪明的 10 岁孩子经常说被其他孩子和老师欺负。学校的情况变得非常困难,以
至于学区同意他转学。在我看来,他没有 ADHD,但实际上患有严重的焦虑症和青少年
慢性疲劳综合症。他早晨的皮质醇水平很低,血清氨和乳酸水平很高。他开始服用
CoQ10,这是一种针对线粒体功能障碍的复合线粒体配方中的成分。保罗承认感觉好
多了,开始入睡了。他的焦虑症持续存在。他开始服用 LDN。起初他的妈妈觉得它不起
作用,所以停了下来。几个月后,妈妈要求重新开始,我们正在等待结果。
*舞蹈样运动必须与 Sydenham 舞蹈症相区别。Sydenham 舞蹈症发生在风湿热中,风湿热也是由 A 组 β 溶血
性链球菌引起的。这种疾病中存在舞蹈症,即大肌肉群的抽搐性、僵硬性运动,不重复或无节奏,经常伴有手足徐动
症,即扭动运动。
‑七‑
女性健康
OLGA L. CORTEZ,医学博士、妇产科医生、FACOG
低剂量纳曲酮在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方面与其他疗法一样,如今也为女性健康做出了贡献。那么,一个值得思考的
问题是:“如果你有一种药物可以逆转自身免疫性疾病并减少慢性感染的炎症,那么如何将其转化为治疗非自身
免疫性的盆腔问题?”我们将在本章中讨论的两种主要诊断 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多囊卵巢综合征 现已被证明
具有炎症成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理解的是,可以使用 LDN 作为传统医疗疗法的辅助手段来治疗这些疾病。
子宫内膜异位症 美国妇产科医师学
会 (ACOG) 将子宫内膜异位症定义为“一种子宫内膜组织(子宫内膜)长在子宫外的疾病”。1这通常会导致月
经期间出现严重的盆腔疼痛,并最终导致月经外的盆腔疼痛。传统上,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方法要么是激素疗
法(使用避孕药、孕激素宫内节育器或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要么是手术疗法(较为保守的手术是腹
腔镜检查,更为确定的手术是子宫切除术)。那么,为什么要尝试一种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药物呢?
在 PubMed 上搜索“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自身免疫”,会返回可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条目列
表。1987 年《妇产科》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表明,异常多克隆 B 细胞活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特征)与子
宫内膜异位症有关。2许多专家都认为子宫内膜异位症确实存在炎症成分。然而,将子宫内膜异位症当做
纯粹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来治疗,对患者来说是一种伤害,因为它是一种多因素疾病。子宫内膜异位症需
要多方面的治疗方法,但 LDN 可能是治疗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下是我的私人诊所的一些案例研究,展示了 LDN 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效果。
案例#1
患者是一名 23 岁的白人女性,长期患有盆腔疼痛和复发性膀胱感染。过去几年,她一直在服用避孕
药,这让她的疼痛有所缓解。她的盆腔超声检查结果正常,但她觉得自己患有持续性膀胱感染。一名泌
尿科医生为患者进行了疑似间质性膀胱炎的治疗。泌尿科医生提供的所有治疗方案都对患者没有帮
助。
当她来我的诊所就诊时,由于患者没有明确的诊断,她选择进行诊断性腹腔镜检查。
发现子宫内膜异位症并切除。一个月后,患者植入了 Mirena 宫内节育器,以继续控制子宫内膜异位症。
两个月后,患者报告盆腔疼痛和排尿困难复发。尿培养结果呈阴性。泌尿科医生给她开了 Elavil。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患者接受了疼痛管理专家的诊治。随后,她因生育原因取出了宫内节育器,几个月后
怀孕。在正常怀孕后,患者因分娩时分娩失败而接受了剖腹产手术。
患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进行母乳喂养。
产后一年,患者再次出现盆腔疼痛,体重意外增加。第二次盆腔超声检查结果正常。
鉴于她过去对传统疗法没有反应,我们向她提供了低剂量纳曲酮的试验,她接受了。
患者开始服用 LDN,剂量为每天一次 1 毫克,然后慢慢增加剂量。开始服用 LDN 三个月后,她
的疼痛明显减轻。她偶尔会出现膀胱疼痛。
患者目前已服用 LDN 两年多,盆腔疼痛得到良好控制。她目前的剂量是每天一次,每次 8 毫克。
案例#2
患者是一名 39 岁的西班牙裔女性,长期因子宫内膜异位症而出现盆腔疼痛。每次月经期间她都会
感到恶心和呕吐。患者过去曾尝试过避孕药和止痛药,但都没有显著缓解她的疼痛。她还接受了腹
腔镜检查,以切除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卵巢囊肿。
手术几个月后,她的骨盆疼痛再次出现。
几年前,患者在生育检查中接受了子宫输卵管造影检查。医生告知她,她的一条输卵管完全闭合,
另一条输卵管基本闭合。最近的盆腔超声检查结果正常。
在我们办公室进行初步实验室检查后,发现患者患有桥本甲状腺炎。因此,我们给她开了低剂量
纳曲酮,最初剂量为每天 0.5 毫克。我们每周将她的每日剂量增加 0.5 毫克,直到她每天服用 4.5 毫
克。三个月后,患者报告说她的月经周期不再疼痛。六个月后,患者要求再次进行子宫输卵管造影。她
的子宫输卵管造影现在正常,双侧输卵管通畅。
案例三
患者为 36 岁的白人女性,曾怀孕并分娩两次。她长期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
2010 年,在生下最后一个孩子后,她放置了 Mirena 宫内节育器。当时,这对缓解疼痛很有效。2015
年,她将 Mirena 宫内节育器换成了新的 Mirena。
患者于 2018 年初出现严重腹痛和腹胀,仅发生在每月 10 日/11 日和每月 23 日/24 日。她没
有月经,这是使用 Mirena 宫内节育器所预期的。疼痛发作期间,她每晚都会感到恶心和呕吐。三位
不同的胃肠病学家看过患者。她接受了内窥镜检查和结肠镜检查,结果均正常。她
然后接受了胆囊切除术,手术很顺利。医生告诉她疼痛可能是肠易激综合征引起的,但胃肠病医生
开的药都不起作用。考虑到她疼痛的周期性,我们确定这可能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引起的,于是第二次
更换了她的 Mirena 宫内节育器。
在为期两个月的随访中,患者报告疼痛程度有所减轻,但并未完全缓解。随后,我们为患者提供
了低剂量纳曲酮。我们一开始每天服用 1 毫克,每周增加 1 毫克。当她达到每天 4.5 毫克时,患者的
盆腔疼痛仍未缓解。因此,我们指示她继续每周增加剂量,直到达到每天 9 毫克。
服用低剂量纳曲酮三个月后,患者现在不再感到疼痛。
她的胃肠道症状也已消失。
案例四
患者是一名 23 岁的西班牙裔女性,之前没有怀孕过,她因严重的盆腔疼痛、无法控制的恶心和月经
期间呕吐而来我们诊所就诊。由于这些症状,她在月经期间只能待在家里。有时,她在月经前或月经
后也会出现盆腔疼痛。
患者做了盆腔超声检查,结果正常。我们讨论了她可能患有超声检查未发现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可
能性。
实验室检查显示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水平升高至 1.0。因此,患者被诊断为桥本甲状腺炎。医生建
议使用低剂量纳曲酮作为治疗方案,患者接受了。她最初每天服用 0.5 毫克,每周增加剂量,直到每
天服用 4.5 毫克。
三个月后,患者表示经期期间骨盆疼痛持续存在,但已有所改善。恶心感轻微,未伴有呕吐。甲状
腺球蛋白抗体水平不降反升,达到 1.6,因此我们将她的剂量增加至每日 9 毫克。
又过了三个月,她的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水平为零。
现在,她月经期间骨盆疼痛非常轻微,不再有恶心或呕吐的症状。她对这些结果非常满意。
多囊卵巢综合征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将多囊卵巢综合征 (PCOS)
定义为“一种以雄激素过多、排卵功能障碍和多囊卵巢为特征的疾病”。3患有这种疾病的患者会出
现一系列症状,包括闭经或月经过多、多毛、痤疮、胰岛素抵抗、代谢综合征和肥胖。这种疾病的传统治
疗方法包括联合激素避孕、仅孕激素疗法、胰岛素增敏剂(如二甲双胍)和生活方式改变(饮食和运
动)。可根据患者的需要添加其他疗法。例如,螺内酯等抗雄激素药物可用于治疗多毛或痤疮,而克罗
米芬或来曲唑可用于诱导想要怀孕的患者排卵。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治疗困难在于其病因尚不清楚。
有研究表明纳曲酮可以作为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及其相关并发症的辅助治疗或单独治疗。
例如,1997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对于克罗米芬柠檬酸盐抵抗性无排卵患者,单独使用纳曲酮或将
纳曲酮与抗雌激素联合使用可成功诱导排卵。”4
低剂量纳曲酮可安全地与激素避孕药、胰岛素增敏剂、抗雄激素药物或促排卵药物一起使用。
以下是一些证明 LDN 对 PCOS 患者效果的案例研究。
案例五
患者是一名 28 岁的女性,在来我诊所就诊的 10 年前被诊断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她之前曾服用过
避孕药,并接受了腹腔镜卵巢囊肿切除术。患者不喜欢避孕,因为避孕会导致她情绪波动和经间期出
血。她还患有复发性膀胱感染,她正试图找泌尿科医生治疗。当她来我诊所就诊时,她没有服用任何
避孕药,盆腔超声检查结果与多囊卵巢综合征相符。
患者当时被诊断患有桥本甲状腺炎,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水平为 2.1。她被建议使用低剂量纳曲酮
作为治疗选择。她开始以每天 0.5 毫克的剂量服用 LDN,并慢慢增加剂量,直到每天达到 4.5 毫克。三个月
后,她的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水平为零,并保持了一年多。患者还出现了正常的月经周期,自开始服用 LDN 以
来,在过去 12 个月中只发生过两次膀胱感染。
案例六
患者是一名 24 岁的女性,由于想要怀孕,她在使用避孕药数年后停止了避孕。停止避孕 9 个月后,她因盆腔
疼痛和月经不调来到我们办公室,并被诊断出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在讨论了治疗方案后,患者决定在 2018
年秋季尝试使用 Clomid 来诱导排卵。在服用 Clomid 未能怀孕后,患者尝试了无麸质、无乳制品、无糖饮
食。她仍然没有怀孕,但减掉了大约 15 磅(6.8 公斤)。此时她的月经间隔时间仍然很长 33 至 47 天。到
2019 年 4 月,她的抗苗勒氏管激素 (AMH) 水平为 7.75(大于 6 表明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患者选
择尝试低剂量纳曲酮。她开始每天服用 2.25 毫克,然后滴定至每天 9 毫克。到 2019 年 10 月,她的 AMH 下
降到 4.32。现在,她无需服用 Clomid,月经周期就很正常。
案例七
患者是一名 27 岁的女性,已知患有桥本甲状腺炎,她因尝试怀孕 8 个月后仍无法怀孕而来我们诊所就诊。盆
腔超声检查发现患者有多个双侧外周卵泡,符合 PCOS 的症状。她当时的 AMH 为 10.2。她一直在改变饮食
习惯并补充营养以降低甲状腺抗体数量。考虑到她渴望怀孕,她同意尝试 LDN。尽管我们正在治疗她的
PCOS,但由于她患有桥本甲状腺炎,我们开始给她每天服用 0.5 毫克,每周增加剂量,直到达到每天 4.5 毫
克的剂量。九个月后,患者自然流产。
随后,她对这个过程感到失望,并停止了 LDN。在生殖医学专家的监督下,她近一年没有怀孕。
内分泌科医生同意重新开始使用 LDN。此时,由于副作用,她无法再忍受 LDN 片剂。因此,我们给她
换成了 LDN 乳膏。我们再次从每天 0.5 毫克开始,每周增加剂量,直到她达到每天 4.5 毫克的剂量。
患者现在的月经周期正常,甲状腺过氧化物酶 (TPO) 抗体水平低于以往任何时候。在此期间,她还从饮食中
剔除了咖啡因、麸质和人工甜味剂。
荷尔蒙变化
过去几年,我们用 LDN 结合其他药物治疗各种疾病的患者,因此我们经常发现患者血液中的激素
水平发生变化。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变化对患者具有临床意义。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很缺乏,但我私
人诊所的一项案例研究证明了这种结果的潜力。
案例#8
患者是一名 37 岁的西班牙裔女性,之前没有怀孕过,从未使用过避孕措施,但想要怀孕。她说她每
个月来一次月经。她的月经期通常持续 10 天。月经的前四天会出现大量出血,并伴有血块从阴道排
出。超声检查显示她的子宫壁内有一个 5 厘米的子宫肌瘤,但其他方面均正常。她补充说,她的月经
周期非常痛苦。
她的初步血液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
促卵泡激素 (FSH):16.6 雌二醇:58.8 睾酮:3 孕酮:3.0 AMH:
0.306
考虑到她想要生育,医生给她做了子宫输卵管造影,结果显示正常。此时医生讨论了治疗方案。
患者决定尝试低剂量纳曲酮。患者最初每天服用 2.25 毫克,后来增加到每天 4.5 毫克。(医生指示
她将 LDN 剂量增加到超过这个剂量,但她选择在 4.5 毫克时停止服用
每天。)三个月后,她报告说她的月经不再疼痛。她三个月的随访血液检查显示如下:
FSH:6.8 雌
二醇:90.0 睾酮:9
孕酮:0.3(月经期间)
抗苗勒氏管激素(AMH): 0.535
她的雌激素水平上升,而 FSH 水平则相应下降,睾酮水平略有上升,更重要的是,仅三个月后,AMH 水
平就上升了。医生指示她将低剂量纳曲酮的剂量增加到每天 9 毫克,并在三至六个月后再次进行随访。她的
下一组实验室检查结果如下:
FSH:5.4 雌
二醇:559.4 睾酮:7 孕
酮:6.6 AMH:0.488
再次,她的雌激素水平有所改善,但没有任何改善
她的睾酮或 AMH 水平。
这个案例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通常,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会做进一步的检查(全面的粪便研究、
食物不耐受测试、慢性感染测试等)。然而,患者是自费的,资金有限,因此无法承担任何进一步的检测来确
定炎症的潜在来源。最后,虽然低剂量的纳曲酮可用于减少整体炎症,但如果患者的炎症来源没有得到解决,
那么长期来看,病情改善的可能性较小。
生育能力变化
不孕不育是一种复杂的疾病,有多种促成因素。
虽然 LDN 不能归类为不孕症药物,但已证明它有助于提高生育能力。1993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服用
25 至 150 毫克纳曲酮可“使 66 名患者中的 49 名月经周期完全正常化”。此外,“在 16 名患者中
在接受不孕症治疗的研究中,有 18 例实现了怀孕。”5
案例#9
该患者是一名 38 岁的西班牙裔女性,有两个孩子,分别为 21 岁和 17 岁。自从
生下 17 岁的孩子后,她就没有采取任何形式的避孕措施。
患者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已有多年,体重一直难以减轻。月经不规律,每两到四个月一次。患者因高
血压无法耐受避孕药。
她拒绝使用其他仅含孕激素的避孕方法。她已经服用二甲双胍好几年了,因为她正在努力减肥,而
且没有
成功。
患者的初级保健医生发现她的尿酸水平升高。随后,医生为患者提供了低剂量纳曲酮作为可能
的治疗选择。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她的体重从 250 磅(113.4 公斤)下降到 215 磅(97.5 公斤),
而饮食和锻炼习惯没有改变。在此期间,她的月经周期也恢复正常,尿酸水平从 8.3 降至 6.3。39 岁
时,她意外怀孕。在服用 LDN 期间,她的月经仍然正常。
给药方案下面我将列出我们自
2016 年与 LDN 合作后在我们的诊所 Cross Roads Hormonal Health and Wellness 开发的
方案。
我们指导患者早上或晚上都可以服用 LDN。
0.5 MG 协议
对于此方案,我们让患者从每天一次 0.5 毫克开始,每周增加 0.5 毫克的日剂量,直到达到每天 4.5
毫克的目标。
这种方案通常只适用于桥本甲状腺炎患者,或任何可能容易出现药物副作用的患者。我们发现
一周的时间足以让大多数患者适应给定的剂量,但这种滴定可以根据需要放慢。我曾让患者在能够
耐受增加剂量之前,坚持服用给定剂量一到三个月。给药方案应根据患者量身定制。如果患者感觉
每天服用 2 毫克效果很好,但每天服用 2.5 毫克时会出现头痛或疲劳,然后恢
复到每天服用 2 毫克的剂量。患者可以保持该剂量至少一个月,然后再尝试增
加剂量。
1 MG 协议
对于该方案,我们让患者从每天一次 1 毫克开始,每周增加 1 毫克的日剂量,直
到达到每天 4.5 毫克的目标。
这种给药方案适用于不易出现副作用的非桥本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这是我们目前在诊所使用的
三种方案中最不常用的方案。
2.25 MG 协议
对于该方案,我们让患者从每天一次 2.25 毫克开始,每周增加 2.25 毫克的日剂量,直到达到每天 9 毫
克的目标。
这是我们的妇科患者最常用的方案。
再次强调,剂量滴定应根据患者情况量身定制。如果患者无法耐受 2.25 毫克的
初始剂量,那么我们会将患者转换为 1 毫克方案或 0.5 毫克方案,并按照较慢的
时间表滴定剂量。
与其他两种方案不同,该方案将使患者每天的剂量达到 9 毫克。根据我们的经验,许多妇科疾病需
要更高剂量的 LDN 才能看到对炎症成分的影响。
不同的复合配方
在我们的诊所,我们让所有患者开始服用 LDN 片剂,而不是胶囊。我们发现患者服用胶囊后出现副作
用的风险更高。我们从服用胶囊的患者那里听说的最常见副作用是头痛、疲劳加剧和肿胀。如果患者希
望改用胶囊,我们会等到他们达到剂量目标,并警告他们服用胶囊可能会出现服用片剂时不会出现的副
作用。
如果患者无法耐受 LDN 片剂,即使剂量为 0.5 毫克,我们也会将其转换为透
皮 LDN 乳膏。然后,我们会像片剂剂量一样,使用上述方案增加乳膏剂量。在我们
的实践中,我们不会尝试将使用 LDN 乳膏的患者转换为口服
配方,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对口服药片产生耐受性。
桥本氏病妇科疾病的给药方法
甲状腺炎
对于患有这种合并症的患者,我们始终遵循 0.5 毫克的方案,并在他们达到每
日 4.5 毫克的所需剂量后对其进行监测。
请记住,每天服用 4.5 毫克并不能改善许多妇科疾病。我们通常需要继续调整剂
量,直到接近每天 9 毫克,具体取决于患者的耐受程度。
妇科疾病的剂量
桥本甲状腺炎自身免疫性疾病
对于这些患者,我们谨慎行事并使用 1 毫克方案。
2.25 毫克方案是另一种选择,但对于这类患者来说可能剂量太大、速度太快。同样,我
们逐渐将剂量增加到 4.5 毫克/天,因为我们知道患者可能需要继续将剂量增加到 9
毫克/天,才能看到妇科症状有所改善。
结论低剂量纳曲酮已被反
复证明对于患有炎症性疾病(包括多囊卵巢综合征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来说是安全有效的。由
于我们正在寻求扩大女性保健领域的治疗选择,因此进一步研究低剂量纳曲酮可能会带来令人兴奋
的可能性。
‑八‑
创伤性脑损伤
SARAH J. ZIELSDORF,医学博士,理学硕士
医学界对头部损伤存在许多误解,尽管我们的知识正在迅速扩展,新的研究正在导致治
疗模式发生重大转变。创伤性脑损伤 (TBI) 是指任何由外部机械力引起的脑部病变(包
括脑功能改变)。近年来,TBI 分类已细分。最常见的 TBI 形式是轻度创伤性脑损伤
(mTBI),美国康复医学会 (ACRM) 将其定义为由外部物理力量作用于头部的机械能所
导致的急性脑损伤,并伴有以下任何症状:意识丧失 (LOC) 不超过 30 分钟、创伤后遗忘
症 (PTA) 不超过 24 小时、受伤后 30 分钟(或就诊时)格拉斯哥昏迷量表 (GCS) 评分
大于或等于 13、一段时间(持续时间未指定)的意识混乱/定向障碍,或其他短暂性神经
系统异常,如局灶性体征或癫痫发作。1轻度 TBI 进一步分为“复杂性”和“无复杂性”的
子类别。这些类别由计算机断层扫描 (CT) 异常的存在与否决定。多达 10% 的急诊科患
者在出现影像异常(蛛网膜下腔出血、颅内挫伤或小的脑外血肿)时,患有复杂的 mTBI。
GCS 为 13 至 15 被认为是轻伤,9 至 12 被认为是中伤,8 或以下被认为是重伤。2虽然
大多数 TBI 临床试验使用 GCS 作为纳入的主要选择标准,但该评级系统并未提供导致神
经系统缺陷的病理生理机制的具体信息。
由于大多数 mTBI 患者的损伤在 CT 扫描等影像学检查中无法看到,因此 TBI 表现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对于寻找有效且有针对性的治疗干预措施而言是一项极其重大的挑战。因此,增
强的分类策略可能有助于验证特定的治疗策略。有人提议,应使用基于个体脑损伤病理解剖
特征的新 TBI 分类来选择临床试验中的患者,因为这些特征可能具有共同的细胞和组织病
理生理机制。这种多维方法将寻求建⽴一种“有针对性的损伤类型”。3这样一来,临床医生
将有更多具体而客观的标准来对 TBI 患者进行分类。
疾病负担
由于大多数轻度 TBI 患者都未得到治疗,因此全球 TBI 的经济成本几乎无法计算。2009 年
的一项研究估计,仅在美国,TBI 的总成本(包括致命病例、需要住院治疗的病例和未治疗
的病例)就超过 2210 亿美元。TBI 的流行主要针对体格健全的男性劳动力,预计将成为全
球主要死亡原因之一。4高达 90% 的 TBI 病例被归类为轻度,但高达 25% 的 TBI 患者无
法完全康复。这些人患有慢性神经认知障碍。从历史上看,主要的 TBI 病理无法通过成像
检测出来。但现在,代谢成像技术让我们能够看到 TBI 患者中发生的弥漫性脑炎症,以及神
经退行性病变的可能性。
据估计,美国有 530 万人患有长期 TBI 相关残疾。罹患 TBI 风险较高的特殊人群包括
军人和参与接触性运动的运动员。饮酒是 TBI 的另一个风险因素。
复发性 TBI 极为常见 高达 13.2% 的运动性头部损伤是复发性的。近 90% 的军人
遭受 TBI 的人员通常会同时出现精神疾病。5最常见的 TBI 后损伤是精神疾病的发展或
恶化,包括抑郁、焦虑和情绪障碍。这可能导致生活质量整体下降,长期发病率和死亡率
增加。在一项对 60 名 TBI 患者进行 30 年随访的研究中,近一半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仅
在 TBI 后才开始出现症状。6
脑震荡和脑震荡后综合症 我们需要新的术语吗?
脑震荡是一个过时的、笼统的术语,指的是具有持续症状的头部损伤。关于它的定义没有
共识,而且这个术语与病理学没有任何关联。论文标题“脑震荡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困
惑”最能说明这一点。脑震荡这个模糊的术语导致诊断的不确定性、不可重复的科学、糟
糕的临床指南和决策中的潜在错误。神经病学家、运动医学专业人士和其他人员越来越
多地对 TBI 症状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类,然后准确诊断潜在的创伤后症状。梅奥系统根据
LOC 持续时间、GCS 评分和创伤后遗忘持续时间的传统测量方法来对 TBI 症状的严重
程度进行分类。神经影像学结合了损伤严重程度的测量,将大多数轻度 TBI 患者分为两
组,即轻度(可能)和有症状(可能)TBI。这凸显了 mTBI 的异质性及其可能的各种神
经病理学。7与脑震荡一词类似,脑震荡后综合征 (PCS)一词缺乏特异性。急性损伤后症
状的存在,包括头痛、头晕、对光或噪音敏感、复视或耳鸣,与这些症状的持续存在有关。
此外,早发性脑震荡后症状(TBI 后一周至一个月)始终与症状的持续存在有关且高度
相关。2015 年对 103 名 mTBI 患者的一项研究发现,82% 的患者在受伤后一个月报告
了脑震荡后症状。研究结果表明,“一个月内出现症状是脑震荡后症状的重要预测因素
一年后出现症状,抑郁症与一个月和一年后的 PCS 显著相关。”8 《精神障碍诊断和统
计手册》第四版和第五版 (DSM IV/V) 和国际
疾病分类 (ICD‑10)对 PCS 的临床定义不明确。这将 PCS 归类为 TBI 后的持续性神
经认知障碍,这进一步妨碍了对患者的准确风险分层、识别、诊断和管理。这些模糊的定
义和分类系统加剧了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提供治疗标准护理的艰巨任务。此外,TBI 表
现的多变性和影响预后的因素范围决定了患者是否能从最初的脑外伤中完全康复。例
如,一项针对 mTBI 患者的队列研究发现,64% 的患者在受伤三个月后符合 ICD‑10 的
PCS 标准,而只有 11% 符合 DSM‑IV 标准。9
PCS 是专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症状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和发病时间各不相同,
这使得量化病情变得极具挑战性。此外,这些症状不具特异性,与未受脑损伤的患者(包
括颈椎扭伤患者,甚至健康人)报告的症状重叠。最后,出现 PCS 症状的患者有时会被临
床医生指责为装病、夸大其词、错误归因和回忆偏差,他们可能会否认脑震荡后症状的存
在。10
PCS 症状与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的过度兴奋方面有显著的重叠,包括易怒、注
意力不集中和睡眠困难。军事人员最常报告同时患有 PTSD 和 PCS。11一项针对 534
名成年 TBI 患者和 827 名对照者的前瞻性研究得出结论,mTBI 是 PTSD 的重要预测
因素,但不是脑震荡后症状的重要预测因素。更令人困惑的是,近 50% 的 PCS 患者之
前被诊断出患有行为健康问题,包括抑郁和焦虑。女性更有可能报告持续的 TBI 后症
状。具体而言,包括高焦虑敏感性、低弹性和应对技巧差在内的症状与 PCS 的发展最密
切相关。目前没有
12
这些肠上皮细胞介导粘膜免疫系统与小肠内部(腔内侧)接收的产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哪些分子可以穿过
屏障。
奇特的
令我失望的是,我的许多同事(包括胃肠病学家)都告诉我的病人,他们没有“肠漏症”。肠漏症并非自然疗法/
补充/替代疗法从业者的诊断,而是指有据可查的肠道通透性过高。肠粘膜屏障由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上皮细胞组
成。
经过验证的模型可以预测受伤后第一周内 TBI 后持续症状风险的患者。
我们现在知道,肠道通过胃肠道 (GI) 衍生的激素分泌、辅因子产生以及被称为细胞因子的信号来影响血脑屏障
(BBB),这会导致血脑屏障通透性或“脑漏”。14
的
免疫系统对肠道的双向调节和上皮细胞层对免疫系统的双向调节是维持体内平衡的基础。当体内平衡被破坏
时,肠道通透性增加被认为会引起慢性炎症和疾病的连锁反应。13另一道屏障是血脑屏障 (BBB),它保护大脑免
受外来或国内敌人的侵袭。它既是守门人,又是过滤器,允许有益的蛋白质、营养物质和信息通过,同时阻止有害
分子。个体的肠道菌群 (或微生物组) 和肠道屏障以及运输蛋白在血液通透性屏障的界面上起作用,帮助调节大
分子在消化环境和
宿主之间的移动。生活方式因素 包括睡眠、压力、抗生素使用、饮食和创伤 塑造了个体的肠道微生物群。
细菌、病毒、真菌,甚至原生动物和寄生虫都构成了一个代谢和激素活跃的微生物生态系统。该微生物群与肠道
相关淋巴组织 (GALT) 共生,以维持消化系统和神经/认知功能之间的锁相关系。
肠漏等于脑漏
健康的血脑屏障对于大脑的最佳功能和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如果大脑渗漏(血脑屏
障渗透性过高),就会导致神经炎症。这与多种疾病有关,包括但不限于抑郁、焦虑、认知
障碍、脑雾、头痛、偏头痛、慢性疲劳综合征、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精神分裂症、
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15
许多因素都会导致脑漏,包括慢性全身炎症、氧化应激、自身免疫性疾病、慢性心理应
激、感染、不良饮食(高度加工、高脂肪、营养不良的饮食添加剂)、睡眠‑觉醒周期紊乱、
过量饮酒、重金属暴露和其他环境毒素。16慢性外周炎症被认为是导致严重精神疾病的
失衡的根本原因,继发于促炎细胞因子升高。通常清理正常细胞功能产生的废物的细胞
被称为活性氧 (ROS) 或活性氮 (RNS)。在正常水平下,这些产物对大脑小血管(内皮毛
细血管)内壁细胞有益。但在长时间处于高水平时,ROS 和 RNS 会引起炎症(分别称为
氧化应激和亚硝化应激),并可能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和 BBB 损伤。17
连蛋白、麸质和肠漏症/脑漏症
治疗标准是只有患有乳糜泻的患者才应严格保持无麸质饮食。但是,我建议我的所有患
者都食用营养丰富、未经加工且无麸质的饮食 这一建议让我受到了很多批评。我非常
关心保持肠道屏障和血脑屏障的稳定性。麸质 小麦、黑麦和大麦谷物中的一组蛋白质
已被证明会增加连蛋白。18连蛋白是一种调节细胞间紧密连接的蛋白质。因此,连蛋白
的破坏会增加肠道屏障和血脑屏障的通透性。19在美国,我们的小麦通常是杂交品种,我
们的免疫系统无法识别这种品种,而且还大量喷洒了包括草甘膦在内的炎性除草剂。研
究表明,草甘膦是导致
乳糜泻发病率不断上升,因为它是一种强大的微生物群破坏者和毒素。20讨论了 zonulin 产量增加与麸质
摄入之间的关联,但结论仍然
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建议从饮食中去除麸质”。21尽管有这样的坚持,但乳糜泻背后有大量的研究
支持,而且临床已经证实乳糜泻与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之间存在关联。众所周知的乳糜泻介导疾病包括小
脑性共济失调、周围神经病变、癫痫、痴呆和抑郁症。此外,现在人们认为神经系统症状可能是肠外麸质敏感
性的临床表现。例如,案例研究显示麸质敏感性会导致大脑白质发生明显变化。22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人并
不需要患有肠道病理(肠病)才能出现乳糜泻或非乳糜泻相关症状。一种极具争议的疾病被称为非腹腔麸
质敏感症 (NCGS),是导致神经系统综合症(尤其是小脑共济失调)的常见原因。非腹腔麸质敏感症表现为
高水平的抗麦胶蛋白抗体,麦胶蛋白是麸质中的一种蛋白质。接触麦胶蛋白不仅会增加肠道通透性,而且血
脑屏障也会因此变得更具通透性。我们建议对似乎对麸质敏感但没有遗传易感性或乳糜泻检测呈阳性的患
者进行排除饮食。
麦胶蛋白不易消化,既能诱发应激反应,又能触发先天免疫系统反应 也许这就是麸质不耐受的原因。最
后,猴子研究重现了西方饮食、正常衰老过程和漏肠病理,表明肠道屏障破坏并不会导致乳糜泻。23对 NCGS
的研究结果不一,需要进一步研究以评估无麸质饮食的功效,并解决麸质敏感性神经系统病理的潜在机制。
24
微生物组和肠脑轴:双重
韦街
微生物群不仅会对大脑产生巨大影响,血脑屏障的破坏也会影响微生物群,从而导致恶
性循环。几十年来,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已经了解了手术引起的生理变化、全身炎症和肠
道细菌病理变化之间的联系。
创伤、烧伤、败血症(全身性感染)和手术损伤可导致一系列肠道屏障变化、肠道运输问
题、营养吸收不良和肠道菌群失衡(称为肠道菌群失调)。肠道菌群失调是全身炎症反
应的强大诱因。机会性微生物的过度生长通常可能不是问题,但不稳定的微生物群加上
损伤更类似于感染状态。微生物群在受伤后数小时内就会被破坏;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受伤患者的健康菌种减少了 1,000 倍。败血症患者的肠道菌群多样性实际上会降低到
病原体可以繁殖并引发个体更严重的疾病状态的程度。肠壁损伤会导致粘膜屏障发炎
和代谢环境改变,进一步有利于潜在危险细菌(如铜绿假单胞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
球菌和肠球菌)的生长。25一项研究表明,这种毒力的增加与脓毒症相关死亡率相关。
肠道细菌可能是维持肠道黏膜屏障的最重要因素,此外还有消化酶和胰腺和肝胆系
统的产物、肠道神经系统(肠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微生物群、肠道和大脑之间的
双向高速公路的主要连接点是脑神经 X,即迷走神经(被称为迷走神经,因为它是最长
的神经,并且支配着胸部和腹部的器官)。
改善迷走神经功能可增强副交感神经系统,该系统负责调节休息和消化。对于因神经炎
症而大脑火热的人,或因交感神经系统对感知到的威胁作出反应而处于战斗或逃跑状
态的人,迷走神经功能是一种解药。
肠道微生物群不仅调节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还通过神经内分泌途径靶向激素并产
生细菌衍生的代谢物。这种微生物群‑肠道‑大脑轴
影响神经递质的产生和传递,以及与神经精神疾病相关的异常行为。因此,调节该轴应
成为神经精神疾病的首要任务。
人类微生物群的滋养或破坏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遗传、健康状况、出生方式和环境。
最重要的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可改变因素之一是饮食结构和营养状况。26特定的肠道
菌群组成会影响身体组成,并对代谢健康和疾病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例如,与肥胖本身
相关的微生物组变化可能会导致与肥胖及其相关病理相关的内分泌、神经化学和促炎
状态的变化。
二十七
TBI 的病理生理学
脑损伤后,连接粘膜上皮细胞的紧密连接功能失调,使食物抗原等大分子进入血液,激
活免疫系统。脑损伤后数分钟内,粘膜内层就会萎缩并坏死。
同样,血脑屏障的紧密连接会瓦解,神经炎症化学物质会进入并造成破坏。脑损伤通常
会导致免疫系统过度活跃或活跃不足,从而分别导致自身免疫或免疫功能低下。TBI
可引发自主神经功能障碍(交感神经系统激活)、内脏感知和处理障碍以及肠道蠕动
受损。
二十八
在 TBI 之后,由于损伤的压力,下丘脑‑垂体‑肾上腺 (HPA) 轴会⽴即急性激活。
这表现为 mTBI 或中度 TBI 后一至两天内循环血浆皮质醇水平升高。然而,在严重
TBI 后,基线血清皮质醇水平在受伤后一至三天内下降。抑制 HPA 轴激活可能会导致
更严重的 TBI 后的结果更糟,即使炎症反应可能会减弱。由于许多人在 mTBI 后不寻
求任何医疗,因此轻度损伤引起的内分泌功能障碍发生的频率可能比目前认识到的要
高得多。筛查内分泌系统的激素异常并不是治疗的标准
TBI 后,这些通常无法诊断出来。此外,TBI 后的 HPA 轴抑制或功能障碍可能发生在
HPA 轴的任何水平 下丘脑、垂体或腺体水平。TBI 后,垂体极易受到功能障碍和损伤
引起的压力变化或出血的影响。由于垂体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 并刺激肾上
腺合成皮质醇,因此垂体功能障碍通常会导致 ACTH 释放减少,从而减少皮质醇的产
生。TBI 后患者的皮质醇水平降低与死亡率增加有关。HPA 轴失调也是神经炎症的一个
因素。总之,这些机制与 TBI 后精神症状的发展或恶化有关。皮质醇是一种糖皮质激素
类固醇激素,通过边缘系统调节动机和情绪。重度抑郁症的特征是与 TBI 后相同的变
化,即 HPA 轴过度活跃和反馈抑制中断。皮质醇分泌减少会导致疲劳、虚弱、体重减轻、
学习和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和易怒 PCS 症状。29 TBI 涉及两个阶段:原发性损
伤和继发性损伤。损伤本身的机械力会造成原发性损伤。这包括轴突剪切、出血和挫伤,
严重程度从轻度到中度或重度不等。继发性损伤是由创伤引起的长期炎症过程引起的间
接阶段,包括肿胀或血流变化。继发性损伤的例子包括通过分子过程导致的神经元损伤
和退化,包括线粒体功能障碍、氧化损伤和神经炎症。
持续性神经炎症与损伤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展有关。许多细胞类型都会导致 TBI 后
的神经炎症反应,但最重要的可能是小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介导的炎症与 TBI 后的许
多症状有关,包括运动障碍、情绪障碍和神经退行性疾病。30
小胶质细胞的作用
作为中枢神经系统 (CNS) 的巨噬细胞(细胞吞噬者),小胶质细胞是免疫系统的第一
道防线。尽管
小胶质细胞仅占成人中枢神经系统细胞总数的 10% 到 20%,但它们在个体一生中对
保护中枢神经系统至关重要。31在非活动或“静止”状态下,小胶质细胞实际上会以动
态方式改变其形态,在短短几分钟内收缩运动过程。研究人员正在努力了解小胶质细胞
在出生后如何发育,并已证明小胶质细胞参与成人神经元可塑性和神经元回路功能。32
为了应对 TBI,小胶质细胞会迁移到受伤部位,并通过吞噬细胞和分子碎片来清除它
们。这些被激活的小胶质细胞会释放有害化学物质,包括促炎细胞因子和活性氧和氮物
质,并通过释放谷氨酸引起持续的神经兴奋。这种兴奋性神经递质会造成更大的损伤,
并先于神经退化。小胶质细胞激活在 TBI 中的作用比之前描述的更加微妙。研究表明,
小胶质细胞以不同的表型被激活,这对应于神经毒性 (M1) 或神经保护 (M2) 启动状
态。这是一种复杂的反应,因为小胶质细胞会获得不同的激活状态来调节这些细胞功能。
在激活 M1 表型后,小胶质细胞会产生促炎细胞因子和神经毒性分子。
这些信号会促进炎症和细胞死亡。相反,当小胶质细胞呈现 M2 表型时,它们会触发抗
炎基因产物和营养因子的分泌,从而促进修复和再生并恢复体内平衡。33目前没有针
对性的药物作为标准治疗方法,将持续激活的小胶质细胞恢复到静止、非活动状态。一
旦激活,它们将继续以这种促炎方式发挥作
用,最终耗尽并经历细胞死亡。这令人担忧,因为它增加了进一步神经退化的风险。
低剂量纳曲酮作为小胶质细胞调节剂
低剂量纳曲酮是一种强效的小胶质细胞调节剂,其使用可能有助于预防 TBI 相关的神
经退化和免疫功能障碍。LDN 对非阿片类受体(如 Toll 样受体 (TLR))具有拮抗作用。
TLR 由不同的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 (PAMP) 激活,包括细菌、病毒和真菌的成分。
LDN 阻断 TLR‑4,最近发现它可以抑制 TLR 7/8 和9.34 TLR‑4 存在于巨噬细胞(包
括小胶质细胞)中。
创伤性脑损伤后的慢性神经炎症是导致脑损伤加重的原因。由于 TLR‑4 的下调会减
少炎性细胞因子并调节小胶质细胞,因此使用 LDN 可能具有神经保护作用。35
新型、多学科的 TBI 诊断和治疗方法在我的诊所和其他诊所,我们经常评
估患者的炎症标志物、自身抗体产生和总毒性负担。我
们还使用新型面板来观察神经组织自身抗体,包括表明脱髓鞘风险增加的标志物、血
脑屏障破坏、视觉和自主神经系统疾病、周围神经病变、神经肌肉疾病、大脑自身免疫、
大脑炎症和感染(尤其是病毒标志物)。目前,大多数 TBI 生物标志物研究都集中在
严重 TBI 上,很少有专门针对 mTBI 的研究。需要额外的候选生物标志物。创新和无偏
见的自身抗体识别方法补充了更传统的方法,以帮助发现新的 mTBI 生物标志物。36
虽然最初的脑损伤涉及急性和不可逆的原发性组织损伤,但随后的继发性脑损伤通常
会在数月至数年内缓慢进展。这非常重要,因为在自身抗体产生与终末器官损伤和临
床症状检测相关之前有一个潜伏期。因此,现在正是采取积极、全面的治疗干预措施的
好时机。37
神经可塑性的概念是指大脑可以在一生中不断变化,最深刻的体现是某些中枢神
经系统损伤中出现的“自发性恢复”。我们现在知道,许多细胞参与者在幕后协调着
对不同信号的一系列动态反应。损伤引起的神经可塑性是由小胶质细胞驱动的,小胶
质细胞会诱发中枢神经系统反应。小胶质细胞在损伤后对大脑的这种调节被称为“可
塑性的可塑性”。这个术语很好地描述了小胶质细胞在受到干扰时改变其形态和基因
表达的能力
SPM 源自 EPA 或 DHA,包括消退素、保护素、脂氧素和马来素。这些新物质可减轻炎症并修复受损组织,从而恢复组织稳态。在
我们的诊所,我们一直使用市售的 SPM 制剂来治疗身体损伤,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治疗与关节疼痛和炎症相关的风湿病/自身免疫性疾
病。将 SPM 与 omega‑3 脂肪酸结合使用是一种极好的策略,可通过促进抗炎细胞因子的表达并将小胶质细胞推向 M2(抗炎)启动
状态来抑制炎症。使用 SPM 的动物研究结果令人满意,表明小胶质细胞表达 SPM(消退素)受体。40治疗 TBI 的其他饮食策略包括热
量限制和生酮饮食。热量限制已知可延长多个物种的寿命和胰岛素敏感性。它是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包括 TBI)的一种治疗方法。生 酮饮食已被证明
Omega‑3 脂肪酸不仅通过新陈代谢提供能量支持,还能调节炎症反应和免疫功能。此外,它们还
能维持内脏器官功能并优化细胞信号传导。多项研究表明,Omega‑3 脂肪酸可抑制 TBI 引起的
炎症反应,这种抑制机制可能与小胶质细胞活化有关。39剂量应考虑受伤后的时间。急性损伤可能
需要更积极的 Omega‑3 疗法(EPA/DHA)。新研究正在研究专门的促分解脂质介质或 SPM。
和 火光
饮食
尤其
最有效的抗炎疗法之一是优化饮食,包括尽量减少 omega‑6 与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比
例。我们的现代饮食使得摄入足够的 omega‑3 以抵消绝大多数含有高 omega‑6 的健康食品的
危害变得异常困难。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 (ω‑3 PUFA) 在人体新陈代谢中起着关键作用,包
括 α‑亚麻酸、二十碳五烯酸 (EPA) 和二十二碳六烯酸 (DHA)。
环境或损伤。小胶质细胞和其他中枢神经系统细胞受细胞外和细胞内因素的精细调节,例如刺激
的性质、细胞外环境和潜在的先前细胞功能。38
有望用于治疗癫痫,也可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前模型。生酮饮食的潜在神经保护作用包括多种可能的机
制,通过改变能量代谢。酮症介导的替代能源使用被认为可以提高对神经元损失的抵抗力,提高对代谢压力的抵抗
力,并通过线粒体的生物合成刺激能量产生。这种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可能会增加主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γ‑氨基丁
酸 (GABA),这有助于防止神经元放电。此外,还可以防止谷氨酸兴奋性毒性(一种主要的刺激性神经递质)。这两
种改变都有助于治疗慢性发炎的大脑。最后,动物研究表明,生酮饮食可减少慢性低血糖、缺氧缺糖和线粒体 ROS。
41如果建议采用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则必须考虑患者的载脂蛋白 E (ApoE) 基因型。纯合 ApoE ε4/ε4 状
态的患者可能需要比 ApoE ε3 携带者维持低脂肪饮食。
无论采取何种饮食调整来治疗 TBI,患者都必须避免饮酒,因为酒精的神经毒性不利于愈合。
水通道蛋白和 TBI在我的
诊所,我们经常要求有持续症状的 TBI 患者除了遵循一般的抗炎饮食建议外,还要避免食用玉米、大豆、菠菜叶和
番茄水通道蛋白。什么是水通道蛋白 (AQP)?每个生物都需要水,但过多的水可能是致命的。植物和动物通过膜通
道蛋白(称为水通道蛋白)将水进出细胞。植物恰好与人类水通道蛋白‑4 (AQP4) 具有相似的氨基酸序列,而水通
道蛋白‑4 (AQP4) 大量表达于星形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是将神经元细胞连接在一起的星形大胶质细胞。因此,
针对饮食水通道蛋白形成的抗体可能会与脑水通道蛋白发生交叉反应,导致血脑屏障通透性并为神经自身免疫和
神经退化奠定基础。星形胶质细胞在 BBB 因创伤(如 TBI)而破裂时形成第二层保护层。如果 BBB 出现破裂,星
形胶质细胞的末端就会暴露出来。高浓度
这些终足中的 AQP4 意味着它们容易受到循环食物 AQP 抗体的攻击。研究表明,针对玉米、大豆、菠
菜或番茄 AQP 的抗体(在 BBB 破裂时在血液中循环)可能会攻击 AQP4,从而破坏大脑的第二层保
护。这是 BBB 破裂、突触微环境功能障碍和神经自身免疫的模型。
四十二
其他抗炎和抗氧化补充剂以下膳食补充剂具有抗炎和抗氧化特性,可帮
助支持高度分解代谢(消耗能量)的炎症状态,例如 TBI。43
白藜芦醇:保护/防御 BBB,促进大脑发育
激素,支持线粒体。
小檗碱:解决肠道菌群失调、稳定血糖、抗炎。
活性 B 族维生素:必要时服用,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
(炎症标志物,表明神经退行性的风险)。
与知识渊博的临床医生合作,确定采取哪种形式(通常为B6、 B9和B12)。
镁:数百种反应所需的辅助因子。不易过量。甘氨酸镁和苹果酸镁吸收更好。
可以使用透皮镁和泻盐浴。
NAC(N‑乙酰半胱氨酸)和谷胱甘肽:支持细胞排毒的强力抗氧化剂。
姜黄素:最强大的神经保护和抗炎化合物之一;降低 BBB 通透性。
维生素 D:抗炎和增强免疫系统;
激活器官正常功能所需的数百种基因。
创伤性脑损伤治疗的关键因素
以下情况会削弱血脑屏障的修复能力,从而限制 TBI 的治疗程度:
潜在感染。
贫血。如果血红蛋白水平低,大脑就没有足够的氧气。
低血压会导致血液循环不良,包括大脑血液循环不良。“手冷、脚冷、脑冷。”血压低并
不总是好事!
高血糖或低血糖。这两种情况都是炎症性的。
霉菌或霉菌毒素暴露。
生活方式
脑损伤后,患者必须⽴即进行一段时间的身体和认知休息,在此期间,他们不得升高血压和心率,也不
得从事加剧神经症状或导致疲劳的活动。患者必须与医疗团队合作,根据个人临床病程确定适当的休
息时间。在最初的休息期之后,运动有利于康复。运动可增强急性期新线粒体的产生,从而增强能量产
生。44
减轻压力
高压力会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皮质醇是一种神经炎症激素,会对血脑屏障产生负面影响。以下是有
助于缓解高压力反应的选项:
神经反馈(引导式冥想的高级形式)
瑜伽
边缘系统重置
肌筋膜放松或其他轻柔的身体锻炼
心率变异性训练(平衡自主神经系统)
优化睡眠‑觉醒周期:皮质醇和褪黑激素睡眠是最不为人所知和
低估的生理状态之一。人类一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中度过。
最佳睡眠质量、数量和昼夜节律对健康至关重要。睡眠对于记忆的产生和保留、学习和注意力以及神
经元通讯必不可少。虽然人们对睡眠的了解甚少,但有人认为睡眠可以充当清除大脑中在清醒时积累
的毒素的管家。睡眠几乎影响每一个
睡眠是人体细胞中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对激素和神经递质的合成、调节和分泌至关重要。缺乏高质量
的睡眠会增加患上所有慢性疾病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抑郁症和肥胖
症。
45以下是优化睡眠的
解决方案:
如果昼夜节律被打乱,可以考虑在睡前一小时服用小剂量的缓释褪黑激素(1
毫克)。
四点唾液皮质醇测试可确定全天四个时间点唾液中的皮质醇水平。这可以揭示肾上
腺功能障碍。对抗疗法中唯一公认的肾上腺问题是肾上腺功能不全或皮质醇增
多症,这两种疾病都会产生严重后果。然而,正常的每日皮质醇曲线中更细微的功
能障碍可能会给患者带来相当剧烈的痛苦。
皮质醇和褪黑激素呈负相关。正常的昼夜皮质醇模式包括醒来后 30 分钟内皮
质醇水平激增,称为皮质醇觉醒反应 (CAR),随后全天逐渐下降,睡前降至最低点。如果
由于慢性压力或其他因素导致昼夜节律紊乱,那么患者可能受益于早晨的全光谱光
和日落后的褪黑激素和蓝光阻挡眼镜。蓝光会抑制人体自然产生褪黑激素。
每天晚上同一时间睡觉。
睡前三小时不要进食。
在阴凉、黑暗的房间里睡觉。
卧室内不准安装屏风。
晚上不要摄入咖啡因或酒精。
晚上不做运动。
养成放松的睡前习惯。
使用正念技巧来镇静交感神经系统。
如果无法入睡,请避免躺在床上。
如果您打鼾、醒来时精神不振或腿部不安,请进行正式的睡眠研究。
四十六
华盛顿大学的 Mark Cooper 博士创造了LDN+一词来描述使用多种抗炎药物来对抗神经炎症损伤。Cooper 博
士将内体描述为可以作为毒性分子(自身抗体)储存位点的细胞器官(细胞器)。这些自身抗体在中枢和周围神经
系统中的积累会导致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
一项前瞻性、随机、交叉对照试验对 56 名患有长期脑震荡后综合症的 mTBI 患者进行了检查,这些患者在受
伤后一至五年内接受了检查。试验包括 40 次高压氧疗法(每周五天,持续八周),每次 60 分钟,使用 1.5 个大气
压的纯氧。高压氧疗法后,两组的认知功能均有显著改善,但在未进行高压氧疗法的对照期后,没有观察到显著改
善。40 次治疗后的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 (SPECT) 成像显示大脑活动增加,这与患者经历的认知改善相符。
这表明高压氧疗法可以诱导神经可塑性,从而修复慢性
神经调节疗法
LDN 与其他免疫和
在 LDN 中添加药物可产生显著效果。高压氧疗法 (HBOT) 已与 LDN 一起使用,以帮助
治疗 TBI 病例以及其他神经自身免疫病例。
LDN 在治疗神经炎症和神经自身免疫方面非常有前景,因为它可以穿过血脑屏障,在中枢神经系统组织中积累,并
进入神经炎症病变。通常需要多种疗法组合(LDN+)才能恢复功能并实现可能的症状缓解。
在动物模型中,高压氧疗法已被证明可以减少程序性细胞死
亡(凋亡)、增加生长因子的产生、提高抗氧化剂水平并抑制炎性细胞因子。47 TBI 会导致整个大脑血
流全面丧失,即所谓的整体低灌注。因此,TBI 最常见的症状是认知障碍。如果组织整体缺氧,则无法再
生。因此,通过增加血液和身体组织中的氧气水平,高压氧疗法可以促进自然细胞修复机制。
脑功能受损,并改善了晚期慢性期 PCS 较长的 mTBI 患者的生活质量。48最后,最令
人印象深刻的是,最近对患有 PCS 和有或无 PTSD
的 mTBI 患者的一项研究表明,高压氧疗法对 TBI 具有持久的益处。该研究包括
30 名年龄在 18 至 65 岁之间,患有一处或多处爆炸引起的轻度至中度创伤性脑损伤
的军事人员。30 名受试者中有 29 名出现显著改善,通过测量神经系统症状、智商、记忆
力、注意力、优势手运动速度和灵活性、生活质量、一般焦虑、PTSD、抑郁(包括自杀意
念)和精神活性药物使用情况进行量化。此外,在六个月的随访中,参与者报告症状进一
步改善。与对照组相比,受试者的初始 SPECT 成像明显异常。
经过 1 次和 40 次治疗后,影像学显示的损伤显著改善,并且在 75% 的大脑异常区域,
与对照组在统计学上没有区别。研究的每个结果都显示出改善:临床医学、神经心理学、
心理学和 SPECT 成像。49
结论
我治疗受伤后长达数十年的 TBI 患者的经验告诉我,慢性炎症和下游病理效应的激
活过程极其复杂。TBI 是一种多维疾病,其表现、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高度可变。阻止神
经炎症级联的高收益策略包括考虑遗传和其他风险因素的治疗性饮食、ω‑3 脂肪酸和
额外补充剂;纠正贫血、低血压和高血糖或低血糖;减少慢性压力;充足的睡眠;尽量减
少毒性暴露;增强毒素代谢/排泄。大脑康复策略必须始终针对个人量身定制,但通常
可以包括多种治疗剂的组合,以实现协同作用、症状缓解和细胞修复。LDN 仍然是 TBI
管理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在这篇总结中,我希望能够传播对这种重要的免疫调节和抗
炎剂的更多了解
在整个国际医学界,并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九‑
分离性障碍
WIEBKE PAPE,医学博士
分离性障碍是继创伤后应激障碍之后最常见的创伤相关障碍之一。与联想相反,分离性障碍描述的是相
关信息整合的缺失,或正常相关的心理过程的分离。根据《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 (DSM‑5)
的定义,“分离性障碍是指心理功能一个或多个方面正常的主观整合的中断和/或不连续,包括但不限
于记忆、身份、意识、感知和运动控制。从本质上讲,心理功能中应该关联、协调和/或联系的方面并没有联
系在一起。”1
在极度创伤的情况下,解离是被动防御反应的一部分。它既可以看作是一种病理反应,也可以看作是
一种保护机制,因为解离使创伤记忆远离意识成为可能。解离患者可能会对创伤事件产生遗忘,或产生
一种脱离感 认为创伤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例如,车祸受害者经常报告的灵魂出窍的经历)。当一个
人经历反复和累积的创伤时,尤其是在童年时期,解离倾向可能会使他们脱离创伤事件并形成依恋,甚
至对造成创伤或疏忽照顾的人 这是一种对生存至关重要的能力。另一种对严重创伤的解离反应是
童年是不同人格状态的发展阶段,有些与创伤记忆有关,有些则在日常生活中安于现状,并经常否
认创伤的发生。认知和社交技能的发展就像创伤没有发生一样是可能的,但在成年生活中,分离症
状通常会成为严重的障碍。
DSM‑IV 分离性障碍结构化临床访谈 (SCID‑D) 是一种标准化诊断工具,可识别出分离性的五种具体症
状:2
1. 失忆症或记忆问题,包括回忆困难
个人信息。
2. 人格解体或与自己分离或断绝关系的感觉。与人格解体相关的一种常见感觉
是感觉自己像个陌生人。
3. 现实感丧失或与熟悉的人失去联系
或一个人的周围环境。
4. 身份困惑或对自我意识/身份的内心挣扎。
5. 身份改变或感觉行为举止像另一个人。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发布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 ( DSM‑5)定义了三种主要的分离
性障碍:3
1. 分离性遗忘症(见上文定义)。
2. 人格解体‑现实解体障碍(见定义
多于)。
3. 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 (DID):“两种或多种不同人格状态的身份识别中断⋯⋯自我意识和主
体意识明显不连续,同时伴有效果、行为、意识、记忆、知觉、认知和/或感觉运动功
能的相关改变。”患有 DID 的人通常还会患有分离性遗忘症。
解离研究表明,解离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形式:分离和区域化。分离
指感知的改变 对自己或身体(非人格化)或周围环境(现实感丧失)的疏离感和疏离感。区域化描述
了对正常可控过程的意志控制缺陷;主要症状是分离性遗忘症(例如,转换症状、分离性神游症、分离性
身份障碍)。4考虑分离性症状的另一种方法是将其归类为积极(表明未整合的创伤材料的生产性症
状,例如侵入性记忆、闪回、创伤相关疼痛、幻听)或消极(导致正常意识功能中断的症状,例如记忆缺陷、
自我意识丧失和/或失去感知或控制身体不同部位的能力)。5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分离性障碍才被认为是罕见的。最近的研究表明“分离性症状与焦虑和抑郁
一样常见,患有分离性障碍(特别是分离性身份障碍和人格解体障碍)的人经常被误诊多年,从而延误
了有效的治疗。患有分离性身份障碍的人经常寻求治疗各种其他问题,包括抑郁、情绪波动、注意力不集
中、记忆力减退、酗酒或吸毒、脾气暴躁,甚至幻听。”6在本章中,我将以临床医生的身份阐述我对分离
性障碍的看法,并尝试说明问题、治疗目标以及 LDN 如何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有用药物。我们的治疗团
队在医院的创伤相关疾病科工作,该科室在住院环境中治疗心身疾病,我们密切关注童年创伤的后果以
及我们的客户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
我经常让我的客户通过案例研究描述他们自己的经历,以便读者能够感受到分离症状以及 LDN 可
能带来的变化,因为症状具有高度的个体性,非分离患者很难想象。
复杂的创伤和分离
复杂性创伤是指一个人在童年和/或青春期遭受反复、长期和/或累积的压力。压力源可能包括性虐待;
残忍;主要照顾者的忽视、遗弃和/或反感;照顾者的持续羞辱和过分要求;缺乏情感安全感;经常被独自
一人;以及早期失去重要的依恋对象。
这些事件通常会对人格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并在以后的生活中产生持久影响。遭受复杂创伤的患者
通常会遭受以下痛苦: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包括创伤事件的侵入性记忆、噩梦、与创伤事件有关的记忆碎
片化、回避创伤相关刺激、情感麻木和慢性过度唤醒。
慢性抑郁症。
情绪不稳定,情感调节困难。
自我认知扭曲,根深蒂固的无助感、无价值感、内疚感和羞耻感(常常导
致人们将自己与他人孤⽴起来)。
依恋障碍涉及不信任和害怕与他人亲近,但也涉及依赖(常常导致人们保持破坏性的关
系)。
慢性疼痛、焦虑症、饮食失调和成瘾症。
分离性障碍。
患者常常会出现复杂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种综合症于 1992 年首次提出,后来被纳入《国际疾
病统计分类》(ICD)第 11 版。7我们的部门主要治疗患有这种综合症的患者。
患有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经常抱怨,他们被与创伤情况相关的多种刺激“触发”,并促使他
们重新体验这些情况。他们报告说,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过去。他们还描述说,感觉自己很无助,就好像自
己又一次处于创伤情况中一样。在这些情况下,患者经常会感觉到年龄的倒退,就好像他们又回到了童
年
并失去了成年人的能力。这可以归因于创伤压力导致的信息碎片化。客户通常会对这些情况产生遗忘。
来访者通常这样描述他们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保护自己,我只能僵住并试图忍
受这种情况,直到它结束。”这种描述反映了来访者重温被动防御反应的方式 这是创伤情况下的主要生
存机制。
大多数患者都有严重的依恋问题,害怕其他人,尤其是害怕新环境。许多人因为社交压力而退出社交活
动。另一个人的某个词、某个表情或某个手势可能会唤起过去创伤性情景的挥之不去的记忆。
对于这些患者来说,情绪的自我调节非常困难;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一种情绪难以承受的状态跌入另一种
状态,并且对反复出现的记忆感到非常焦虑。
对创伤相关信号的常见反应是解离:关闭,将注意力从威胁性刺激上转移开,转向内心,飘忽不定。患者
会描述一种大脑一片空白的感觉。
分离性反应的触发因素不仅来自外部,而且往往来自内部,例如情绪。持续性创伤的受害者在早年就学会了
情绪通常是压倒性的(例如,存在主义恐惧、恐怖、孤独、悲伤或愤怒)。由于生活条件不稳定和缺乏情感关
怀,他们从未学会正确调节自己的情绪,为了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正常运作和生存,他们常常被迫将自己的感觉
与意识分开。因此,他们在成年后害怕情绪,并试图抑制它们,因为它们是陌生的和有威胁性的。这些人经常
描述感觉像机器人一样 麻木、沮丧、对他人没有反应,缺乏活力和快乐。他们形容自己与内心生活脱节,在
自己的身体里感到疏远。他们的情绪往往是麻木的,或者 当不被压抑时 是压倒性的。当情绪出现时(例
如在让他们想起以前的压力情况的情况下),它们通常会导致类似于创伤时所经历的反应。患者因恐惧而
僵住,无法采取适当的行动或做出适当的反应,并且感觉
正如我的一位病人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处于无助和“听任犯罪者摆布”的状态。
创伤情境中的分离反应是一种保护机制。它有助于抑制对正在展开的恐怖的认识,就像麻醉一样。当一个
人在创伤情境中分离时(创伤后分离),他们的感知会发生变化;一切似乎都变得遥远而不那么重要。受影响
的人经常描述灵魂出窍的经历。一方面,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机制。然而,在复杂的创伤情况下,个人习惯了这
种保护技能,分离会在与创伤情境略微相似的时刻自动发生。我们可能会说,身体反应过度,因为创伤在几年
前就结束了。因此,受创伤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分离。当他们遇到具有挑战性的情况时尤其如此,因为这些情
况会引起情绪反应,而不像熟悉和安全的情况。为了尽量减少分离,他们会专注于安全和控制,试图避免挑战。
如前所述,解离可以以不同的模式出现:
现实感丧失(外部世界似乎不真实)
人格解体(对自己身体的感知被扭曲)
情感麻木
缺乏对自己身体的感知(躯体形式分离)
忘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事情
日常生活中的遗忘事件
创伤事件或情绪的侵入性记忆以及与创伤相关的身体感觉
固定
听到声音
创伤导向治疗的目标分离性患者的安全和稳定是治疗的首要关注点。下一步是尝试解
决过去发生的创伤事件,以尽量减少它们对当前的影响。为了克服以前的创伤并应对日常生活,患者
必须学习新的策略来区分危险情况和
他们需要学会如何面对无害的事物,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并保护自己。他们还需要培
养正念和自我同理心。他们被鼓励面对新情况,以了解新情况与创伤情况的不同之处。然
而,如果患者有严重的分离症状,他们就很难专注于当下,尤其是当情况具有挑战性和
令人恐惧时。改善分离症状是一个费力而缓慢的过程。分离类似于自动机器,因为它是
一种经过多年训练的反射。分离行为往往是无声的、平淡无奇的,这给治疗增加了另一
层挑战。
例如,治疗师可能在治疗中达到一个重要点或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对患
者来说可能很艰难,但这次治疗似乎很成功。在下一次治疗中,当治疗师想要继续上一
次治疗时,客户说:“哦,我记不清上一次治疗的任何内容了,一定是太累了,我刚刚昏
过去了。”
患者通常表示,他们非常害怕自我认知 害怕意识到自己内心正在发生的事情 因
为这可能会引发与创伤相关的感受。因此,如果患者想要克服分离,他们必须有“意识
到的准备”:一方面,分离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障碍;另一方面,它是一种保护策略 避
免意识到内心正在发生的事情。意识到的准备是复杂创伤患者的治疗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主题。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管理自己的生活,假装“只要我继续生活,只要我不仔细
观察自己的状态,我一切都好。”
作为治疗师,我们的经验是:客户越容易意识到当下 用所有感官去感受当下 并且
在遇到困难时保持当下,他们就越容易应对日常生活和过去的创伤经历。因此,在治疗
中,主要重点是激励客户保持对当下的意识,并提高他们在当下采取行动和感觉尽可能
安全的能力。
片刻。
尽量减少分离症状:LDN 如何提供帮助心理治疗是治疗分离症状的首
选,但如上所述,患者单
靠治疗很难取得快速进展。目前尚无直接影响分离的既定药物干预措施。用于治
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可以帮助治疗某些分离症状 焦虑、抑郁、情绪不稳定 但
这些都被视为标示外用途。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使用 LDN 时并没有完全理解其复杂的工作机制 事实上,这些机制仍在
更广泛的医学界探索中。在描述分离性障碍患者的作用机制时,我参考了 Dr.
乌尔里希·拉尼乌斯 (Ulrich Lanius),我从他那里了解了 LDN,并鼓励我尝试将其作为药物
来支持治疗分离性患者。8
分离和 LDN 之间有何联系? 一个过于简单的模型
解离至少部分由内源性阿片类药物的释放介导。9当无法逃避危险时,内源性阿片类药物就会释放,
此时主动的交感神经防御(战斗或逃跑)已无法再进行。阿片类药物会激活副交感神经防御反应,包
括固定、镇痛和麻痹情绪痛苦:用亨利·克里斯托博士的话来说,“在屈服和紧张症反应状态下,所有
疼痛都会停止,随之而来的是舒缓的麻木。”10创伤事件的特点是“无法逃避的休克”,内源性阿
片类药物会激活被动(副交感神经)防御反应。当创伤应激变成慢性时,会导致阿片类药物的释放持
续增加,随后阿片类受体会减少。由于剩余的受体较少,即使是少量阿片类药物的释放也会导致这些
受体饱和,引发被动防御反应和分离。
此外,内源性阿片类药物系统参与情感调节和情绪依恋的调节。阿片类受体的下调导致调节能力
严重受损。因此,应对压力源变得不那么灵活,
并且很少的压力源会导致副交感神经激活和分离。由于童年时期的压力,内源性阿片类药物活性的长期变
化可能很早就发生了。
主动(交感神经)防御反应受到内源性阿片类药物的抑制,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阻断阿片类药物介导的
防御反应会支持主动防御反应。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使用纳曲酮/纳洛酮阻断阿片类受体以减少分离
一直是药理学研究的主题。在早期的研究中,纳曲酮的正常剂量为 25 至 100 毫克,11这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了过度效应,唤起了创伤记忆或自杀倾向。12
据推测,使用高剂量纳曲酮治疗会导致阿片类受体几乎完全被阻断,从而导致患者分离能力被阻断。由
于缺乏替代应对策略,这对高度分离的患者来说可能是巨大的负担。
LDN 对患者分离能力的影响较小。必要时可以选择分离,这使得 LDN 比高剂量替代方案对患者更耐受。
此外,LDN 似乎可以重新激活内源性阿片类药物系统的情感调节能力 这似乎是 LDN 在治疗分离症状
方面的特殊作用。
开具 LDN 处方
在我们的住院治疗机构中,我们于 2009 年首次开出 LDN 处方,作为治疗患有严重分离症状的患者的一
种方式。
治疗的可靠性(尤其是在危急情况下)和出院后继续门诊治疗是开始用药的条件。患者同意观察并记录任
何出现的症状变化。
由于德国没有 LDN,我们医院的药房用 50 毫克的药片制作胶囊。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只能生产 2 毫
克的胶囊,因为 1 毫克的剂量无法可靠地测量。因此,我们不得不将 2 毫克 LDN 设定为起始剂量。我们目
前开出的剂量范围从 2 毫克到 6 毫克,有时甚至高达 12 毫克。我们早上以 2 毫克开始治疗,等待大约一
周以观察效果。进一步的剂量根据个人情况进行调整
症状和患者评估。有时我们会将单剂量增加至 6 毫克。中午再给一次 LDN(从 2 毫
克增加到 6 毫克)通常很有帮助,因为 LDN 的半衰期较短,因此效果会在午后减弱。
几周内,我们会根据患者的个人需求调整剂量。有时,根据需要服用额外剂量对他们
很有帮助 例如,当由于压力情况而出现更多分离时。有时,当患者在某些时候无法忍
受效果时,也需要减少剂量。
通常我们的患者会根据自己的症状来调整个人剂量。
病例报告 #1我们的
第一位患者是一位 47 岁的女性,她是一名教授,多年来一直患有分离症状。她生命中前七年的记忆被失忆所笼
罩;她只记得一些关于性虐待的零碎创伤记忆。在她入院前的四个月里,她的症状恶化了:创伤记忆增加,她在日常
生活中经常“浪费时间”,严重伤害自己。她越来越难以集中精力处理诸如讲座之类的复杂事务。她的情绪不稳
定,经历过抑郁发作。她被送进我们医院,因为她再也无法应付工作了。最让她尴尬的是,她经常在具有挑战性的
情况下表现得像个孩子,尤其是在工作中。
她对自己的分离症状表现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她很担心,因为这些症状让她失
去了控制。另一方面,她说:“当事情太过分的时候,分离可以帮助我摆脱它;这是一种
解脱。”她解释说,当她进入分离状态时,她会进入一个想象中的内心世界,里面有各
种美丽、色彩缤纷的图案。
在服用了第一剂 2 毫克 LDN 后,她说:“我再也无法关闭我的感知了。”在服药
之前,当她分离时,她只会感觉到周围的环境是“低语”;之后她可以区分噪音并正
确聆听对话。她的注意力集中能力提高了,但她觉得周围的环境更具挑战性。
在服用 LDN 之前,她解释说:“我从来没有生气过,我完全不知道这种感
觉。”服用 LDN 后,她感到愤怒,并报告说愤怒
她脑海中浮现出对其他人的回应,这让她感到非常害怕。
许多受过创伤的人害怕愤怒,因为这种情绪与他们所经历的暴力有关。在过去,表达愤怒可能导致
惩罚。在当下,愤怒的情绪会引发分离,从而保护他们免受创伤经历的影响。如果无法感知自己的愤怒
情绪,自我保护和自我照顾就会很困难,并可能导致再次受害。
当这位客户开始感到愤怒时,她必须根据这种感知变化做出适当的反应。她学会了在达到极限时
正确保护自己。她说感觉自己有能力采取行动,并描述了她如何“意识到自己并活着”。
自动分离减少了,但她仍然可以在必要时自愿分离。她选择在一周后将 LDN 剂量从 2 毫克增加
到 4 毫克,然后在另一周增加到 6 毫克,因为她在积极应对周围环境方面取得了进展。几周后,她描述
感觉“与我的同伴和环境保持联系”。愤怒和悲伤等情绪不再威胁她。
她可以利用这些经验来制定新的自我护理策略。她的注意力和意识一天天提高。
服用 LDN 19 个月后,她描述了以下变化:
在服用 LDN 之前,我花了很多时间处于分离状态 通常是无目的的 以活在自己的
世界中并保护自己免受苛刻的环境影响。一方面,我对这种情况很着迷;另一方面,分
离对我造成了损害,因为我无法控制它。自从我服用 LDN 以来,我注意到自己何时开
始分离。然后我可以选择退出世界或回到现在。我能够阻止它,而且我可以控制它。总
的来说,分离很少发生,也失去了它的很多魅力。我感觉更加活跃,可以承受许多挑战。
只有在要求极高的情况下,我才需要分离。但在这些情况下,这是一种应对巨大压力
的能力。
治疗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因为当事情变得紧张时我能够保持意识,并且能够继续工
作。
这位客户不再服用 LDN,因为她最终学会了停止服用
无需药物帮助即可实现分离。
客户评价
“就好像有人打开了我脑袋里的灯一样。”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我能感觉到身体的力量。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爬楼梯而不感到疲
惫。”
“我第一次意识到地毯是有图案的。而且,我第一次明白了它的含义,以及将脚放在地上保持稳
定的感觉。”
“我敢于尝试新事物:我可以加入一群我不太熟悉的人。我不必时刻保持警惕。”
“我可以集中精力,理解复杂的事情。我一直以为自己很笨,因为我理解的太少,忘记的却太
多。”
病例报告 #2一位被
诊断患有分离性身份障碍的 38 岁女性正在我们住院部处理创伤事件。在接受 LDN 治疗之前,她说:“经过一次
对质治疗后,我整晚都处于分离状态;就好像我又回到了创伤的过去。早上我醒来时感到无比恐惧。经过几天的对
质治疗后,我感到非常疲惫和虚弱。”
她开始每天早上服用 2 毫克 LDN 后,她说:“服用 LDN 药物的第二天,我就能区分之前只是‘恐
惧’的情绪了。我没完没了的沉思消失了;我的思维变得清晰且结构良好。”
几周后,她描述道:
LDN 重塑了我的情感生活。服用之前,我感觉周围好像有一堵雾墙 部分是为了保护我。它
完全消失了。所以我可以看到和感受到创伤对抗工作带来的情绪。我学会了如何应对它们。
在服用 LDN 之前,当情绪
发生了。现在,当闪回发生时 在服用 LDN 之前,这种闪回是无法忍受的 我可以更
轻松地使用我的稳定策略来应对它们。
回顾性研究
2012 年,我们开展了一项回顾性研究,研究了 LDN 对我们用这种药物治疗的首批 15 名患有复杂创伤
的患者的影响。这些治疗可以追溯到 2009 年。13表 9.1列出了患者表现出的不同分离症状,以及出现
每种症状的患者人数。
对 LDN 的初步反应
在研究中的 15 名客户中,有 11 名描述了服用 LDN 的第一天或第二天后的积极效果,2 名不喜欢这种
效果,2 名没有注意到任何变化。在第一次使用 LDN 后的四到六周内以及解雇后的头几个月内,记录了
各种短期反应:
过度刺激:尽管有 11 名患者在最初几天就注意到了积极效果,但其中三名患者还是停止
服用 LDN。他们的分离感减少导致他们对思想、情绪、身体感觉和周围环境的
感知增加,这对他们来说太具挑战性了。三名停止服药的患者中有两名报告称,他们
接触到了之前被压抑的创伤记忆。
这三位患者还表示,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产生压力。一位患者在服用 LDN 几周后
出现血压升高,另一位患者则表示,他们全身出现弥漫性流感样疼痛。这些患者停止服
药后,报告的副作用就消失了。
尽管最初有些烦躁,但治疗效果逐渐显现:两位患者在治疗的头几天描述了一种负面影响,即
由于感知更加清晰,他们的烦躁和焦虑感有所增加。他们报告了接下来两周内
出现的有趣变化:他们注意到自己有一种冲动,想要更加
在日常情境中活跃并有动力参与新的体验。
其中一位客户在几周后停止服用 LDN,因为她发现治疗期间这种发展“太多
了”。另一位客户“接受了挑战”,并在随后的几周内在自我调节方面取得了重大进
展。
无效:在两个客户中,LDN 没有显示任何效果。我们
他们在服用 4 毫克两周后没有发现任何变化,然后结束了治疗。
15 位客户中有 7 位回答了我们 2012 年的问卷,问卷内容是
这项研究考察了8至27个月的治疗持续时间。
长期影响
讲述他们在 LDN 的持续经历。
总客户数)
转变为孩子般的人格状态。
僵住,或无法采取行动 触发
难以集中注意力。
受过精神创伤的孩子。
表 9.1. 患者描述的分离症状
冻结和关闭 由
侵入性记忆/闪回。
14
出现症状(共 15 个)
环境。
15
7
部分。
每天发生数次失忆症。
9
15
11
分离症状
客户对自己情绪的认知。
9
10
自残行为。
一名外表具有威胁性的人。
表现和体验刺激就像
暂时模糊、遥远且扭曲的感知
客户数量
无法感知自己的情绪。
6
9
无法感知自己的身体和/或身体
所有 9 名继续服用 LDN 的患者均报告称
LDN 效应持续存在并继续帮助他们缓解症状。
我们的诊所。
15 名患者中有 9 名在出院后继续服用 LDN
一位客户将剂量从每天 6 毫克减少到 4 毫克,原因是
反复弥漫性疼痛。随着剂量的减少,客户的
疼痛消失了,但积极效果却没有减弱。
2
减少受伤。
找到了
症状变化
“关闭”的情况较少发生
闪回强度降低。
患者
调节(负面)情绪。
2
1
0
主观上
提高感知清晰度
0
8
提高思考能力和专注力
WHO
2
2
数量
增强感知和
有压力
1
可以更容易地调节
表 9.2. LDN 患者分离症状的变化
患者
调节。
0
压力情况下的意识。
感知自己身体的能力。
6
控制自残行为的能力增强,从而
1
患者
2
复杂的概念。
1
改变
1
改变
记忆(对于一些客户来说,这些
主观上
7
2
2
数量
更频繁,更容易
数量
0
8
提高创伤的清晰度
改变
8
1
增强维护能力
0
找到了
有帮助
周围环境。
2
稳定技术)。
7
注意并理解
3
经验丰富
1
一位患者由于生活和治疗环境的多重变化而停止服用 LDN,尽管其仍然
有积极效果。
她没有对自己的分离症状的变化发表评论。
表 9.2概述了 LDN 治疗后分离症状的长期变化,表 9.3描述了患者在不同治疗时间后
出现的不同副作用。
2017 年对 50 名 LDN 客户的调查
时间):
3
睡意
2
1
表 9.3. 不同使用时间后的 LDN 副作用
饱腹感
体重增加(不清楚是否是 LDN 的影响)
2
直接的副作用(通常会随着时间而减少)
创伤记忆增加
1
肌肉疼痛(戒烟后复发
头痛
数周或数月后的副作用:
嗜睡
4
患侧患者人数
几天后的副作用(通常持续):
1
伦敦
胃炎
焦虑
5
血压升高
效果
1
1
排尿障碍 1
是否有副作用。他们的回答如下:
出院后继续服用 LDN。
症状是否发生了变化,LDN 的效果是否以及如何变化,以及
仍然是阳性,他们修改了剂量方案。一些
如果他们完成了药物治疗,为什么他们要完成药物治疗,他们的分离症状是如何出现的?
50 位客户中有 37 位报告了积极效果,并且
从 2009 年开始。患者被问及是否仍在服用 LDN,
2017 年,我们对 50 名接受 LDN 治疗的患者进行了调查
他们的各自答复如下:
上述 37 位客户中有 14 位表示,尽管 LDN 的效果
– “当我减少剂量时,分离症状又回来了,所以我继续服药。”
– “我会根据具体情况调整 LDN 的剂量。当我必须全神贯注时,
我会增加剂量。”
– “当我认为有必要时,我会按需服用 LDN
影响。”
四位客户报告称,经过大约一年的不同时间段后,他们不再需要
LDN。他们表示:“药物产生了一种冲动;一些事情开始运转,现
在发展正在自行进行。”
– “停止使用 LDN 后,我发现我学会了尽量减少分离。现在我可以不使用 LDN 来
使用我的新能力了。”
两位顾客停止服用 LDN,因为药物太贵了。
50 位客户中,有 6 位没有注意到服用 LDN 的任何效果。
在接受 LDN 治疗的 50 名患者中,大多数患者报告了持续的副作用,并且不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逆转。一些患者感觉副作用减少了,因此不得不暂时增加剂量。两名患者
报告说,一段时间后,他们不再注意到副作用。副作用随时间变化的原因尚不清楚。
常见问题
是否有可能预测谁将从服用 LDN 中受益?
我们的印象是,LDN 对患者的帮助程度似乎至少部分取决于他们应对日常问题的能
力。认为自己需要保护并倾向于避免挑战的患者似乎将 LDN 视为负担。“进步”或“亲
力亲为”的患者通常会经历短暂的烦躁,随后在治疗和应对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目前尚
不清楚为什么有些患者根本没有注意到任何效果。
长期使用 LDN(2‑5 年)后客户的证言
“随着我分离症状的减少,我能够应对治疗和生活中的困难任务。我的工
作生活稳定了下来,
减少病假。”
“我感觉自己充满活力,并且能够与自己的情感保持联系。”
“我不再像服用 LDN 之前那样感到孤独。我与其他人和周围环境保持着联系。”
“我能够感知自己的需求和极限,并能保护自己。”
“我的精神危机减少了。”
“不幸的是,我再也无法摆脱慢性疼痛;我对疼痛的感知也增加了。”
LDN 可以用作短期药物还是长期药物?
根据我们的经验,LDN 既适合作为短期用药,也适合作为长期用药。让患者停用 LDN 一段时间有助于
验证 LDN 效应是否仍然存在以及药物是否有效。
根据患者应对 LDN 影响的不同方式,我们制定了三种治疗策略:
如果 LDN 长期有效,则需要永久用药,并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剂量。
当 LDN 的效果不再明显或不再需要其效果时,可进行短期用药。
在需要时进行情境药物治疗 例如,当患者在治疗中遇到困难话题或试图应对特别具
有挑战性的情况时。
LDN 对分离性遗忘症有影响吗?
我们的印象是,LDN 不会动用新的创伤材料,分离障碍似乎仍未打破。然而,更清晰、更少碎片化的感知
和更高的个人认识可以在短期内增加客户对创伤内容的负担。
另一方面,LDN 似乎可以促进客户发展稳定技术和远离创伤记忆的方法,以便更容易地应对这些记忆。
LDN 与其他药物有何区别?
其他药物(如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和情绪稳定剂)通常会减轻症状。因此,患者会感觉更加疏远
他们会感觉与自己格格不入,有时就像灵魂出窍一样。通过 LDN,他们会感到与自己相连,甚至可以获得以前
没有意识到的感觉。当客户能够接触到自己的情绪和自我同理心时,他们经常会描述自己感觉活着,与内心生
活和其他人保持联系。这通常在治疗师和客户的关系中很明显,根据我的经验,这通常是治疗中非常感人的
时刻。当客户在服用 LDN 几天后描述他们变化的感觉时,我经历过很多这样的时刻。对于这些经常感到与自
己脱节的客户来说,这就像恢复了联系一样。
结论
根据我们的经验,LDN 可以成为一种非常有用的药物,用于治疗患有分离性障碍的复杂创伤患者。在 LDN 的
影响下,情绪调节、自我同理心、自我照顾和正念可能会增强。我们用 LDN 治疗的患者发现即使在困难的情
况下也更容易保持现状。因此,创伤记忆和情绪的整合更容易实现,因为患者能够在创伤对抗期间承受痛苦的
情况,保持在“容忍窗口”内,并在出现威胁性情绪时安抚自己。
此外,与以前用于治疗分离和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药物相比,接受 LDN 治疗的患者身上出现的一些新
效果。不仅焦虑症状有所减轻,而且似乎认知思维和情绪感知之间产生了新的联系,这可能导致自我意识、自
我反省和自我同理心的增强。在 10 年的标外处方 LDN 之后,我们得出结论,它是一种心理治疗药物,因为它
可以帮助患者温和地接触他们的内心生活和过去的痛苦。
考虑到心理治疗致力于发展自我护理策略,它可以在心理治疗中起到辅助作用。事实上,LDN 治疗应该伴随
心理治疗,因为药物的效果需要中介和整合。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效果有不同的解读。
目前,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经验,我们只能推测患者从 LDN 中获益的先决条件是什么。需
要对患者的状况、应对能力以及改变和发展的动机进行个性化评估,但预测治疗成功率仍然很
困难。我们希望未来的研究能进一步阐明这些前景。
ULRICH LANIUS 博士和 GALYN FORSTER 硕士
在本章中,我们讨论了使用纳曲酮(尤其是 LDN)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截至本文发
表时,尚无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使用 LDN 治疗 PTSD。然而,根据我们基于数百例病例的
临床经验,LDN 为难治性 PTSD 提供了一种有希望的干预选择,特别是对于有多重创伤
和发育创伤史的个体。
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是对创伤性生活事件的慢性反应,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军
事战斗、自然灾害、机动车事故、性侵犯、医疗创伤或意外失去亲人。PTSD 症状通常包括
过度兴奋、侵入性思维、夸张的惊吓反应、闪回、噩梦、睡眠障碍、情感麻木以及持续回避
与创伤相关的刺激。据报道,社区样本中 PTSD 的终生患病率约为 8%。1通常,PTSD 与
多种身体健康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有关,包括工作困难和社会功能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
十
创伤和分离
PTSD,复杂性 PTSD,发展性
2
人格解体:感觉与自己失去联系。
现实感丧失:感觉世界扭曲或不真实。
C‑PTSD 最近被纳入国际
疾病分类 (ICD‑11)。《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 (DSM‑5) 中与 C‑PTSD 最相
似的诊断是 PTSD 分离性亚型。3 C‑PTSD 也与发展性创伤的概念有关,当儿童面临巨
大压力,而他们的照顾者没有帮助减轻这种压力,或者是压力的根源时,就会发生这种创
伤。其中一些儿童会继续
发展为 PTSD 或其他精神健康障碍,但许多儿童不会。然而,他们面临着一系列复杂
的情绪、认知和身体疾病的风险,这些疾病通常会影响他们的一生。4因此,有发育创伤史
的人经常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精神和生理症状,包括严重的分离症状。5这些症状往往难以
治疗,而且通常对标准的创伤治疗方法反应很小或根本没有反应。6与单纯性 PTSD 患者
相比,患有 C‑PTSD 的人的分离体验水平明显更高。7 分离症状因类型和严重程度而异。
它们通常会影响人的身份、记忆和意识,以及自我意识和对周围环境的意识。它们可能包
括以下内容:
与单纯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相比,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C‑PTSD) 通常是在有
童年创伤史(包括长期虐待、忽视或成长过程中的其他逆境)时诊断出来的。C‑PTSD 形
成的关键是长期反复经历人际创伤,而个人几乎没有机会逃脱。患有 C‑PTSD 的人通常
合并症的发病率较高,包括但不限于重度抑郁症、广泛性焦虑症、物质使用障碍、恐慌症
和强迫症。
身份混乱:感觉不到自己;行为举止令人通常会觉得冒犯或憎恶。
失忆症:无法通过医学解释的记忆问题。
严重的记忆丧失,例如忘记重要的个人信息。
情感失调:处理强烈情绪的问题。
情绪突然发生意外的变化,例如无缘无故感到非常悲伤。
抑郁和/或焦虑。
其他认知(思维相关)问题,例如注意力问题。
强迫症状:感到被迫以某种方式行事。
易患疼痛障碍:慢性/持续性疼痛问题增多。
根据我们的经验,LDN 对 PTSD 具有有益的作用,特别是在存在明显的分离症状时,并且它作为心
理治疗的辅助药物干预具有明显的益处,远远超出了抗抑郁药等更传统的药物干预所提供的益处。
PTSD 与身体健康越来越多的文献强调,PTSD 患者和其
他精神疾病患者罹患其他慢性身体疾病的风险增加。除了公认的 PTSD 心理社会症状外,还有大量证
据表明,与创伤应激障碍相关的多种生物因素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这需要我们拓宽对 PTSD 的概念。
虽然目前仅根据心理和行为症状来诊断 PTSD,但 PTSD 与免疫系统和炎症系统的改变之间可能存在
联系。8
例如,在大量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越战老兵样本中,博斯卡里诺发现常见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
率有所增加,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牛皮癣、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和甲状腺疾病。他认为,慢性创伤后应
激障碍(尤其是伴有多种合并症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 C‑PTSD)与所有这些疾病都有关。他特别指
出,存在与多种炎症性疾病相一致的生物标记,包括
心血管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例如,临床上 T 细胞计数较高、标准化延迟皮肤超敏反应测试中的高反应性免疫
反应、临床上免疫球蛋白‑M 水平较高、临床上脱氢表雄酮水平较低)。9
同样,最近一项针对 666,269 名伊拉克和阿富汗退伍军人的研究证实了 PTSD 与自身免疫性疾病之间的
关联:患有 PTSD 的退伍军人被诊断出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是没有任何精神疾病的退伍军人的两倍,
与患有除 PTSD 之外的其他精神疾病的退伍军人相比,风险高出 50% 以上。相比之下,所有其他精神疾病的
影响大小都小于 PTSD。10具体而言,Miller 等人在一篇评论中提出:
常见并发症包括慢性疼痛、心脏代谢疾病、神经认知障碍和痴呆症。创伤后应激症的标志性
症状 反复出现创伤的感觉记忆 与威胁和压力相关的神经生物学通路同时激活有关,这
些通路在睡眠障碍和生理兴奋增强的背景下发生。新出现的证据表明,这种压力持续综合症
的分子后果包括全身氧化应激和炎症水平升高。11
压力引起的阿片类药物系统功能改变或受损会直接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 (HPA) 轴的免疫调节功能,
因此不仅在极端压力下,而且在儿童早期创伤后,免疫系统功能受损都可能存在。这使得使用 LDN 干预阿片
类药物系统成为潜在治疗干预的合理途径。12
内源性阿片类药物、压力和
解离
解离至少部分由内啡肽和内源性阿片类药物介导,这可以解释麻木、意识模糊和认知障碍(包括失忆症)等
解离现象。13 研究人员几十年来都知道,遭受巨大创伤通常会导致持续的镇痛。在战斗中受伤的士兵所需的
吗啡剂量通常比在非战斗环境中受伤的患者所需的剂量低得多。14应激性镇痛 (SIA) 是多种创伤应激形式
中一种有据可查的现象。急性应激时释放内啡肽具有明显的生存优势。动物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抚慰伤口
以减轻疼痛会严重损害其防御能力。多种动物模型可能与我们对创伤性解离的理解有关。这些模型包括研
究 SIA、习得性无助 (LH) 和强直性静止 (TI) 的模型。15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动物对压力的常见反应,至少部
分是由阿片类药物介导的。此外,这些反应是固有情感反
应的一部分,不仅发生在动物身上,也发生在人类身上。16
感觉、情绪、防御反应和创伤后应激障碍防御反应是面对威胁时固有的情绪反应,旨在最大程度地提
高生存率。当我们想到
创伤后应激障碍和一般威胁时,最常想到的防御反应是战斗和逃跑,但还有其他防御反应。潘克塞普确定了
以下哺乳动物固有的防御情绪:寻求保护、愤怒(或战斗)、恐惧(或逃跑)和恐慌(或无法动弹)。17这些
防御反应通常以层级方式发生,部分表现为基于个体差异,包括遗传倾向以及威胁的性质和背景。
最初的反应是寻求与他人的亲近以获得安全,或者,对于孩子来说,寻求一个主要的依恋对象来保护自
己 通常是妈妈或爸爸。如果在面临威胁时得不到这样的支持,RAGE 通常会被调动起来抵御攻击者。如果
攻击者体型更大或恰好是主要的依恋对象,RAGE 不太可能
充分动员起来,并发起下一个防御反应,即恐惧。
幼儿发起这种积极的防御反应 逃跑 往往是不成功的:无法逃脱。这会导致恐慌和无法动弹,最终导致副
交感神经崩溃。神经系统的副交感神经激活与 SIA 同时发生,最终导致 TI 和伴随的 LH。
对于试图逃跑的小孩来说,固定不动(也称为强直性固定不动)是一种不得已的防御行为,至少部分由
阿片类药物激活介导。这是一种天生的、根深蒂固的防御行为,其特征是暂时的深度运动抑制状态。18 TI 与
束缚应激有关,后者具有相似的特征。TI 部分由内源性阿片类药物介导,作用于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 (PAG)
中的阿片类受体,PAG 是中脑上部的一个结构。例如,当将 β‑内啡肽直接注射到 PAG 中时,它会产生类似于
固定状态的严重紧张症。19此外,对腹外侧 PAG 进行阿片类药物刺激会增加固定状态,这种效果可以通过
阿片类拮抗剂纳洛酮逆转。20据报道,PAG 功能和连接的改变最近与 PTSD 有关。21事实上,固定状态可能
是创伤应激和免疫系统功能的结合点:Farabollini 等人认为,由于急性束缚而导致的固定状态会诱发阿片
类药物介导的免疫系统效应,特别是在腹内侧下丘脑和 PAG 中。22
依恋、创伤和内源性阿片类药物内源性阿片类药物系统在人类依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参
与维持亲和行为的
脑回路恰恰是阿片类受体最丰富的脑回路。23吗啡可以抑制分离痛苦反应,消除婴儿的分离哭声以及母亲
对此的反应。24这表明内源性阿片类药物系统在维持社会依恋中起着重要作用。25
Schore 认为,虐待和/或忽视,包括头两年内感官输入不足,尤其是触摸,会对
31
使用 LDN 治疗 PTSD:历史和背景Ulrich Lanius 博士自 1999 年以来
在使用常规剂量纳曲酮
治疗 PTSD 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此外,Schore (2001) 认为,不良童年经历导致的过度唤醒和分离为儿童后期、青少
年期和成人期的 PTSD 奠定了基础。28 C‑PTSD 中阿片类药物功能的改变也可能导致
与创伤应激综合征相关的多种合并症,包括重度抑郁和焦虑症。29因此,儿童期阿片类
药物系统的改变可能会因成年期创伤导致的阿片类受体结合改变而进一步加剧,这使
得 LDN 成为 PTSD (尤其是 C‑PTSD)药物干预的潜在候选药物。30
影响人类大脑的主要调节系统,即眼眶前额叶边缘系统。26动物研究表明,生命最初几周
缺乏照料会减少扣带回中阿片类受体的数量。27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的忽视和缺
乏照料是否会对阿片类系统产生类似的影响,导致阿片类受体减少。这可能会降低人类
体验快乐的能力,同时由于阿片类结合位点数量减少,大脑更容易受到阿片类药物的影
响,导致分离倾向。
虽然许多接受常规剂量纳曲酮治疗的患者受益匪浅,但其
他人也经历了负面副作用,约 30% 的患者在首次服药时经历了一些胃部不适。32 2002 年,一名患者出现严
重的发育创伤和早期医疗创伤。她有纤维肌痛病史,并有严重的分离症状,包括严重的失忆症。医生给她开了常
规剂量的纳曲酮(每天 50 毫克),成功
缓解了持续的分离症状。不幸的是,这也导致记忆障碍被打破,患者自发回忆起之前分离的记忆材料;这让
患者非常不知所措。
当时,Lanius 博士刚刚通过另一位使用 LDN 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客户了解到低剂量纳
曲酮,因此提出了对低剂量纳曲酮进行经验性试验的可能性。医生给这位客户开了每天 3
毫克纳曲酮(每 1 公斤体重约 0.06 毫克纳曲酮)。她不仅从纤维肌痛症状的减轻中受益,
而且还从人格解体和现实解体以及自我状态不受控制的转换减少中受益 这与常规剂量
纳曲酮的益处非常相似,但没有像高剂量那样打破记忆障碍。有趣的是,客户发现将剂量增
加到每天两次(BID)3 毫克,有时增加到每天三次(TID)3 毫克,实际上增加了纳曲酮对分
离症状和纤维肌痛症状的益处。降低剂量的纳曲酮似乎与常规 50 毫克剂量具有类似的益
处。
纳曲酮剂量
目前,尚无公认的、正式确⽴的用 LDN 治疗 PTSD 的给药方案。有一些研究使用常规和高
剂量的纳曲酮(每天 50 至 400 毫克),但只有两项研究专注于 LDN:一项是针对抑郁症
的试点试验,另一项是用 LDN 治疗分离和复杂创伤的研究。33关于纳曲酮,已报告了非线
性剂量效应。34也就是说,效应的大小不一定与剂量成正比。有人认为,极低和高剂量最有
效,中等剂量则效果较差。Belluzzi 和 Stein 报告称,高剂量纳曲
酮可能激活突触后受体位点,而低剂量可能优先作用于突触前受体位点。35一些患者可
能从高剂量纳曲酮对突触前 mu、delta 和 kappa 受体的阻断中受益更多,而其他患者可
能对低剂量更微妙的影响反应更好,主要影响 mu 受体。
更为复杂的是,Collin 等人证明,kappa/强啡肽阿片类药物系统(负责介导烦躁不安)
对 mu/内啡肽系统有调节作用,但对 delta 受体则无调节作用。36 虽然尚未得到证实,但
双向调节可能存在,即
mu 系统也对 kappa 系统发挥调节作用,因此 LDN 可以通过间接下调 kappa 活性来缓
和烦躁不安。
与通常用于治疗免疫系统功能障碍的 LDN 相比,我们发现 C‑PTSD 患者通常对每天
多次剂量(通常每天两次)的反应更为积极,这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过度警觉、焦虑和
分离症状。在某些情况下,PTSD 症状对每天三次甚至每天四次 (QID) 的给药方案反应更
好。大多数 C‑PTSD 患者对基于体重的剂量反应良好;我们发现正常情况下的理想剂量约
为每公斤体重 0.06 毫克。例如,对于体重约为 180 磅(81.6 公斤)的人来说,这相当于每
天服用两次约 5 毫克的剂量。有趣的是,这是酒精成瘾大鼠停止寻求酒精的相同剂量比。
患有 C‑PTSD 和同时发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个体通常对每日两次或有时更频繁的
给药反应有所改善。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反应模式是否是 PTSD 所独有的,可能归因于
PTSD 中阿片类受体结合的改变。37
虽然大多数患有 C‑PTSD 的人可以⽴即耐受全体重剂量的 LDN,但有些人更喜欢其
他给药方案。一般来说,创伤幸存者一开始服用的 LDN 剂量要低于全体重剂量。系统中因
压力而产生高阿片类药物紧张度的人(根据我们的经验,约 30% 被诊断患有 C‑PTSD
或分离性障碍的人)在服用纳曲酮时会出现一些提示阿片类药物戒断的症状。此类戒断症
状(通常是恶心和胃部不适)在使用 LDN 时通常很轻微,但可以通过更缓慢地引入 LDN
完全避免。
这也避免了那些被诊断患有并发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可能出现的自身免疫症状。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通常会以 0.5 毫克或 1 毫克的剂量引入 LDN,然后根据体重将剂量增加到
目标剂量,以患者可以忍受的速度增加。在最初几个月内,剂量通常会多次调整,因为患者
正在适应药物并且一般生物功能正在恢复。
极佳的灵敏度和低剂量的纳曲酮
剂量
对于某些极其敏感的个体,更低的起始剂量可能更有益。对于有多种过敏和/或敏感症(包括对药物
和环境物质过敏)的人,以及对于那些似乎具有普遍高度敏感的神经系统的人,我们建议不同的初始
剂量以进一步将副作用的可能性降至最低:例如,从 1 毫克开始,增加到每天两次,然后再增加 1 毫克
的剂量。剂量逐渐增加,直到达到上述公式推荐的量。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患者感到不知所措或出现任
何负面影响,可以维持较低剂量或进一步减少,直到他们适应为止。对于某些人来说,低于公式建议的
每日剂量会更好。对于极其敏感的个体,即使是 0.5 毫克或 1 毫克的剂量也可能太多。
他们可能需要低至 0.01 毫克的剂量(通常以液体制剂形式开具),并且可能需要非常
缓慢地增加剂量。对于一些患有严重分离性身份障碍 (DID) 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有时每
天仅 2 毫克的剂量差异就可能导致他们接触到自我的自杀部分和不接触自我的自杀部
分。
虽然大多数 C‑PTSD 患者报告称,服用 LDN 后睡眠质量有所改善,噩梦减
少,但一小部分患者会出现睡眠中断的情况,尤其是在适应 LDN 的早期阶段。在
这种情况下,最后一剂应在当天早些时候服用,减少剂量,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完
全避免服用。有时,早期服用晚间剂量没有效果的患者在治疗后期会得到良好反
应。
复杂影响:情感恐惧症和情感
不宽容
恐惧和/或回避情绪,以及情绪麻木和/或感觉迟钝是 PTSD 的常见症状,尤其是 C‑PTSD。根据我们
的经验,无法、准备不足或不愿意接触情绪体验会损害患者耐受正常 LDN 剂量的能力。这在具有不
良依恋历史、自我意识分裂并学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感受情绪的个体中很常见。在某些情况下,
明显的积极情感恐惧症:患者已经认识到感觉良好或放松是不安全的。38正在从毒瘾中恢复的患
者应该接受这方面的筛查。
当针对这一群体进行工作时,心理教育非常重要。
LDN 减少分离,导致一些患者最初误以为自己情绪的增加是件坏事。没有分离的缓冲,更明显地感
受到所有情感,尤其是体验积极情感,可能会感到难以承受,一开始可能会感到厌恶。对于这些个
体,尤其是当他们对其他环境刺激也极其敏感时,定期服用 LDN(特别是在治疗早期)可能会引发
焦虑或难以承受,因此通常建议非常缓慢地滴定 LDN 剂量或降低基线剂量。通常,安全关系中的
心理治疗干预将使患者提高对自己情绪和 LDN 的耐受力。
一般而言,当接受 LDN 治疗的患者报告感到情绪困扰或不适,且这种感觉超出了其他地方提到
的最初短暂的副作用(见第 1章)时,临床医生应排除这种反应是由情感恐惧症引起的可能性。这
种共同的积极情感恐惧症概念对临床医生和普通人群来说都具有挑战性,因为积极情绪可能会让
人感觉不好的想法违背了常理。
一位在混乱、缺乏照料的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客户报告说,在服用 LDN 后的前六个小时内,他的
所有情绪都变得更加强烈,而积极情感尤其令人生畏。
尽管如此,他说这对他来说是值得的,因为积极的影响大于消极的影响:他脚部的神经病变被消除
了,精神迷雾散去了,他可以重新找到自己的想法并正确看待问题,而且他在家里和工作中的效率
都提高了许多。
另一位客户报告说,当她开始接受 LDN 治疗时,“一开始,感受事物会让人筋疲力尽,但现在,
有了感觉,能够哭泣而不是与感觉脱节,这是一种解脱。”她还表示,“一开始,接受心理咨询很重
要;如果被困在同样的旧思维模式中,我不知道该如何利用新获得的清晰思维。”
纳曲酮和解离:药物吸收问题Lanius 和 Corrigan 认为 C‑PTSD 中的解离过程可能
会干扰药物的正常吸收或代谢。
39这可能部分解释了药物对这一人群缺乏疗效以及产生矛盾作用的原因。对于正在服用需要
达到特定血液水平的药物的患者或服用高剂量其他药物的患者来说,与 LDN 同时服用的药
物吸收改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对于服用华法林(一种血液稀释剂和抗凝剂)的患者来说,特定的血液浓度是一个问题。
个体剂量通过测量国际标准化比率 (INR) 来确定。Lanius 和 Corrigan 报告了一个服用华
法林的客户的案例,对于该客户,添加 LDN 显著改变了 INR 比率,因此需要调整华法林剂量。
40因此,在患者已经服用高剂量其他药物的情况下添加 LDN 可能会增加出现副作用的可能
性。Lanius 和 Corrigan 描述了一名有广泛性忽视病史的患者,该患者出现发育障碍、精神分
裂症和 C‑PTSD。该患
者被开具了高剂量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但对其反应不显著。添加 LDN 后,患者突然对抗
精神病药物产生了明显的副作用。
随着抗精神病药物剂量的降低,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减轻,功能显著改善。这一反应与文献
中阿片类拮抗剂可以增加抗精神病药物反应的说法一致。41
Lanius 和 Corrigan 进一步描述了几个病例,其中单独使用 LDN 或单独使用抗抑郁药
均没有显著的治疗效果。然而,添加 LDN 增强了其他药物的治疗效果。
文献中描述了这种现象,即阿片类拮抗剂增强了对抗抑郁药的反应。42强迫症、难治性抑郁症、
饮食失调和戒烟患者也报告了类似的效果。43这些增强药物效果和血液药物浓度升高的临
床观察表明,LDN 可能对
吸收可能继发于或伴随减少分离症状。鉴于这种血药浓度改变的经验,以及开始使用 LDN
后对其他药物产生副作用的情况,我们建议对正在服用高剂量其他药物或被开具依赖特定血
药浓度的药物的患者要格外谨慎并密切监测。
LDN 的临床效果:增强自我调节Lanius 和 Corrigan (2014) 认为阿片类拮抗
剂(包括 LDN)可显
著帮助 C‑PTSD 创伤患者通过减少分离症状保持在耐受范围内。44 LDN 似乎可以减少过
度唤醒、闪回、侵入性症状和过度警觉,同时提高注意力功能。情绪调节和/或自我调节以及对
情绪和身体感觉的耐受力通常会得到改善。述情障碍(情绪麻木)和自残行为通常都会减少。
通过进食来舒缓情绪的行为减少,大多数患者的食欲和食物摄入量往往得到更好的调节,但
饮食失调通常对更高剂量(每天至少 50 至 100 毫克)的反应要好得多。
自我状态之间不受控制和不可预测的切换减少,同时自我各部分之间的共同意识增加,从
而增加了个人自我意识的连续性。随着分离症状的减少,通常不仅不动和无助感减少,而且自
信行为增加,同时个人自主感增强。
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患有记忆丧失症的患者,其记忆力往往会下降。对于 LDN 患者,这种情
况通常非常缓慢地发生。结合情感耐受力的提高,这往往不成问题:患者不必突破分离障碍,
而是能够选择他们想要关注的问题,强迫性思维和反复思考往往会减少。
鉴于阿片类药物系统在焦虑调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会怀疑焦虑会增加,正如文
献中有时报道的那样。45在我们的客户中,他们都处于
心理治疗关系,当开始使用 LDN 时,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发生过。然而,在未解决的情感恐惧症患者中,
激动通常被解释为焦虑,直到他们学会忍受感受情绪的体验。在缺乏稳定的人际关系或治疗关系的情
况下,LDN 有可能令人厌恶,通常在治疗开始时。通常,这可以通过减少剂量来控制,尽管在极少数情
况下,患者对常规剂量的纳曲酮反应更好。
案例研究
以下是我们众多患有 C‑PTSD 的患者的案例研究的一小部分,选择这些案例研究是为了让人们了解
广泛的客户群以及 LDN 通常可以缓解的各种创伤相关症状。博士。
Lanius 在之前的出版物中提供了更多的案例研究和讨论。46
患有军事 PTSD 的越战老兵:愤怒、抑郁和焦虑一名拥有丰富战斗经验以及童年创
伤的越战男性老兵被诊断患有 C‑PTSD。他自
称是一个幸存者和刺激瘾君子,总是在奔波,常常在成功触手可及的时候离开。他脾气暴躁,有严重的
愤怒管理问题,并且患有发作性抑郁症,包括他所描述的“黑洞”感觉。他曾两次参加退伍军人管理局
的 PTSD 住院治疗项目,并报告说他“尝试了 [他] 能找到的每一种处方药和非处方药,试图帮助 [自
己] 感觉好些。”他每天吸食大麻来改善情绪,每晚服用唑吡坦来改善睡眠。
在接受心理治疗期间,他开始每天服用一次 2 毫克 LDN,在副作用很小后,将其增加到每天两次。
他保持这个剂量(标准的一半,即 0.06 毫克/千克/体重)和使用频率大约两年。LDN 作为眼动脱敏和
再处理 (EMDR) 的辅助手段
心理治疗,在这两年里,他减少了大麻的使用,并停止使用唑吡坦作为助眠剂。
他对LDN的效果如下:
在服用 LDN 之前,我经常有一种处于恐慌边缘的感觉:恐惧是类固醇。当我第一次
开始服用纳曲酮时,我感觉到一种类似苯丙胺/安非他明的快速反应,但这只持续了
几天。尽管如此,我⽴刻感到脚踏实地,能够专注于生活的“当下”。
“脚踏实地” 对我来说是关键词。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感觉自己
像是在一台搅动的洗衣机里努力漂浮。现在,我能够感受到我的所有情
绪,并首先看到我的想法,而不是像我自己的反应的奴隶一样⽴即采取行
动。有了 LDN,我在行动或不行动之前有额外的一秒钟时间思考⋯⋯
我感觉自己自由而有活力,就像我 10 岁
时那样,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吓得要死”。
由于沟通不畅,他的剂量一直保持在 2 毫克,而不是逐渐增加到目标剂量 4 毫克。当他将剂量增
加到 3.5 毫克时,他的焦虑和发作性抑郁症状进一步减轻。在下一次台球锦标赛中,他没有像往常一
样在压力下窒息,而是获得了第一名。在将剂量增加到 4 毫克后,他打电话说:“我痊愈了!我感到精
神集中,有一种深深的幸福感,我不再等待另一只鞋子掉下来!”
该患者服用 LDN 已超过八年,且未出现并发症。
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阿富汗退伍军人:
过度警觉、注意力不集中和睡眠
困难
一名 26 岁的男性退伍军人,曾在阿富汗服役三次,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符合 PTSD 的标准。他还报
告有严重抑郁症病史。他的抑郁症发作通常每隔几个月持续两周。他生长在一个经常搬家的军人家
庭。他报告说,他成长过程中没有亲密的朋友。
他每晚睡眠时间长达10个小时,但睡眠质量非常差。
睡眠研究显示,他晚上醒来大约 200 次,但有趣的是,他没有睡眠呼吸暂停。他报告说他赛跑
想法、难以完成想法、强迫型思维以及注意力和记忆力问题。
极度过度警觉使他感到暴露无遗、脆弱不堪,并且极度不信任他人。在餐厅和演讲厅,他总是背靠
墙坐着,或者坐在能看清周围环境的位置,但他仍然难以集中注意力。注意力和与注意力相关的记忆问
题导致了学业问题。他报告说,当他尝试使用 SSRI 抗抑郁药时,它削弱了他的情绪和动力,加重而不
是减轻了他的抑郁。
在心理治疗创伤治疗的早期,他开始在晚上服用 5.5 毫克(0.06 毫克/千克/体重)的 LDN。他⽴
即发现入睡更容易了(以前他需要阅读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他开始整夜安睡,醒来时精神饱满。
当他开始在早上服用 LDN 时,他发现自己在课堂上的过度警觉减少了,在其他学生身边时也更
加放松了。他报告说,当他站在足球比赛中喧闹的学生区时,他能够享受生活,而不会因为被推搡而感
到愤怒和焦躁。他不再需要避开人群,可以在白天而不是深夜购物,而且他大多数时间都不会感到怀
疑和愤怒,而是“感觉好玩又友好”。
服用 LDN 几个月后,他停用了几个星期的早晨剂量,但发现过度警觉又复发了,白天变得更加烦
躁和难以集中注意力。当他恢复早晨剂量时,过度警觉⽴即像以前一样减轻了。
由于无法让退伍军人管理局支付配药费用,该患者将 50 毫克的药片切成约 5 至 6 毫克的剂量。
在离开心理治疗中心之前,他服用了八个月的 LDN
治疗。
伴有强迫症症状、药物滥用和肠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问题
一名体重 190 磅(86.2 公斤)的 30 岁男性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他有童
年创伤,以及与安保工作相关的创伤,这使他面临持续的威胁。他表现出极度过度
警觉、强迫症
类型症状(包括拔毛癖)、积极情感恐惧症、焦虑、惊恐发作和睡眠障碍/剥夺。
他患有慢性胃病和消化问题,传统药物治疗无效。使用 sn‑1 单月桂酸甘油酯补充剂
治疗改善了念珠菌过度生长的可能性,但肠道问题仍然存在。在接受 LDN 治疗前三个
月,他似乎通过 EMDR 疗法有效地克服了创伤。然而,他的过度警觉和焦虑仍然很严重,
他继续反复思考。
第一次早上服用 4.5 毫克 LDN 后,他最初感觉变化不大,但第二天报告说他感觉
更积极,焦虑感略有减少。在增加下午剂量后,焦虑和对触发事件的反应性有所降低。虽
然焦虑和反复思考也有发生,但强度和持续时间都较短。服药 10 小时后,焦虑和抑郁
再次出现,直到他服用下一剂 LDN。中午服用 3 毫克可提高 LDN 水平,并减少焦虑和
抑郁感。
他的思维更加清晰。他不再为做决定而苦恼,变得更加果断。阅读暴力犯罪的描述
(这是他研究生课程的一部分)对他的 LDN 产生了更强烈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分离
反应和情感麻木的中断。他还报告说,过度警觉减少了,因此他不再觉得有必要关注餐
厅、酒吧或教室里每个人的所作所为。
此前,这已经影响到他在公共场合自如社交的能力。
用他的话说:“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第三人称来观察自己;而通过 LDN,
我发现自己以第一人称来体验生活。在 LDN 期间与人交谈时,我可以变得风趣幽默,就
像我遭受所有创伤之前一样。在社交活动之后,我感觉没有必要像过去那样在脑海里重
温整个事件。”
LDN 似乎打断了他适度吸烟的习惯。他报告说:“抽完半支烟后,我就把它扔掉了,
因为我不喜欢它的味道和气味。服用 LDN 11 或 12 小时后,我又恢复了原来的习惯,我
会把整支烟都抽完。”饮酒也遵循类似的模式。和朋友出去时,如果他最近服用了 LDN,
他可以在喝两三杯后停止饮酒。
服用 LDN 11 或 12 小时后,他似乎已无法打破导致他吸烟和饮酒的分离性恍惚状态,旧模式又
重新出现。但当 LDN 发挥最大效力时,他更能全身心投入当下,而不是处于恍惚状态
状态。
使用 LDN 后,肠道问题很快开始改善,他可以进食而不会腹胀和疼痛。第 2 周,他将治疗方案增
加到早上 7 点 4.5 毫克,上午11 点和下午 3 点3 毫克,睡前 4.5 毫克。开始此治疗方案两周后,肠道
问题几乎完全解决。经过多年的肠道疼痛,他又开始正常消化食物了。他不再“每天、全天”胃灼热,
也不再需要抗酸药或质子泵抑制剂 (PPI)。他认为不再需要服用 sn‑1 单月桂酸甘油酯补充剂,几周
后,LDN 对他不再起作用。恢复补充剂后,LDN 再次快速有效地减轻了焦虑并支持了健康的肠道功
能。
服用 LDN 的前几个晚上,他睡了一整晚,然后又恢复了长期的凌晨 2:30 醒来的习惯(在他原
来的街区,酒吧凌晨 2 点关门)。凌晨 2:30 服用 3 毫克后,他在半小时内又睡着了。睡前(大约午
夜)服用 5 毫克 LDN,他开始睡整晚。
最初,他的注意力和阅读记忆力受到了干扰。我们认为,这一困难是因为他养成了不断查看互联
网的学习策略,这种策略是为了适应他长期的过度警惕和扫描周围环境以寻找威胁的需要。
大约四周后,这种情况就解决了;大约在同一时间,他的肠道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支持副交感神经放
松、休息和恢复。LDN 似乎正在帮助他的大脑和肠道适应更安全的当前现实。
LDN 减轻了他的多种 PTSD 症状,并加快了创伤愈合速度。截至撰写本文时,他已服用 LDN 大
约两到三次,持续了 18 个月。
创伤后应激障碍、忽视、绑架和家庭暴力:
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情绪化饮食
一名 48 岁的女性在早期遭受忽视和虐待、绑架和长期家庭暴力,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尽管
她
当她接受心理治疗时,她已经摆脱了一段虐待关系两年了,她的前伴侣仍然对她的生活产生着持续的负
面影响。
她的症状包括极度过度警觉、持续焦虑、频繁惊恐发作和社交受限。她的睡眠受到严重干扰,部分原因
是创伤主题的噩梦使她害怕入睡。她还正在接受风湿病专家的治疗,以治疗家族性冷诱发自身炎症综
合征 (FCAS)(一种罕见的遗传综合征)和肠易激综合征 (IBS)。
在冬季,她使用秋水仙碱预防性治疗 FCAS,以防止肾脏损害并控制因寒冷引起的发作。发作包括发
烧、关节炎、肿胀和疼痛。她报告说,在症状出现的前半小时内使用高 CBD 大麻食品通常可以控制
FCAS 症状并防止发作。萘普生也用于治疗炎症相关疼痛。
她开始服用 LDN,每日剂量为 2.5 毫克,并迅速将剂量增加到每日三次。两个半月后,她没有增加剂
量,而是将剂量加倍至每日三次,每次 5 毫克。这对她来说非常有效。将剂量增加到每日三次,每次 5 毫
克三天后,她的症状明显减轻:用她的话说,“我⽴刻就不再感觉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弹簧了。我感觉很
正常!⋯⋯
直到焦虑
感消失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焦虑程度有多么严重。”
在接受 Galyn Forster 的治疗之前,这位客户曾短暂接受过舍曲林治疗,但后来停用,因为这种药物导致她产生自杀
倾向。在开始接受 LDN 治疗的同时,她开始使用丁螺环酮治疗抑郁和焦虑。她报告说,这种药物对她来说效果不错,但两
个月后就停用了,因为 LDN 效果更好,而且没有副作用。在开始心理治疗之前,她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阿普唑仑治疗焦虑
和恐慌。她抱怨说,这种药物让她“昏昏沉沉”,在 LDN 和创伤治疗使恐慌减少并消除了大多数侵入性记忆后,她停止使
用这种药物。
阿米替林曾短暂用于治疗失眠,但由于半夜在睡眠状态下喝酒,她停止定期使用。LDN 显著减轻了
失眠,因此她
限制她在极度失眠的情况下使用阿米替林,即当她已经躺了几个小时才清醒的时候。
除了减轻焦虑之外,LDN 还让她不再需要通过食物来控制情绪,她的 IBS 症状几乎和焦虑一样迅速消
退,直至完全缓解。此时,她短暂停止了奥美拉唑治疗,但由于食管裂孔疝,她又恢复使用奥美拉唑,以降低
喉咙受到进一步损害的风险。
几周之内,她就从一个经常因焦虑和恐慌而早退的人,变成了一个很少缺勤的人,并成为了部门的领导
者和导师。她说:“同事们一直在评论我最近性格开朗多了。不再被焦虑所困扰,能够开怀大笑、放松心情,
真是太好了。”她成为了勇气和创造力的典范,想出了如何更有效地应对难缠或愤怒的客户,并找到让同事
和同事享受工作场所的方法。
顾客。
使用 LDN 一个月后,她报告称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有所改善,并且 IBS 持续缓解。她的左膝慢性疼痛
消失了,失眠消失了,她报告称正常的 PMS 症状(易怒和爱哭)也消失了。
两个月后,她报告称 FCAS 发作的频率和强度显著降低。发作时仅持续数小时至一天,而不是过去通常
的三天或更长时间。她将萘普生的用量从每天两次减少到每天一次。她报告称 FCAS 发作时会出现典型的
炎症和关节疼痛,但这是 10 年来第一次发作时没有出现令人虚弱的发烧。
将 LDN 作为心理治疗的辅助手段加速了她的 EMDR 治疗,因为她在治疗过程中能够更好地保持专注,
分离感极少。她还能够更快地解决创伤记忆。
她从一个因焦虑和恐惧而陷入瘫痪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充满力量、快乐、过着富足而有意义的生活的
人。
LDN 本身并不能解决创伤,但它在
过程并继续帮助控制焦虑和过度警觉,以及她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PTSD:情感忽视和性虐待
一名 30 岁的女性,曾遭受过情感忽视和童年性虐待,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当 LDN 作
为心理治疗的辅助治疗引入时,EMDR 疗法更容易让人接受。她报告说,当她与丈夫发生冲突时,LDN
帮助她保持客观。她怀孕了,由于担心早产,在妊娠中期后停止了 LDN。当她的预产期过去后,她重新开
始 LDN。
客户报告:
LDN 极大地帮助我缓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我以前每周会做两到三次可怕的噩
梦。开始使用 LDN 后,我大概每个月、每两个月才会做一次噩梦。LDN 极大地帮助我
缓解了“我知道自己被触发了,我也明白这个事实,但我就是无法停止惊慌失措”的感
觉。LDN 也改善了我与丈夫的关系。我能够更好地平静地谈论情感问题,感觉我们正在
一起解决问题,而不是感到过度挑剔和敏感。
我注意到,当我停止服用 LDN 时,负面经历会更加困扰我,因此我相信 LDN 确实
具有独⽴于其他因素的显著效果。它没有任何负面副作用。我最近正在经历产后抑郁
症;舍曲林很久以前帮助我治疗抑郁症,所以我又开始服用舍曲林,真恶心!它太恶心
了,所以我停用了它,又回到了 LDN,它没有负面副作用。当我服用 LDN 时,副作用很
微妙,但它让我感觉好像刚刚发生了一些好事。同时,我会说我并不像以前那么需要它
了,因为我已经好多了。
该客户定期使用 LDN 超过 3 年,并已持续使用 10 年,以帮助应对更具挑战性的发作
她的生活。
结论
目前的药物和心理治疗往往无法满足许多 PTSD 患者的治疗需求,尤其是那些符合 C‑PTSD 诊断标
准的患者。多种因素(包括阿片类药物系统参与 C‑PTSD 常见症状的有力证据)表明 LDN 可能是一
种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的有用工具。
C‑PTSD 通常与依恋中断和慢性创伤有关。研究表明,早期依恋中断可能会导致阿片类受体密度
改变,这可能有助于为成人 PTSD 奠定基础,而成人 PTSD 又与阿片类受体结合的变化有关。根据这
项研究和我们的临床经验,我们假设,暴露于压力驱动的高水平内源性阿片类药物,再加上阿片类受
体密度降低,不仅会导致 C‑PTSD 的显著分离症状,还可能导致自身免疫和炎症脆弱性,而这些脆弱
性经常出现在遭受慢性创伤和/或发育创伤的人身上。
此外,内源性阿片类系统改变可能与多种分离和 C‑PTSD 相关症状有关,例如人格解体、现实解
体、状态转换、遗忘症、述情障碍、情感失调以及与分离相关的其他现象。
阿片类药物激活在习得性无助、压力引起的镇痛和强直性静止等相关现象中也起着关键作用。
四十七
鉴于内源性阿片类药物活性参与了分离症状的表现,试验 LDN 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也是经
常表现出分离症状的创伤应激综合征患者的一种有前途的治疗策略。其吸引力还在于其作为炎症和
自身免疫问题的治疗方法的既定记录。
我们的临床经验支持了 LDN 是治疗多重创伤患者的可行干预措施这一观点。不仅经典的 PTSD
症状(如过度唤醒、侵入性思维、夸张惊吓、闪回、噩梦、睡眠障碍和情感麻木)
减少,但患者往往会体验到情绪稳定性的提高,包括愤怒减少、自我调节能力提高、意识增强和正念能力增
强。自发状态转换、人格解体和现实感丧失等分离症状通常会减少。此外,LDN 似乎可以缓解抑郁症状,并且
通常会降低焦虑。
LDN 似乎对阿片类药物系统具有调节作用,可直接缓解 C‑PTSD 特有的分离症状。除了针对传统的
PTSD 症状外,它似乎还能缓解与该人群中常见的自身免疫问题和相关全身炎症相关的症状。此外,LDN 具
有经过验证的安全记录,无毒,副作用少,价格低廉且易于获得。与其他药物干预相比,LDN 以相对无副作用
和对生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而著称。这些效果的结合使 LDN 成为治疗 PTSD 尤其是 C‑PTSD 的有希望的
候选药物。
这里描述的所有病例患者要么符合 C‑PTSD 的标准,要么对常规治疗没有显著反应。鉴于他们使用
LDN 的成功,研究人员值得研究 LDN 在 C‑PTSD 和简单 PTSD 中的使用,以及 LDN 与其他干预措施的比
较。无论如何,虽然上述治疗效果看起来很有希望,但使用 LDN 治疗创伤应激综合征必须被视为实验性的,
直到这些效果可以在安慰剂对照的双盲试验中得到证实。最后,我们建议进一步研究对于同时患有 PTSD
和 C‑PTSD 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多次给药的明显益处是否可能归因于阿片类药物系统的改变,以及
LDN 对炎症和其他与免疫系统功能相关的生物结构的影响。
达林·英格尔斯,ND,FAAEM,FMAPS
历史和传播20 世纪 70 年代末,康涅狄格州莱姆
市的一群儿童报告出现神秘的关节疼痛,据信是青少年类风湿性关节炎 (JRA) 的一种。
JRA 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疾病,因此这个小镇上有这么多孩子出现类似症状真是奇怪。
公共卫生官员开始研究可能的传染性病因。他们
在本章中,我将讨论莱姆病的传播方式、诊断莱姆病的复杂性以及治疗莱姆病的传
统和替代方法。我还将探讨莱姆病与免疫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 LDN 在治疗中的相应
应用。
莱姆病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传染病之一,美国每年新增病例超过 329,000 例,欧洲新
增病例超过 85,000 例。1这些数字可能看起来令人震惊,但实际情况是发病率要高得
多,因为许多莱姆病病例被误诊或未报告。莱姆病的症状通常不明显,许多人几个月甚
至几年都得不到正确的诊断或治疗。更糟糕的是,医学界和科学界对诊断和治疗莱姆病
的最佳方法并没有真正的共识。
传染疾病
莱姆病和其他蜱虫病
十一
将血液样本寄给了昆虫学家和微生物学家 Willy Burgdorfer 博士,他是一名政府研究员,也是昆虫传播疾病方面的
专家。经过几年的研究,Burgdorfer 博士终于能够确定病原体:一种新发现的细菌,伯氏疏螺旋体,以其发现者的名
字命名。
虽然伯氏疏螺旋体仍然是美国莱姆病的最常见病因,但研究表明,北美有 100 多种伯氏疏螺旋体菌株,全球有
300 多种,但并非所有菌株都会使人患病。在北美,伯氏疏螺旋体、宫本疏螺旋体和马约尼疏螺旋体是分布最广泛的
菌株,而阿氏疏螺旋体和伽氏疏螺旋体在欧洲最为常见。有证据表明,某些菌株可能比其他菌株产生更强烈的症状,
但需要更多研究来验证这一观察结果。2
大多数莱姆病病例都是由蜱虫叮咬引起的,特别是鹿蜱(技术上称为硬蜱)。大多数公共卫生官员认为蜱虫需
要附着在皮肤上至少 24 到 48 小时才会传播莱姆病,但研究表明,莱姆病可以在蜱虫叮咬后 16 小时内传播。3许多
人认为只有在森林徒步旅行或露营时才会接触到莱姆病,但事实是莱姆病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因为鸟类会将蜱虫
带到以前没有蜱虫的地方。即使是居住在洛杉矶、芝加哥、伦敦、悉尼和纽约市等城市地区的人也会感染莱姆病。全球
有 80 多个国家报告了该病。4 有人推测莱姆病可能通过其他昆虫(如蚊子、跳蚤和苍蝇)传播,但医学文献中并未明
确证实。目前有证据表明,孕妇可能将莱姆病传染给未出生的孩子,导致出生缺陷、死产或发育迟缓。5莱姆病的性传
播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尽管雷·斯特里克博士在某些男性的精液和某些患有莱姆病的女性的阴道分泌物中发现了莱
姆病菌,这表明性传播是可能的。6但是,目前尚无研究表明莱姆病存在性传播,因此莱姆病是否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
仍不清楚。
莱姆病的诊断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莱姆病等由昆虫传播的疾病将每年影响
越来越多的人。
慢性疲劳综合症
肠易激综合征(IBS)
偏头痛
莱姆病发病率的增加被归因于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几个因素,包括冬季气温升高、鸟类迁离其正常栖
息地、蜱虫天敌数量减少以及更多人在温暖的天气里待在户外活动。
风湿性多肌痛
纤维肌痛
图雷特综合症
狼疮
脑膜炎
类风湿关节炎
沮丧
多发性硬化症
阿尔茨海默病
单核细胞增多症(单核细胞增多症)
莱姆病被誉为“伟大的模仿者”,因为它的症状通常与许多其他疾病的症状相似。莱姆病有 100 多种
不同的症状,因此这种臭名昭著的微生物疾病如此难以诊断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这些症状经常被误
认为是其他疾病,人们可能几十年都得不到正确的诊断或治疗。他们可能会看无数医生和专家,得到几
种诊断,却找不到他们感到不适的真正原因。莱姆病可能与 300 多种不同的疾病有关,包括以下几种: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 或卢格里格氏症)
儿童自身免疫性神经精神综合征(PANS)
帕金森病
不安腿综合征
7
如果您被确诊为上述疾病之一,并已苦苦挣扎了数月或数年才找到答案,那么进行
莱姆病和其他合并感染检测可能会有所帮助,至少可以排除这些可能性。在我的诊所
里,我看到许多人的真正病因是莱姆病,一旦我们确定了病因并开始适当的治疗,症状就
会开始改善。获取正确的信息是改善健康和保健的第一步。缺乏早期诊断和治疗会导致
关节、神经系统和肠道的慢性炎症,以及可以攻击任何器官的自身免疫综合症。未经治
疗的莱姆病会导致严重的神经系统损伤、心脏炎症,甚至导致死亡(罕见)。
过去十年来,莱姆病的诊断一直存在争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建议采用两
级检测系统,首先进行莱姆病筛查测试,测量针对莱姆病菌的抗体。如果该测试呈阳性,
则进行第二次更具体的抗体测试,即蛋白质印迹法。如果第二次测试呈阳性,CDC 会将
此视为莱姆病暴露的确认测试。不幸的是,莱姆病的初步筛查测试并不敏感,这意味着
它无法发现许多疾病病例。研究表明,目前的莱姆病筛查测试检测到的莱姆病病例不到
46%。8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些发现,表明莱姆病血液检测在诊断莱姆病方面并不可靠。
在成为自然疗法医师之前,我是一名医学技术员,我曾经在实验室进行莱姆病检测。
假阳性检测并不常见,但假阴性却很常见。这意味着阴性检测结果并不排除患有莱姆病
的可能性。由于这是一种抗体检测,因此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个人的免疫
系统产生抗体的能力;他们是否服用可能干扰检测的免疫抑制药物(如类固醇);他们
被蜱虫叮咬后的时间长度(免疫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以及他们是否患有遗
传或获得性免疫缺陷或其他影响抗体产生的疾病。医生在解释莱姆病检测结果时不会
考虑这些因素,因此有些医生会忽略莱姆病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患者,即使他们有许多症
状。
此外,伯氏疏螺旋体菌株众多,使得莱姆病检测更加困难,因为标准的商业检测只检测伯氏疏螺旋
体。在北美以外,这甚至不是最常见的菌株,因此检测会漏掉任何感染其他类型伯氏疏螺旋体的人。有
些实验室确实提供更全面的检测,并会检测其他伯氏疏螺旋体菌株,但这不是护理标准,许多医生不知
道这些实验室的存在。这又增加了许多人无法及时得到正确诊断的原因。
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莱姆病是一种临床诊断,这意味着它基于莱姆病的体征和症状的存在,
特别是对于那些生活在鹿蜱流行地区的人来说。9因此,莱姆病检测实际上是为了确认是否接触过这
种细菌。
排除其他潜在症状原因非常重要,包括狼疮或类风湿性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巴尔通体病、巴贝斯
虫病或无形体病等其他蜱传感染;以及霉菌或霉菌毒素等环境暴露,等等。
莱姆病经常被忽视,那么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否患有这种病呢?急性莱姆病可能在蜱虫叮咬后 3 至
30 天内发生,并且通常感觉像严重的流感一样。莱姆病的标志性症状之一是看起来像靶心或靶子的
皮疹,技术上称为游走性红斑 (EM) 皮疹。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声称,多达 80% 的莱姆病
患者会出现这种典型的皮疹,但其他研究表明,只有不到 50% 的莱姆病感染者会患上这种皮疹。10出
现 EM 皮疹证实接触过莱姆病,但没有出现皮疹并不排除接触过莱姆病的可能性。
大多数患有急性莱姆病的人感觉不适,需要寻求医疗帮助。急性莱姆病的一些体征和症状包括:
发烧
寒冷
剧烈头痛
持续的、使人衰弱的疲劳
麻木和刺痛
关节和/或肌肉疼痛
淋巴结肿大
贝尔氏麻痹症(面部肌肉张力丧失,一侧或两侧下垂)
游走性红斑(EM)皮疹
如果您足够幸运,能够尽早发现莱姆病并⽴即接受治疗,您的症状可能会很
快消退,您可能会再次感觉良好。如果没有,那么情况就会开始发生变化。您可能
最终会去看多个医生,试图找到您神秘症状的答案。许多莱姆病患者被告知他们
患有慢性疲劳综合症、纤维肌痛、不安腿综合症、多发性硬化症、抑郁症、神经病
变或其他疾病。痛苦持续不断,病情恶化。
如果莱姆病没有得到早期治疗,可能会发展为慢性病。有些人的症状会逐渐恶化,并影响多个身体
系统。莱姆病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因此没有一套特定的症状可以因人而异。慢性莱姆病的一些最常见
症状包括:
游走性关节痛(经常从一个关节移动到另一个关节 这在某种程
度上是莱姆病所特有的)
脑雾和健忘
失眠
慢性腺体肿胀
不明原因的发烧或盗汗
情绪波动和易怒
沮丧
肌肉抽搐
耳鸣
心悸或胸痛
肠易激综合症
甲状腺问题(通常是甲状腺功能减退)
笔迹改变或单词混淆
性功能问题
神经病变恶化,平衡、协调问题
慢性头痛或偏头痛
新发对食物、霉菌、花粉或化学物质的过敏或超敏反应
血压极低或难以维持体温
如上所述,诊断莱姆病的一部分是排除其他类似疾病。在 20 年的实践中,我见过无数
被诊断出患有其他疾病的人,后来才发现他们所经历的症状是由莱姆病引起的。然而,反之
亦然。有一句老话说,“如果你只有一把锤子,那么一切看起来都像钉子”,这句话与一些
莱姆病医生采取的方法再贴切不过了。莱姆病医生很容易通过莱姆病的视角看待整个世
界,而忘记人们有这种感觉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曾经有一位年轻女士因严重的关节疼痛、头痛和情绪波动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看过另一
位医生,医生根据她的症状(她的血液检测呈阴性)诊断她患有莱姆病,并开始对她进行治
疗。她接受了一年多的治疗,症状没有明显改善。
当我见到她时,她提到她的偏头痛从小时候就开始了,而其他症状则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出
现的。
她还抱怨有慢性胃肠道症状,但从未得到过专门治疗。
初次咨询后,我们决定看看她是否有食物过敏或敏感。测试显示她对多种食物有高度反
应,因此我们开始实施消除有问题的食物和舌下免疫疗法的方案,这是一种帮助人们脱敏
过敏的技术(很像过敏针)。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她的头痛几乎完全消失了,她的关节疼痛
和情绪波动都得到了明显改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的所有症状都完全消失了,她又感
觉很好了。
她的情况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系列症状最初看起来像莱姆病,但实际上与莱姆病无
关。根据我的经验,当你治疗莱姆病患者并尝试了多种疗法但都失败了时,很可能还有另一
个尚未确定的罪魁祸首。
其他被误认为莱姆病的常见疾病包括感染
另一种微生物、霉菌毒性、小肠细菌过度生长 (SIBO) 和肥大细胞活化综合征 (MCAS)
等等。
合并感染
莱姆病还不算什么,许多携带莱姆病的蜱虫还会传播其他传染病。公共卫生部门报告
称,在世界上鹿蜱流行的地区,超过 30% 的携带莱姆病的蜱虫还携带多种可致病的其
他微生物。一些与莱姆病同时感染的常见微生物包括:
巴尔通体:一种最广为人知的引起猫抓热的细菌,可引起关节疼痛、疲劳、发烧、
麻木、刺痛和类似妊娠纹的紫色变色痕迹(称为束),但与体重变化无
关。
巴贝斯虫:一种血液寄生虫,是疟疾的近亲,可引起周期性发烧、关节或肌肉疼
痛、疲劳、盗汗以及需要深呼吸的感觉(称为气饥)。
无形体:一种引起严重头痛、发烧、发冷、
恶心、呕吐、肌肉疼痛、腹泻、食欲不振、白细胞计数低等症状;严重时会导致
器官衰竭和出血问题。
埃里克体:一种与无形体相似的细菌。它也会引起严重的头痛、发烧、发冷、恶
心、呕吐、肌肉疼痛、腹泻、食欲不振、精神错乱、白细胞计数低,有时还
会出现皮疹(多见于儿童)。埃里克体可损害大脑或神经系统。与无形体
一样,它也会导致器官衰竭和出血问题。
⽴克次体:一种因引起落基山病而广为人知的细菌
斑疹热,通常以发烧开始,发烧后两到四天出现斑点或斑块状皮疹。它还会
引起头痛、发烧、发冷、恶心、呕吐、肌肉疼痛和食欲不振。
支原体:这是轻度肺炎的主要病原体,会导致持续数周的干咳。
支原体微生物通过吸入另一个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喷出的飞沫传播。但
是,你也可能通过蜱虫叮咬感染支原体,并且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典型的肺
炎症状。支原体可引起关节疼痛、疲劳、头痛和眼睛发炎。
柯克斯体:这些细菌会引起发烧、发冷、肌肉疼痛、疲劳和肠道问题,但关节痛
很少见。它们是 Q 热病的病因。
除了上述微生物外,研究人员还怀疑,伯氏疏螺旋体的另一菌株可能导致一种名为南
方蜱相关皮疹病 (STARI) 的疾病,尽管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STARI 的表现类似于莱姆
病,但皮疹较小,呈靶心状。它会导致疲劳、头痛、肌肉疼痛和发烧。这种疾病不是通过鹿
蜱传播的,而是通过主要在美国西南部发现的孤星蜱传播的。
许多其他微生物可以通过蜱叮咬传播。每年我都会参加一个关于蜱传疾病的会议,
似乎每年我们都会了解到蜱叮咬后导致疾病的新微生物。一些看起来像莱姆病的新疾
病包括波瓦桑病毒、科罗拉多蜱热、土拉菌病和复发性蜱热。如果您有莱姆病症状,请务
必进行其他病原体检测,因为不同微生物引起的症状在临床上有很多重叠。
莱姆病的治疗CDC 建议对早期莱姆病患者进行 10
至 21 天的口服抗生素治疗,如果医生怀疑莱姆病已引起脑膜炎或早期神经症状,则进
行 14 至 28 天的静脉注射抗生素治疗。对于在皮肤上发现鹿蜱并将其拔出,或知道自
己在过去 72 小时内接触过该蜱的成年人,建议使用单剂量 200 毫克的强力霉素。但
是,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单剂量方法有效。只有一项研究对其进行了检查,并且仅对患者
进行了六周的随访。虽然该研究确实发现强力霉素可以抑制靶心皮疹,但它并不一定能
预防更全身性的莱姆病。11
十三 研究表明,多达三分之二的莱姆病患者的症状无法通过常规抗生素疗法得到缓解。
莱姆病的传统治疗方法常常达不到目的,导致全球数百万人遭受慢性莱姆病的折磨。
蜱虫叮
咬后 72 小时过后,抗生素不太可能成功根除莱姆病。14抗生素疗法可能有助于某些症状暂时缓解,但这些症状通常
会在稍后再次出现,因为建议的 10 到 21 天可能不足以完全阻止病原体的生长。国际莱姆病和相关疾病协会 (ILADS)
制定了一套不同的莱姆病治疗指南,并建议更长的疗程 六周抗生素治疗或更长时间,具体取决于患者在此时间后的
感觉。
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它似乎处于休眠状态;免疫系统根本无法识别它。12因此,抗生素更难发挥我们想要
它们发挥的作用。
由于没有客观的测试来确定患者是否好转,因此他们的症状是治疗是否成功的最佳标志。
伯氏疏螺旋体是一种生长极其缓慢的生物,与人体中的其他细菌不同,它能够逃避我们的免疫系统。
我们体内的大多数细菌每 10 到 20 分钟复制一次,但伯氏疏螺旋体每 1 到 16 天复制一次。它还是一
种真正的变形者,可以从一种长而盘绕的细菌变成一个小球(称为圆形体形)。
截至撰写本章时,美国传染病学会 (IDSA) 正在最终确定莱姆病治疗的新指南,该指南将比以前更
加保守,仅要求进行 7 至 14 天的抗生素治疗。许多公共卫生当局(包括 CDC)都已使用 IDSA 指南来
制定莱姆病治疗的公共政策和护理标准。这意味着医生被指示遵循这些莱姆病治疗建议,这可能会给
那些完成治疗但仍有症状的人带来麻烦。
抗生素可以帮助一些莱姆病患者;一旦他们得到治疗,他们就不会再出现症状。但无数其他人对短
期抗生素没有反应,症状仍然持续。虽然长期抗生素治疗可能更有益,但也有
相关风险。抗生素不仅针对伯氏疏螺旋体,还会杀死您体内的一些有益细菌,尤其是肠道,大多数有益
细菌都生活在那里。这会导致某些细菌、酵母菌和其他有害细菌大量繁殖。由于每个莱姆病患者受到
的影响可能不同,因此患者和医生必须权衡长期抗生素治疗的利弊。
我对治疗莱姆病的热情源于我本人的莱姆病经历。2002 年,就在我计划开设自己的诊所的几周
前,我感染了莱姆病。我很早就发现了蜱虫叮咬(是的,我出现了典型的靶心状皮疹),并⽴即开始服
用抗生素。
仅治疗 4 天后,我的症状就消失了,但需要服用 21 天的抗生素。然而,由于我工作时间很长,新生意
刚刚起步,八个月后病情开始复发。我再次出现关节疼痛、疲劳、麻木、刺痛和头痛。我再次开始服用抗
生素,但没有任何改善。近九个月来,我服用了各种抗生素,病情持续恶化,我的肠胃也变得一团糟。
幸运的是,我认识一位纽约市的中医师,他治疗莱姆病,我有几个病人看过他,对他的治疗反应良
好。我去看了他,他给我开了一系列中药方剂和针灸。一个月内,我感觉好了 80%。我意识到我没有以
正确的方式照顾自己 我没有好好睡觉和吃饭,我的身体需要恢复。所以我继续服用中药,更加注意
睡眠和饮食,经过近三年的治疗,我过上了无症状的生活。
我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塑造我与他人治疗莱姆病的方法,并发现这种方法对我治疗的大多数
莱姆病患者都很有效。我制定了一个五步计划,该计划针对整个身体,而不仅仅是依靠杀死莱姆病。像
任何其他感染一样,为什么有些人因莱姆病而病得很重,而其他人却没事?这取决于地形。让您的肠
道、免疫系统、激素和其他必需的信号分子发挥最大作用是帮助您的细胞和器官自我修复和愈合的关
键。这五个步骤是:
1.治愈您的肠道:您的肠道是身体健康的基石,占您免疫功能的 80%。
确保消化和吸收食物、减少炎症和治疗潜在感染对于恢复
健康至关重要。许多莱姆病患者会出现肠漏,本应过滤掉的食物
物质会穿过肠壁并刺激炎症,这可能会导致胀气、腹胀、腹痛和排便
习惯改变。消化酶、益生菌、鱼油和其他营养物质可以帮助修复损伤
并治愈肠道内壁。
2.饮食:我建议遵循碱性饮食,这意味着
吃有助于碱化身体的食物。
大多数细胞在碱性 pH 值下功能最佳,因此食用可保持 pH 值平衡的食物有助于减少炎症
并促进细胞修复。它还能让细胞中的酶发挥作用,使细胞更有效地运作。碱性饮食意味着主
要以植物为主,将动物蛋白和水果的摄入量限制在一周总摄入量的 20% 以下,并
杜绝高酸性食物,如垃圾食品或加工食品、乳制品和咖啡。在尝试了许多其他饮食
后,我发现这种饮食对人们来说是可持续的,而且营养丰富。
3.治疗活动性感染:虽然尚不清楚是否有可能完全根除体内的伯氏疏
螺旋体,但您肯定可以控制它,并与之共存而不出现症状。这有点像
您在 5 岁时得了水痘,然后在 55 岁时得了带状疱疹。由于您的免
疫系统一直在控制它,所以这种病毒已经潜伏了 50 年。但是一旦
您的免疫系统受到损害,病毒就会变得机会主义并开始产生症状。
莱姆病很可能就是同样的情况。我更喜欢使用草药,因为它们可
以有效杀死伯氏疏螺旋体,而不会像抗生素那样损害您的正常肠道
细菌。草药还有其他健康益处
莱姆病有很多好处,包括帮助减少炎症、支持免疫系统、改善血
液流动和增加能量等。有几种草药和草药疗法可用于治疗莱姆病,
因此我建议与了解草药的医生合作,为您找到合适的组合。
4.控制环境:环境中有很多东西会伤害我们并削弱我们的治愈能力,
其中许多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从我们家中和周围使用的化学品,
到我们用于皮肤的个人护理产品,再到我们用来清洁衣服和餐
具的产品,这些化学物质和毒素会在体内积聚,直到我们的肝脏
无法跟上并出现症状。用更安全、更天然的产品替换任何可能有害
的物品是一个好的开始。我在实践中看到,导致疾病的最大环
境因素之一是霉菌。霉菌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但水损坏的建筑
物对健康构成严重风险,霉菌暴露的症状与莱姆病非常相似。
如果您住在老房子里或气候潮湿的地方,最好检查一下家里是否
有霉菌,以确保它不会对您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5.生活方式管理:你的睡眠质量,你
管理压力和身体活动方式都对健康和康复有影响。我们的大脑
和细胞在深度睡眠期间排毒并修复受损组织。许多莱姆病患者
抱怨他们睡眠不安,醒来时感觉精神不振。确保睡眠良好对康
复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要遵循每晚同一时间上床睡觉的规律,睡
前避免使用兴奋剂和电子产品,并在黑暗、安静的环境中获得适
当的睡眠。莱姆病会给您和您的亲人带来压力,因此制定控制压
力的策略有助于缓解慢性疾病对身体和情绪的影响。冥想、生
物反馈和其他
这些技巧可以缓解您白天的紧张情绪。
运动有助于增加血液流动,从而为细胞带来更多氧气和营养。当你感到疲倦,
不想做任何事情时,伸展运动、散步、瑜伽或游泳等温和的运动可以很好地活动身
体,而不会给身体带来额外的压力。所有这些策略都有助于改善你的身心健
康。
最重要的是,没有一种莱姆病治疗方法适合所有人,你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正确治疗方法。有一位
了解莱姆病的医生可以让这个过程变得容易得多。
有关我的全面、全身性莱姆病治疗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莱姆病解决方案:对抗炎症自身免疫反
应和战胜莱姆病的 5 部分计划》。
15
莱姆病和免疫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一个由细胞、器官和化学物质
组成的复杂组织,它们都旨在以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相互“交流”。每个部分都发挥着防止外
来微生物和过敏原伤害我们身体的作用。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开始学习识别哪
些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哪些不是。这个过程对于帮助我们的身体在需要时抵抗感染,然后在感染消
除后关闭这种反应非常重要。
然而,当一些人接触到某种微生物或毒素时,他们的免疫系统就会开始失去对“自身”的耐受性。
为了抵抗感染,免疫系统会意外攻击健康组织,导致炎症和损伤。正常、健康的细胞和器官,包括肠道、
关节、肌肉、皮肤和大脑,都成为免疫系统的目标。这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标志。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细菌和病毒可以触发免疫系统开始对抗自身。16那么免疫系统为什么会如此困
惑呢?答案是所谓的分子模拟。当入侵的微生物含有与你自己细胞中
发现的蛋白质相似的蛋白质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当免疫系统准备好对抗入侵的微生物时,针对
该微生物产生的抗体也会针对你身体中已经感染的部位
类似标记。抗体不再区分什么是你,什么是微生物,而是同时攻击两者。莱姆病的许多症状
可以归因于对莱姆病的免疫反应,而不是伯氏疏螺旋体直接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持续性或慢性莱姆病的许多症状可归因于自身免疫。研究表明,伯氏疏螺旋体外表面有
一种称为外表面蛋白 A (ospA) 的特定蛋白质,其结构类似于我们体内一种称为人类淋巴
细胞功能相关抗原 1 (hLFA‑1) 的蛋白质。17对这种蛋白质的自身免疫反应会导致人们出
现关节疼痛和神经系统症状,即使他们已经接受过抗生素治疗。
许多其他蛋白质也会与莱姆病细菌发生交叉反应,包括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ECGF)、载
脂蛋白 B‑100 和膜联蛋白 A2,这些蛋白质常见于患有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类风湿性
关节炎和狼疮)的人。18一项研究发现,针对莱姆病菌尾部(称为鞭毛)的抗体会与手臂和
腿部神经中的一种蛋白质发生交叉反应,导致麻木、刺痛和疼痛。19还有证据表明,莱姆病
可以触发与大脑发生交叉反应的抗体,导致各种神经症状。20由于潜在的免疫靶点如此之
多,莱姆病患者最终会出现长期自身免疫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幸的是,目前还没有针对莱姆病相关自身抗体的商业化检测。如果您出现发烧、腺体
肿胀和腹痛症状,医生可能会进行血液检测,以寻找导致单核细胞增多症的爱泼斯坦‑巴尔
病毒。但是,如果您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或帕金森病,医生不太可能会寻找可能引起症状的传
染病。我总是很困惑,为什么有些医生不调查许多慢性病的病因。如果你从不寻找病因,就
找不到病因,这并不奇怪。有如此多的证据表明感染与慢性病之间存在联系,您可能会认为
标准治疗方法是进行一系列检测以排除感染,尤其是因为许多感染可以通过简单的血液
检测来确定。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莱姆病和低剂量纳曲酮多年来,我一直成功地为莱姆病患者使用低剂量纳曲酮。
虽然目前还没有研究 LDN 对莱姆病的影响,但研究表明该药物如何调节免疫系统并帮
助“关闭”自身免疫反应。通过改变 Th1/Th2 比率,LDN 似乎关闭了激活自身免疫的开
关。
有证据表明,LDN 可能有助于保护大脑,特别是防止自身免疫损伤。2011 年,研究人员发现,给
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服用 LDN 可减少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这种疾病会导致大脑和脊髓周围的保护
鞘破裂(脱髓鞘)。21由于多发性硬化症和莱姆病之间有许多重叠的症状,因此可能存在类似的机
制来触发这两种疾病的症状,这表明 LDN 可能对莱姆病患者的大脑健康产生类似的影响。然而,还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这是否属实。
莱姆病常常引起肌肉疼痛。一项小型研究发现,LDN 可有效减轻纤维肌痛的肌肉疼痛和炎症症
状。22其他研究发现,LDN 有助于减轻慢性疼痛并改善生活质量,这两者对于莱姆病的治疗都很重
要。
下面,我提供了我治疗过的两名患者的病例报告
莱姆病采用 LDN 和其他疗法相结合的方式治疗。
案例研究 #1
朱莉是一名 47 岁的女性,有 2 年关节痛、疲劳、腹痛、失眠和脑雾病史。她曾去功能医学医生那里看
过病,发现炎症标志物升高,但她的血液检查结果显示没有患上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狼疮、类风
湿性关节炎等)。她的其他粪便检查和血液检查显示她患有酵母菌过度生长,因此她接受了抗真菌
药物治疗。
她的胃肠道症状有所改善,脑雾也略有改善。
饮食改变也有助于减轻她的关节疼痛,并进一步改善她的胃肠道症状,但六个月后她的进展停
滞了。她的
失眠症状没有明显改善。医生对她进行了莱姆病检测,结果呈阳性。随后她被转介到我的办公室接受
莱姆病评估和治疗。
朱莉开始接受草药疗法治疗活动性莱姆病,并接受低剂量免疫疗法,这是一种调节免疫系统对抗
莱姆病的疗法。在接下来的六周里,这种疗法帮助她缓解了疲劳和脑雾。她的关节疼痛也略有改善,但
她仍然睡不好。我开始在睡前给她服用 1 毫克低剂量纳曲酮,以缓解疼痛和睡眠。两周后,病情没有好
转,所以我让她睡前服用 2 毫克低剂量纳曲酮。增加剂量后不久,她报告说睡眠质量有所改善,关节疼
痛略有改善。她告诉我她比以前睡得更深、时间更长。
两周后,我将朱莉的睡前剂量增加到 3 毫克。增加剂量后,她报告说她整晚睡眠充足,排便规律,精
力充沛。三个月后,她的健康状况继续全面改善,但肩膀和手部仍有残留的关节疼痛。我继续将她的睡
前剂量增加到 3.5 毫克。
一个月后,朱莉睡得很好,她的手也不再疼痛。她的握力很好,她能够不受限制地进行所有活动。她
的消化功能继续良好,她不再抱怨脑雾或腹痛。她甚至可以每天滑雪六到八个小时,之后没有任何关
节或肌肉疼痛。朱莉继续在睡前服用 3.5 毫克纳曲酮,并能够减少其他营养补充剂和草药的用量。她
继续感觉良好,过着最好的生活。
案例研究 #2
亚历克斯在与莱姆病斗争多年后来找我。他尝试过各种抗生素和草药疗法,但症状只得到了轻微改
善。他正在应对关节疼痛、疲劳、脑雾、肠道问题和睡眠困难。食物不耐受测试发现他对许多食物敏感,
所以我开始对他进行排除饮食和免疫疗法,以帮助他建⽴对有害食物的免疫耐受性。几周后,他的关
节疼痛有所改善,肠道感觉也好多了。
然后我给他开了 1 毫克的 LDN,并让他每两周增加 1 毫克,直到他能耐受,最高剂
量为 4 毫克。当他睡前服用 2 毫克时,他的睡眠开始好转,醒来时感觉更加放松。他的脑
雾也得到了改善,因为他的睡眠更加稳定。我让他继续服用 4 毫克,因为他耐受性良好,
没有不良副作用。他的精力慢慢好转,但仍然不如预期。
莱姆病会损害线粒体(细胞中产生能量的部分),因此我在他的补充方案中添加了
辅酶 Q10 和乙酰左旋肉碱等营养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亚历克斯的精力明显改善。
他继续在睡前服用 4 毫克 LDN,我将他的剂量增加到 4.5 毫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亚历克斯感觉好多了,可以重新开始锻炼,并做了很多他因为健康问题而停止做的事
情。他的健康状况继续改善,LDN 是他康复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论
我已经用低剂量纳曲酮治疗了数百名莱姆病患者,并且对治疗效果非常满意;我很少看
到副作用。只有少数患者抱怨过梦境逼真或睡眠模式发生变化。我发现许多莱姆病患者
对药物过于敏感,因此我谨慎地从低剂量开始,例如睡前服用 0.5 至 1 毫克,然后每两
周增加一次剂量,直至耐受剂量达到 6 毫克。有些莱姆病患者在服用 1 毫克时反应良
好,而其他患者则需要服用 6 毫克才能看到健康状况的变化。我的方法是从小剂量开
始,然后慢慢增加剂量。我发现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不良副作用,并让身体适应新的
药物和补充剂。
鉴于 LDN 的安全性和潜在的积极益处,我鼓励大多数莱姆病患者尝试它。对于少数
无法在睡前服用的人,我建议在白天服用,这样通常效果更好。作为莱姆病综合治疗方
法的一部分,LDN 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药物,为您提供症状缓解并改变您的免疫系统,
使其更健康地运作。
结语
JILL COTTEL 医学博士
很难相信《LDN 之书》第一版出版至今已经四年了。自那时以来发生了太多事情。
主流医学期刊上发表的有关 LDN 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熟悉低剂量纳曲
酮,许多医生已经开始在实践中开出这种药物。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琳达·埃尔斯古德 (Linda Elsegood) 领导的 LDN 研究基金会的努力,她一
直致力于让医生和患者都了解低剂量纳曲酮。毫不夸张地说,琳达所做的工作确实挽救了生命。
当我写第一本书的序言时,大约有 100 名患者服用 LDN。在此之前,我一直在用电子表格记录每位
服用该药物的患者。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患者数量不断增加。很快,服用 LDN 的患者就超过 300 名,大
约在那个时候,我不再记录这个数字。最终,我感觉我的诊所里服用 LDN 的患者比不服用的患者多,尽
管我确信事实并非如此。
我在 LDN 研究基金会和低剂量纳曲酮方面的工作经历让我受益匪浅。作为一名内科医生和初级
保健医生,我之前的日程安排很平淡,主要负责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胆固醇患者。一天中会偶尔咳嗽、感
冒,偶尔还会扭伤脚踝。
每当有病人出现有趣的症状时,他们就会被迅速送往各个专科医生那里。因此,有大量的
这些疾病我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但从未亲眼见过。
由于我使用低剂量纳曲酮的经验,我现在有机会看到我整个职业生涯中一些最有趣的病例。
其中一些病例非常不寻常,有些则很罕见。医生将这些罕见疾病称为斑马病 这一术语历史上归因于
已故医学教授西奥多·伍德沃德博士。根据 Quote Investigator 网站的说法,俗话说:“当你听到马蹄
声时,不要指望看到斑马。”医学上现在通常使用斑马一词来描述罕见疾病或病症,尤其是当其发生令
人意外时。
多年来,我很荣幸能成为 LDN 研究信托会议的演讲者。2017 年,我发表了题为“初级保健中治疗
斑马”的演讲。
由于我见过许多不寻常的患者,我能够单独就斑马患者做整个演讲。众所周知,LDN 用于治疗多发
性硬化症、纤维肌痛和克罗恩病,这些疾病是我们拥有最多已发表数据。我们还发表了关于其用于治疗
许多其他疾病的病例报告和病例系列,包括炎症性皮肤病、结节病、肥大细胞活化综合征、溃疡性结肠
炎和慢性局部疼痛综合征。
除了治疗患有上述所有疾病的患者外,我的斑马病患者还包括患有中耳肌阵挛、嗜酸性食管炎、强
直性脊柱炎、重症肌无力、埃勒斯‑丹洛斯综合征和寻常型天疱疮的患者。看到这些病例让我着迷,但我
工作中更有意义的部分是会见所有向我讲述他们的故事的非凡患者。
我注意到,来找我寻求低剂量纳曲酮治疗的患者似乎有些不同。我现在希望这些患者具有更高的健
康素养,更精通互联网,并且与他们的健康社区有更紧密的联系。
然而,我与病人的交谈中真正体现出来的是,他们是斗士。他们不是被动接受治疗,也不是听天由命。
他们意志坚定,坚持不懈地寻求帮助。他们拒绝接受“学会忍受”的想法,而这往往似乎是西方医学对
疾病的答案,而这种疾病
没有明显的治疗方法。这种坚决的态度是有帮助的,我认为这也是我的病人康复良好的主要因素之
一。
我可能命中注定要为这类患者服务,因为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就引领我踏上了一条全新的旅程。两
年前,我从一个海岸搬到了另一个海岸,放弃了私人诊所,在一家免费慈善诊所工作,现在我是这家诊
所的医疗主任。我现在治疗的患者虽然在很多方面与我以前诊所的患者大不相同,但与我那些坚定不
移的 LDN 患者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也是幸存者,来自艰难的背景和处境,努力维持生计,同时还要
努力应对健康问题。
当我开始在新诊所工作时,我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不能开低剂量纳曲酮的情况下行医。
我们很幸运在诊所拥有自己的药房,并且能够免费或以象征性的费用向患者提供大多数药物。
然而,LDN 并非随处可见,因为它需要复合和个性化治疗。此外,尽管 LDN 与大多数其他治疗相比并
不昂贵,但我们的患者没有足够的资源来长期负担得起。
令我高兴和惊讶的是,新泽西州的 CareFirst Specialty Pharmacy 挺身而出,向该诊所提供非
常慷慨的捐赠。
由于他们的支持,我们现在能够为一些患者开出 LDN 处方。这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人生的重大改变,以至于
一些患者在离开诊所并购买私人保险后选择自掏腰包支付处方费用。
为服务不足的人群提供服务面临许多挑战。患者通常在患病后期才寻求治疗。他们以前的医疗保
健服务往往缺乏一致性。他们可能存在语言障碍,或者存在读写和教育问题。其他人的健康素养可能
较低,这使得阅读处方瓶或遵循提供者的指示等简单的事情变得困难。
我们的病人经济资源也有限。他们在食物、衣服、交通和住房等基本需求上挣扎。拥有温暖的冬装、
穿着合适的鞋子以及能够去看医生是他们不会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压力
管理和自我护理时间几乎不存在。食物不安全导致营养问题。患者吃任何最容易获
得的食物,通常是营养不足且糖、盐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更容易引起炎症。让患者接
受无麸质饮食几乎是不可能的。
话虽这么说,我最初的想法是,LDN 在免费诊所的效果不会像我以前的诊所那么
好。
从综合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患者中的许多人已经表现良好。他们的饮食干净、营养
丰富、炎症少,而且通常不含麸质。他们的维生素水平和激素水平已经得到优化。大
多数人都有良好的压力管理计划,并有机会定期锻炼。所有这些对于治疗任何疾病
状态的患者都很重要。
考虑到所有这些,我开始治疗少数患有慢性疼痛的 LDN 患者。当我发现患者有
反应时,我非常激动。接受治疗的前 20 名患者在最近的 LDN 会议上记录的病例系
列报告中进行了报告。在这 20 名患者中,大多数是女性,超过一半的患者年龄超过
50 岁。大约一半的患者患有肌筋膜疼痛,另一半患有炎症性或神经性疼痛。
20 名患者中只有 3 名因副作用而停药,这些副作用包括消化道症状、头痛和焦虑
等常见症状。另外 3 名患者因认为没有效果而提前(不到三个月)停药。在 14 名继
续治疗超过三个月的患者中,11 名患者的症状至少有所改善。他们的诊断包括纤维
肌痛或肌筋膜疼痛综合征、慢性区域疼痛综合征、局部神经痛和未另行说明的慢性
疼痛综合征。这些患者中的大多数已经尝试过所有标准疗法来治疗他们的医疗问题,
但均未见效果,因此,找到一种有帮助的方法会让人非常高兴。
我迄今为止在免费诊所治疗 LDN 患者的经历证明了治疗的有效性。研究通常在
原始环境中进行,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患者指导和教育。很多时候,患者群体已
经过筛选,找出最有可能产生反应的群体。高反应率
这项研究可能会报告这一点,但在社区中,医生们并没有在他们的实践中看到同样的结果。不过,我现
在可以说,我已经看到 LDN 对处于最不理想情况下的患者有效。
如果您是一名正在考虑用低剂量纳曲酮治疗患者的医生,这些话应该会让您感到鼓舞。如果 LDN
可以在我们不太理想的现实免费诊所中发挥作用,那么在典型的诊所中尝试一下肯定是值得的。即使
只有一半的患者有反应,您的诊所仍然比以前更好。即使有些患者只有适度的反应,这些患者仍然比
以前更好,尤其是如果他们患有慢性疼痛。
如果您是正在考虑使用低剂量纳曲酮治疗的患者,也应该鼓励您这样做。大多数处方医生(包括
我自己)都会告诉您,这没什么可失去的。LDN 安全、耐受性好、研究充分,并且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
如果您和我一样是已经开具 LDN 处方的从业者,Linda 和我要向您表示感谢。我们参与的人越
多,LDN 的知识传播得就越多。我们的目标是让从业者和患者对低剂量纳曲酮的认识不断提高 与此
同时,增加对需要的患者开具 LDN 处方。
我们可以共同做出改变,让我们的病人和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致谢
我要感谢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给我机会编撰《LDN 书》第2 卷。感谢工作人员,他们出色
地完成了编辑和校对工作;感谢所有贡献者的奉献和辛勤工作,没有他们的付出就不会有第二本
书;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感谢 Paula Johnson 所做的尾注工作 这是一项漫长而繁琐的
任务!
‑附录‑
给药方案
SARAH J. ZIELSDORF,医学博士,理学硕士,MARK MANDEL,
PHARMD 供稿
低剂量纳曲酮是一种廉价的处方药,可用于治疗多种疾病。*由于剂量极低,因此必须配制。患者应
确保由信誉良好的药房配制处方药,以保证已进行质量和安全检查。
我与 LDN 的亲身经历始于 2014 年,当时我的女儿刚产后三个月,我患上了严重的桥本自身
免疫性甲状腺疾病。LDN 让我在一个月内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我也得以完成住院实习。现在,我有
幸作为主治内科医生和诊断师治疗了数千名慢性病患者。我的自身免疫症状通过 4.5 毫克 LDN
得到控制。
我花了些时间并选择重新开始。
29 岁那年,我开车去上班,只开了六英里就无法下车,背部和身体疼痛难忍。在 LDN 的帮助下,
我不再每天忍受慢性疼痛,我的整体态度也更加积极。我已经成为 LDN 的狂热拥护者。
它确实可以纠正低内啡肽水平
状态。
在我 2017 年第一次参加 LDN 会议期间,包括我在内的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一致认为,治疗
剂量方案只有几种,即服用 1.5 至 4.5 毫克的复合
每晚服用纳曲酮(如果导致失眠或严重噩梦,则在早上服用)。正如我在 2019 年会议上了解到的那样,在短短两年内,
我们的治疗方案似乎充满了创造力和多样性。通过定制治疗方案和定制剂量形式,我们的 LDN 研究信托基金的医疗和
研究顾问以及 LDN 临床医生能够分享见解,从而扩大了医疗知识和患者护理的治疗范例。我们正在使用社交媒体接触
更多患者,患者正在向临床医生询问 LDN 的使用情况,并且正在开展更多合作研究。简而言之,自从 Ian Zagon 博士
在 1970 年代假设内源性阿片类药物充当生长因子,以及 Bernard Bihari 博士在 1980 年代初测试使用 LDN 增强对
感染(艾滋病)、自身免疫和癌症的免疫反应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纳曲酮的复合形式
纳曲酮可以配制成多种不同的形式,包括胶囊、片剂、小熊软糖、舌下滴剂、液体、眼药水、片剂、外用洗
剂和透皮乳膏。
口服液 LDN允许滴定剂量从 0.1 毫克到 16 毫克,以及其间任何剂量。
LDN 舌下滴剂最适合吞咽困难的患者
舌下 LDN 滴剂可直接通过口腔黏膜吸收,因此非常适合那些难以适应或无法从
口服液制剂中获益的人。舌下 LDN 滴剂可直接通过口腔黏膜吸收。这样可以加快
吸收速度,并减少胃肠道副作用。
LDN 胶囊可以从 0.1 毫克到任何剂量
处方人员会更喜欢。填充剂在不同的药房可能有所不同,但通常包括蔗糖、
Avicel 或益生菌,具体取决于患者的个人敏感性。
LDN 片剂可以混合并刻痕,因此剂量可以轻松
滴定。
LDN 外用乳液和乳霜通常用于儿童和
牛皮癣等皮肤病。
LDN片剂可制成任意剂量,并可分成四片。
它们在舌下一到两分钟内就会溶解。
其益处与舌下滴剂相当。
剂量指南正如本书各章
节所明确指出的,剂量方案会根据病情或患者类型而有很大差异。
极低剂量纳曲酮(VLDN)
低剂量纳曲酮
超低剂量纳曲酮(ULDN)
50–100毫克
纳曲酮强度 剂量
全剂量纳曲酮
表 A.1. 剂量定义
0.5~16毫克*
1~20微克
* 传统上,LDN 定义的上限是 4.5 毫克,但这一定义已略有放宽。
50–500 微克
天,每两周增加 0.5 至 1 毫克,直至达到 4.5 毫克或最高耐受剂量 3 毫克或以上。
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性脑损伤:从缓慢开始,慢慢增加剂量:每天 1 毫克,持续 14 天,
每两周增加 0.5 至 1 毫克,直至达到 4.5 毫克或最高耐受剂量 3 毫克或以上。虽然 LDN
通常每天使用一次,但对于精神健康问题,每天最多可使用四次。
慢性疼痛:开始缓慢,逐渐增加剂量:每天 1 毫克,持续 14
慢性疲劳综合征/肌痛性脑脊髓炎:可规定每日两次给药(每次 1.5 至 4.5 毫克)
癌症:每天 1.5 毫克,连续服用七天,每周增加 1.5 毫克,直至达到 4.5 毫克。一旦病情
缓解,剂量为 4.5 毫克,连续服用七天;如有需要,开始交替服用三天,停服三
天。
生育/怀孕:慢慢开始并慢慢增加:每天 1 毫克,持续 14 天,每两周增加 0.5 至 1 毫克,直
至达到 4.5 毫克或最高耐受剂量 3 毫克或以上。
是“低剂量,慢剂量”。从低剂量开始,慢慢增加剂量:每天 1 毫克,持续 14 天,每两
周增加 0.5 至 1 毫克,直至达到 4.5 毫克或最高耐受剂量 3 毫克或以上。
自身免疫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经验法则
剂量)。
过敏:一些临床医生对过敏患者给予每天最多三次较高剂量的药物(每次剂量最多 8
毫克)。
行为健康问题:每天最多可以开四次低剂量的药。
儿童: 40 公斤以下的儿童:每公斤 0.1 毫克,从 0.1 毫克开始,四周内增加至计算剂
量。
乳膏的疗效证据很少,但可用于局部给药。体重超过 40 公斤的儿童:按成
人治疗。对于儿童,要特别注意确保家庭成员了解该药物为未经许可的药物。
宠物:每天最多 15 毫克的剂量可用于治疗狗的癌症和慢性疼痛。每天同一时间给药;白
天或晚上都无所谓。
阿片类药物成瘾:剂量为 1 mcg(超低剂量纳曲酮/ULDN),可与阿片类药物
一起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阿片类药物剂量,增加 ULDN 剂量,直
到患者服用 LDN。这应始终在医生监督下进行。请参阅下文,了解阿片类药物
戒断注意事项。
给药时间
通常,LDN 是在晚上服用或给药的,尽管许多人更喜欢在早上服用以避免睡眠障碍。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患者每周跳过一晚服用可获得最大益处,这可能有助于提高受体敏感性。过去建议使用开/停循
环,即服用 LDN 三天,然后跳过几天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效果,但截至上次 LDN 会议,许多 LDN 处
方者认为每日剂量之间的时间间隔反映了阿片类药物/脑啡肽产生的反弹效应,因此受体被重置。
复合 LDN 的质量保证,作者:Mark Mandel,PharmD
经认证的配药药房必须对其配制的药物进行非常严格的质量控制。他们使用纯原料(活性药
物成分/API)
每批原料药的药效已知且有记录(化验证书)。批次相对较小,易于监控。由于认证委员会的监
督职能及其非常严格的规定,患者应收到内容和药效一致的复合产品。
警告化学药
品纳曲酮是一种水溶性药物,市面上有 50 毫克的仿制药片。取一片药片,滴入约 11 毫升水中,每
毫升可获得约 4.5 毫克,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不准确,原因
有很多,包括市售仿制药片的剂量不稳定,而且很容易受到污染。
未经处方在线购买纳曲酮或 LDN 是违法的,而且非常危险,因为您无法知道购买的是什么。
假药看起来与真药一模一样。
然而,它们不会像医药级药物一样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查。它们充其量可能是无害的,不含任何活
性成分,也可能含有致命的有害成分,或者介于两者之间。运往其他国家的处方药如果没有处方
购买,通常会在海关被没收。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不错的交易可能根本不是。永远记住,最昂贵的药
物或治疗方法是无效的!
药物兼容性如果正在接受以下任何一种治
疗,请在开始 LDN 之前与您的临床医生讨论您的个人情况。
生物制剂:只要在开始 LDN 之前进行监测并保持稳定,即可与 LDN 兼容。包
括达克珠单抗 (Zinbryta)、富马酸二甲酯 (Tecfidera)、芬戈莫德
(Gilenya)、干扰素 β‑1a (Avonex、Rebif)、米托蒽醌 (Novantrone)、那他
珠单抗 (Tysabri)、奥瑞珠单抗 (Ocrevus)、聚乙二醇干扰素
beta‑1a(Plegridy)、特⽴氟胺(Aubagio)、醋酸格拉替雷(Copaxone、
Glatopa)、干扰素 beta‑1b(Betaseron、Extavia)。
抗生素:四环素类和氨基糖苷类相容
警告。
类固醇:只要每日剂量小于 20 毫克等效泼尼松龙且不用于器官置换抗排斥治疗,即可使用
泼尼松/甲基泼尼松。只要接受肿瘤学监测,任何剂量的地塞米松均可使用。
短效止痛药(如可待因/曲马多):服用 LDN 前应间隔四至六小时。
氯胺酮:使用氯胺酮时应谨慎使用 LDN。
酒精和曲马多:纳曲酮通常用于缓解对酒精的渴望。对于低剂量纳曲酮,不同个体对 LDN 和同
时服用酒精的反应不同。许多人喝几杯酒都没问题,对 LDN 药物没有反应。然而,在
实践中,我遇到过一些患者在使用 LDN 时出现严重头痛或酒精耐受性下降的情况。
因此,我建议在服用 LDN 后六小时内尝试少量饮酒之前,确保您在不饮酒的情况
下耐受 LDN。据传,一些有酒精‑LDN 相互作用的患者如果在早上服用 LDN,可以耐
受酒精,并适度饮酒,只在晚上。由于曲马多是可待因的合成类似物,通过与 μ‑阿片
受体的选择性相互作用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 (CNS),因此人们担心曲马多与 LDN
一起使用。然而,曲马多的镇痛作用仅被纳曲酮部分抑制。
因此,研究人员认为曲马多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其他方面。1因此,建议曲马
多与 LDN 和酒精间隔六个小时。
阿片类药物:同时服用阿片类药物会增加戒断风险。与短效阿片类药物一起使用时应谨
慎。
禁用缓释阿片类药物或高剂量(缓释吗啡或类似物:MST、羟可酮、地匹哌酮和芬
太尼)。如果正在使用缓释阿片类药物,请改用
替代疼痛控制,并在阿片类药物和 LDN 之间留出四到六小时的间隔。
不相容:正在接受临床试验或服用抗
排斥药物、抗肿瘤坏死因子、程序性死亡配体‑1(PD‑1)抑制剂(检查点抑
制剂包括 Opdivo 和 Keytruda,以及所有同类药物)、抗癌疫苗
CAR‑T 及同类药物。
除非上面描述或警告,否则所有其他处方药均兼容。
患者特殊注意事项在过去五年中,我与数千名慢性病患者和病
情极为复杂的患者打交道,发现具体情况需要对 LDN 进行细致的处方。患有以下疾病的患
者可能有不同的剂量需求,需要仔细考虑。
桥本甲状腺炎患者可能需要更密切的滴定和
在起始阶段,每四至八周检测一次 T3/T4 水平。一般来说,新甲状腺患者从 0.5
毫克开始,通常为液体形式,然后以较小的增量滴定,甚至每周增加 0.1 毫克。
长期甲状腺患者可能能够耐受从 0.5 到 1.5 毫克的常规剂量增量,每两
周增加 0.5 到 1.5 毫克,最高剂量为每晚 4.5 毫克。
慢性疲劳综合征/肌痛性脑脊髓炎患者经常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可能需要缓
慢滴定。如果症状加剧,请减少剂量,直到能够耐受滴定为止。
多发性硬化症患者通常在前八周内症状会恶化。这是正常现象,通常是长期疗效良
好的表现。
莱姆病患者服用多种抗生素和改善病情的抗
风湿病药物治疗者在开始 LDN 治疗之前,应该向经验丰富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和药
剂师寻求谨慎的建议并与他们合作。2
无法耐受常规药物剂量的敏感患者
可能需要从极低剂量纳曲酮 (VLDN) 开始,通常会滴定直至 LDN。
甲状腺药物依赖患者可能需要减少
一旦 LDN 开始起效,就应服用剂量。
吸收不良病例可能需要更高剂量和/或液体形式。
阿片类药物戒断注意事项:建议的 ULDN 剂量为每天两次,每次 1 μg。一项随机、
对照、盲法试验对 719 名患有慢性腰痛的患者进行了研究,他们同时使用每天
80 mg 或更少的羟考酮和每天 2 或 4 μg 纳曲酮进行治疗。对 360 名患者的
最终分析得出结论,每天使用 2 μg 纳曲酮的阿片类药物相关不良
反应最少,包括便秘、嗜睡和瘙痒,此外在积极治疗和戒断后戒断症状也最少。3
阿片类药物戒断的一般建议是逐渐减少剂量
如果患者服用阿片类药物超过一年,则每月减少 10%。对于相对
未服用过阿片类药物的患者(使用时间不超过几周至几个月),可以考虑更
积极的停药,例如每周减少 10%。
使用 ULDN,即使对于长期使用阿片类药物的患者,也可以更快地完成停药。这
是一种通用方法,必须针对每个患者进行个性化治疗。必须采用多学科方法,利
用初级保健、疼痛管理和其他专家来确定适当的治疗计划,并密切监测不良反
应和是否需要更多支持。使用这些微剂量,同时逐一增加和减少阿
片类药物的剂量,目标是成功戒除阿片类药物;许多患者随后逐渐增加至
LDN 剂量。
ULDN 还用于增强阿片类镇痛效果,尤其是针对慢性疼痛患者。
纤维肌痛患者群体是这种组合的受益者。纤维肌痛专家兼内科医生
Ginevra Liptan 博士对此进行了很好的阐述:“关键是找到最佳剂量,
让 LDN 能够镇静神经胶质细胞,但又不会破坏
ULDN可能通过降低神经胶质细胞的敏感性来恢复和增强阿片类药物的有效
性。事实上,ULDN 可能充当阿片类药物反应通路的重置按钮,就像重新启动一台
死机的电脑一样。
5
*您可以在 LDN Research Trust 网站上找到条件列表: www.ldnresearchtrust.org
/状况。
笔记
第 1 章:LDN 的历史和药理学1. MP Stapleton,“詹姆斯·布莱克爵士和普萘洛
尔。基础科学在药物开发中的作用
心血管药理学史”,德克萨斯心脏研究所杂志24,第 4 期(1997 年):336‑42。
2. MD Kertai 等人,“他汀类药物和β受体阻滞剂的组合与
降低接受腹主动脉瘤手术患者的围手术期死亡率和非致命性心肌梗死发生率”, 《欧洲血管和血管内外科杂志》第 28 卷,第 4 期
(2004 年 10 月):343–52。
3. MJ Brownstein,“阿片类药物、阿片肽和阿片受体简史”,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90,第 12 期(1993 年 6 月):5391‑93。
4. O. Schmiedeberg, Über die Pharmaka in der Ilias und Odysse (斯特拉斯堡:Karl J. Trübner,
1918),1‑29;L. Lewin, Phantastica (纽约:Dutton,1931 年)。
5. Reginald L. Campbell 和 R. Everett Langford,《药物滥用简史》,《工作场所药物滥用》 (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刘易
斯出版社,1995 年)。
6. 布朗斯坦,《阿片类药物简史》。
7. Campbell 和 Langford,“药物滥用简史”。
8. JM Scott, 《白色罂粟:鸦片史》 (纽约:Funk & Wagnalls,1969 年)。
9. 印度:SC Dwarakanath,“鸦片和大麻在印度传统医学体系中的应用”, 《麻醉品通报》 17 卷,第 1 期(1965 年):15‑19 页;中国:J. Fort,
“愉悦的赐予者还是罪恶的解放者:亚洲的吸毒和‘成瘾’”, 《麻醉品通报》 17 卷,第 3 期(1965 年):1‑11 页。
10. Campbell 和 Langford,“药物滥用简史”。
11.布朗斯坦,《阿片类药物简史》。
12. Hearne 和 Van Hout,“‘老式药物’:鸦片酊使用者决策、家庭准备和消费模式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药物使用与滥用》第 50 卷,第 5
期(2015 年 4 月):598–608 页。
13. Hearne 和 Van Hout,“ Vintage Meds ”
14. P. Prioreschi,“中世纪麻醉 睡眠海绵”, 《医学假说》第 61 卷,第 2 期(2003 年 8 月):213‑19 页;G. Keil, “睡眠海绵。中
世纪全身麻醉和局部麻醉的里程碑”,《麻醉师》第 38 卷,第 12 期(1989 年 12 月):643‑48 页。
15. FWA Sertürner,“Darstellung der Reinen Mohnsäure (Opiumsäure),Nebst Einer Chemischen
Untersuchung des Opium”, J. Pharm。 f.阿策.阿波化学。 14(1806):47‑93。
16. FWA Sertürner,吉尔伯特的《物理学年鉴》 25 (1817):56‑89。
17. D. Noble,“克劳德·伯纳德,第一位系统生物学家,以及生理学的未来”,
实验生理学93, no. 1 (1993 年 1 月): 16‑26。
18.诺布尔,《克劳德·伯纳德》。
19. J. Sawynok,“海洛因的治疗用途:药理学文献综述”,
加拿大生理学和药理学杂志64,第 1 期(1986 年 1 月):1‑6。
20. MC Michel,“Naunyn‑Schmiedeberg 药理学档案选集”,
Naunyn‑Schmiedeberg药理学档案373,第2期(2006年5月):139。
21. CC Scott 和 KK Chen,《强效镇痛剂 1,1‑二苯基‑1‑(二甲氨基异丙基)‑丁酮‑2 的作用》, 《药理学和实验治疗学杂
志》 87,第 1 期。
1 (1946年5月):63–71。
22. S. Hosztafi、T. Friedmann 和 Z. Furst,“合成和合成抑制剂的结构‑活性关系
半合成阿片类激动剂和拮抗剂”, Acta Pharmaceutica Hungarica 63,第 6 期(1993 年 11 月):335–49。
23. Sankyo Co.,新型吗啡酮和可待因酮衍生物及其制备方法,英国专利 939287 A,1962 年 3 月 9 日提交,1963 年 10
月 9 日颁发;MJ Lewenstein,吗啡衍生物,美国专利 3254088,1961年 3 月 14 日提交,1966 年 5 月 31 日颁
发。
24. “基本药物”,世界卫生组织, http://www.who.int/medicines/services
/essmedicines_def/en。
25. Endo Lab, 14‑羟基二氢去甲吗啡酮衍生物, 1966 年 12 月 6 日提交,并颁发
1967 年 7 月 25 日。
26. CB Pert 和 SH Snyder,“阿片受体:神经组织中的示范”, Science 179,
第4077号(1973年3月):1011‑14。
27. MR Hutchinson 等人,“阿片类药物可能具有 Toll 样受体 4 和 MD‑2
效应”, 《大脑、行为和免疫》第 4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83–95。
28. M. Galanter 和 HD Kleber, 《美国精神病学出版药物滥用治疗教科书》,第 4 版。(华盛顿特区:美国精神病学
出版公司,2008 年 4 月)。
29. K. Miotto 等人,《纳曲酮与烦躁不安:事实还是神话?》, 《美国成瘾杂志》
11,第 2 期(2002 年春季):151–60;ER Zaaijer 等人,“缓释纳曲酮对海洛因依赖患者纹状体多巴胺转运体可用性、
抑郁和快感缺乏的影响”, Psychopharmacology 232,第 14 期(2015 年 7 月):2597–607;“盐酸纳曲酮
50 mg 薄膜包衣片”, medicines.org.uk,最后更新于 2014 年 3 月 5 日, https://www.medicines.org.uk/
emc/medicine/25878 。
30. JE Blalock 和 EM Smith,“免疫系统和神经内分泌系统之间的完整调节回路”,联邦会刊44,第 1 期(1985
年 1 月):108‑11。
31. Blalock 和 Smith,“完整的监管循环”。
32. Blalock 和 Smith,“完整的监管循环”。
33. B. Bihari,“低剂量纳曲酮在 HIV 感染治疗中的作用”, lowdose naltrexone.org,最后修改于 1996 年 9 月,
http://www.lowdosenaltrexone.org/ldn_hiv_1996.htm。
34. Bihari,“低剂量纳曲酮。”
35. IS Zagon 和 PJ McLaughlin,“阿片类拮抗剂诱导的脑和
海马发育:组织学和形态学研究”, 《脑研究》 393,第 2 期(1986 年 8 月):233‑46;IS Zagon 和 PJ McLaughlin,
“阿片类拮抗剂(纳曲酮)
小脑发育的调节:组织学和形态学研究”,神经科学杂志6,第 5 期(1986 年 5 月):1424‑32。
36. RN Donahue 等人,“阿片类生长因子 (OGF) 和低剂量纳曲酮 (LDN)
抑制小鼠人类卵巢癌进展”,妇科肿瘤学122,第 2 期(2011 年 8 月):382‑88。
37. S. Gupta 等编,“淋巴细胞激活和免疫调节机制 X:先天免疫” ,实验医学和生物学进展,第 560 卷(纽约:Springer,2005 年),41‑45。
38. Gupta 等人,“淋巴细胞活化的机制。”
39. C. Giuliani,“NF‑kB转录因子:在炎症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疾病及其治疗意义”,临床治疗学152,第 4 期(2001 年 7‑8 月):249‑53;B. O Sullivan 等人,“NF‑κB 作为自身
免疫性疾病的治疗靶点”,治疗主题专家意见11,第 2 期(2007 年 2 月):111‑22。
40. CS Mitsiades,“在人类多发性骨髓瘤细胞中通过IGF‑1/Akt信号传导激活NF‑κB并上调细胞内抗凋亡蛋白:治疗意义”,
Oncogene 21,第37期(2002年8月):5673‑83。
41. MR Hutchinson 等人,“纳洛酮和纳曲酮对神经性疼痛的非⽴体选择性逆转:Toll 样受体 4 (TLR4) 的参与”, 《欧洲神经科学杂
志》 28 卷,第 1 期(2008 年 7 月):20‑29。
42. Hutchinson 等人,“神经性疼痛的非⽴体选择性逆转”;Rachel Cant、Angus G.
Dalgleish 和 Rachel L. Allen,“纳曲酮在刺激细胞内 Toll 样受体的配体后抑制人类免疫细胞亚群中 IL‑6 和 TNFα 的产
生”,
免疫学前沿8 (2017 年 7 月):809, https://doi.org/10.3389/fimmu.2017.00809。
43. Hutchinson 等人,“神经性疼痛的非⽴体选择性逆转。”
44. Cant、Dalgleish 和 Allen,“纳曲酮在用细胞内 Toll 样受体的配体刺激后抑制人类免疫细胞亚群中 IL‑6 和 TNFα 的产生。”
45. A. Marshak‑Rothstein,“Toll 样受体在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作用”, 《自然》
Reviews Immunology 6, no. 11 (2006 年 11 月):823–35;VD Pradhan 等人,“Toll 样受体在自身免疫中的作用,特别指系
统性红斑狼疮”, Indi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18, no. 2 (2012 年 5 月 ‑8 月):155–60;D. Singh 和 S. Naik,“Toll 样
受体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作用”, Journal of Indian Rheumatology Association 13 (2005):162–65。
46.LAJ O Neill,“癌症中的Toll样受体”, Oncogene 27(2008):158‑60。
第 2 章:慢性疼痛
1.SE Mills 等人,“慢性疼痛:基于人群的流行病学和相关因素回顾”, 《英国麻醉杂志》 123,第 2 期 (2019):e273–e283。
2. TP Jackson 等人,“慢性疼痛的全球负担”, ASA Monitor 78,第 6 期(2014 年):24–27。
3. J. Barcellos de Souza 等人,“慢性疼痛的患病率、治疗、认知和
对生活活动的干扰:基于巴西人口的调查”, 《疼痛研究与管理》 2017 年 (2017):文章 ID 4643830。
4. Jackson 等人,“慢性疼痛的全球负担。”
5. Barcellos de Souza 等人,“慢性疼痛的患病率。”
6. Barcellos de Souza 等人,“慢性疼痛的患病率。”
7. E. Wambre 和 D. Dong,“口服耐受性的形成和维持”,免疫学和
北美过敏诊所38,第 1 期 (2018): 27–37。
8. Wambre 和 Dong,“口服耐受性的产生和维持。”
9. S. Akbari 和 AA Rasouli‑Ghahroudi,“维生素 K 与骨代谢:
《临床前研究的最新证据》, Hindawi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18 年):文章 ID 4629383。
10. V. Nurminen 等人,“人类单核细胞的主要维生素 D 靶基因”, Frontiers in
生理学10 (2019): 第 194 篇文章。
11. MAM Rogers 和 D. Aronoff,“非甾体抗炎药对肠道微生物组的影响”,《临床微生物学和感染:欧洲临床微生物学和传染病学会官方出版物》 22,第 2
期 (2016):178.e1–178.e9。
12. LP James 等人,“对乙酰氨基酚引起的肝毒性”,药物代谢和处置31 (2003): 1499–506。
13. D. Hota 等人,“标签外低剂量纳曲酮治疗难治性糖尿病疼痛性神经病变”,
疼痛医学17, no. 4 (2016 年 4 月): 790–91。
14. D. Trofimovitch 和 SJ Baumrucker,“药理学最新进展:低剂量纳曲酮可作为某些慢性非恶性疼痛综合征的
非阿片类治疗方式”, 《美国临终关怀与姑息治疗杂志》第 36 卷,第 10 期(2019 年 10 月):第 907–12
页。
15. Hota 等人,“标签外低剂量纳曲酮”。
16. F. Birklein 和 V. Dimova,“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征‑最新进展”,疼痛报告2,
第6期(2017年11月):e624。
17. GM Alexander 等人,“CRPS 患者脑脊液促炎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 Pain 116,第 3 期(2005 年 8 月):
213‑19;L. Parkitny 等人,“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征中的炎症: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 Neurology 80,第 1 期
(2013 年 1 月):106‑17。
18. L. Del Valle 等人,“长期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征患者的脊髓组织病理学改变”,《大脑、行为与免疫》第 23 卷第
1 期(2009 年 1 月):85‑91;P. Chopra 和 MS Cooper,“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征 (CRPS) 的治疗
使用低剂量纳曲酮 (LDN)”,神经免疫药理学杂志8,第 3 期(2013 年 6 月):470–76。
19. Chopra 和 Cooper,“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征的治疗”。
20. LR Webster,“Oxytrex:一种羟可酮和超低剂量纳曲酮制剂”, Expert Opinion on Investigational Drugs 16,
第 8 期(2007 年 8 月):1277–83;YHJ Kim 和 K. West,“用低剂量纳曲酮和超低剂量纳曲酮治疗慢性疼痛:一
篇综述论文”, Journal of Pain Management and Therapy 3,第 1 期(2019 年 2 月):1–5。
21. VL Chindalore 等人,“将超低剂量纳曲酮添加到羟可酮中可增强和
延长镇痛时间:Oxytrex 的随机对照试验”, 《疼痛杂志》第 6 卷,第 6 期(2005 年 6 月):392–99。
22. K. Toljan 和 B. Vrooman,“低剂量纳曲酮 (LDN) 治疗应用回顾”,
医学科学(瑞士巴塞尔) 6,第 4 期(2018 年 9 月):82。
23. Z. Li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 (LDN):一种有前途的免疫相关疾病和癌症治疗疗法”,国际免疫药理学第 61 期(2018
年 8 月):178–84。
24. D. Segal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诱导克罗恩病缓解”,
Cochrane 系统评价数据库2(2014 年 2 月):CD010410;JP Smith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疗法改善活动性
克罗恩病”,美国胃肠病学杂志102,第 4 期(2007 年 4 月):820–28。
25. G. Raknes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对炎症性肠病药物治疗的影响:一项准实验性前后处方数据库研究”, 《克罗
恩病和结肠炎杂志》第 12 卷,第 6 期(2018 年 5 月):677–86。
26. M. Lie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用于诱导炎症性肠病患者缓解”, 《转化医学杂志》第 16 卷,第 1 期(2018 年 3
月):55。
27. CE Parker 等,“低剂量纳曲酮诱导克罗恩病缓解”,
Cochrane 系统评价数据库4(2018 年 4 月):CD010410。
28. G. Raknes 和 L. Småbrekke,“低剂量纳曲酮:对类风湿和血清阳性关节炎药物的影响。一项全国性登记册为基础的
对照准实验前
研究之后”, PLoS One 14,第 2 期(2019 年 2 月):e0212460。
29. SJ Peterson 等人,“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的在线调查显示
不满”,甲状腺28,第 6 期(2018 年):707–21。
30. SJ Zielsdorf,“试试 LDN:从 1,000 多名患者使用低剂量纳曲酮的 3 年经验中得出的见解。”该研究于 2019 年 6 月 7‑9 日在俄勒冈州波特兰
举行的 LDN AIIC 2019 会议上发表。
31. A. Alonso 和 MA Hernan,“多发性硬化症发病率的时间趋势:
《神经病学系统评价》 71,第 2 期(2008 年 7 月):129‑35。
32. MT Wallin 等人,“美国 MS 患病率:使用健康声明数据进行的基于人群的估计”,神经病学92,第 10 期(2019
年 7 月):e1029–e1040。
33. Michael D. Ludwig、Ian S. Zagon 和 Patricia J. McLaughlin,“专题文章:多发性硬化症患者血清 [Met5]‑ 脑啡
肽水平降低,低剂量纳曲酮可恢复”,
实验生物学和医学(Maywood) 242,第15期(2017 年 9 月):1524‑33。
34. KA Rahn 等,“实验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预防和表达减弱
低剂量纳曲酮 (LDN) 或阿片类生长因子 (OGF) 长期治疗引起的脑脊髓炎:对多发性硬化症的治疗意义”,脑
研究1381(2011 年 3 月):243–53。
35. Ludwig、Zagon 和 McLaughlin,“专题文章:血清 [Met(5)]‑ 脑啡肽水平
“减少了。”
36. MD Ludwig 等人,“专题文章:OGF–OGFr 通路的调节会改变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和多发性硬化症中的细胞
因子谱”, 《实验生物学与医学》(梅伍德) 243,第 4 期(2018 年 2 月):361–69。
37. M. Gironi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治疗原发性进展型多发性硬化症的试点试验”,多发性硬化症杂志14,第 8
期(2008 年 9 月):1076‑83。
38. BA Cree 等,“低剂量纳曲酮与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生活质量的试点试验”
硬化症”,神经病学年鉴68,第 2 期(2010 年 8 月):145‑50;AP Turel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治疗多发性硬化症:
安全性和耐受性的回顾性图表审查”,临床精神药理学杂志35,第 5 期(2015 年 10 月):609‑11。
39. N. Sharafaddinzadeh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对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一项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
多发性硬化症杂志16,第 8 期(2010 年 8 月):964‑69。
40. G. Raknes 和 L. Småbrekke,“低剂量纳曲酮治疗多发性硬化症:对药物使用的影响。一项准实验研究”, PLoS One 12,
第 11 期(2017 年 11 月):e0187423。
41. B. Ghai 等人,“标签外低剂量纳曲酮治疗难治性慢性腰痛”, 《疼痛医学》 15 卷,第 5 期(2014 年 5 月):
883–84。
42. LR Webster 等人,“Oxytrex 在提供有效镇痛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身体依赖:腰痛随机对照试验”, 《疼
痛杂志》 7,第 12 期(2006 年 12 月):937‑46。
43.Toljan和 Vrooman,“低剂量纳曲酮 (LDN) 治疗利用回顾。”
44. DJ Clauw,“纤维肌痛:临床回顾”,美国医学会杂志311,第 15 期(2014 年 4 月):1547–55;LM Arnold 等人,
“AAPT 纤维肌痛诊断标准”,疼痛杂志20,第 6 期(2019 年 6 月):611–28。
45. Clauw,“纤维肌痛:临床回顾。”
46. Arnold 等人,“AAPT 纤维肌痛诊断标准”。
47. J. Younger 等人,“使用低剂量纳曲酮 (LDN) 作为慢性疼痛的新型抗炎治疗”,临床风湿病学33,第 4 期
(2014 年 4 月):451‑59。
48. J. Younger 和 S. Mackey,“低剂量纳曲酮可减轻纤维肌痛症状:
《疼痛医学》第 10 卷,第 4 期(2009 年 5 月 ‑6 月):663‑72。
49. L. Parkitny 和 J. Younger,“低剂量纳曲酮治疗纤维肌痛八周后促炎细胞因子减少”, 《生物医学》 5,第 2 期(2017 年 4 月):
16。
50. Younger 和 Mackey,“低剂量纳曲酮可减轻纤维肌痛症状”;J.
Younger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治疗纤维肌痛:一项评估每日疼痛水平的小型、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平衡、交叉试验的结果”,
《关节炎与风湿病学》第 65 卷,第 2 期(2013 年 2 月):529–38。
51. S. Metyas 等,“低剂量纳曲酮在纤维肌痛治疗中的应用”, Current
风湿病学评论14, no. 2 (2018): 177–80。
52.Toljan和 Vrooman,“低剂量纳曲酮 (LDN) 治疗利用回顾。”
53. A. Coutinho Jr. 等,“深部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的 MR 成像:图文并茂”
RadioGraphics 2,第 31 期(2011 年 3 月)。
54. J. Mercier 和 K. Miller,“Mercier 疗法帮助不孕妇女怀孕”,
当今助产学105 (2013): 40, 68。
55. CH Choi 等,“子宫切除术后穹窿部医源性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罕见病例”,
妇产科科学54,第5期(2015):319‑22。
56. O. Laghzaoui 和 M. Laghzaoui,“鼻腔子宫内膜异位症:1 个病例的相关情况”, 《妇产科和生殖生物学杂志》(巴黎)
30,第 1 期。 8(2001):786‑88。
57. Milton S. Hershey 医疗中心的 Timothy A. Deimling,“低剂量纳曲酮在
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标准治疗相结合”, Clinical Trials.gov。
标识符:NCT03970330, https://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3970330。
58. F. Malfait 等人,“2017 年 Ehlers‑Danlos 综合征国际分类”,
美国医学遗传学杂志:医学遗传学研讨会175,第 1 期(2017 年 3 月):8‑26。
59. Z. Zhou 等人,“Ehlers‑Danlos 综合征慢性疼痛的治疗:两例病例报告和一篇文献综述”, 《医学》(巴尔的摩)第 97 卷,第 45
期(2018 年 11 月):e13115。
60. DK Patten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在治疗
多发性硬化症、纤维肌痛、克罗恩病和其他慢性疼痛疾病中的慢性疼痛和炎症”,药物治疗学38,第 3 期(2018 年 3 月):382–89。
61. G. Raknes 和 L. Småbrekke,“挪威低剂量纳曲酮 (LDN) 处方量突然前所未有地增加。患者和处方者的特征以及配药模式。药物利用
队列研究”,药物流行病学和药物安全26,第 2 期(2017 年 2 月):136–42。
62. Patten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第 3 章:肠道健康1. Jill P. Smith
和 Leonard B. Weinstock,《炎症性肠病》, 《LDN 之书:鲜为人知的仿制药 低剂量纳曲酮 如何彻底改变自身免疫性疾病、癌症、自闭
症、抑郁症等的治疗》,Linda Elsegood 编辑(佛蒙特州怀特河交界处:Chelsea Green,2016 年),第 55‑68 页。
2. Yi‑Zhen Zhang 和 Yong‑Yu Li,“炎症性肠病:发病机制”,世界胃肠病学杂志20,第 1 期(2014 年):91–99, https://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 /PMC3886036/pdf/WJG‑20‑91.pdf。
3. Laurent Peyrin‑Biroulet 等人,“基于人群的队列中成人克罗恩病的自然史”,美国胃肠病学杂志105,第 2 期(2010 年 2 月):
289–97, https://doi.org/10.1038/ajg.2009.579。
4. Peyrin‑Biroulet 等人,“成人克罗恩病的自然史。”
5. Claire E. Parker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诱导克罗恩病缓解”,
Cochrane 系统评价数据库4(2018 年 4 月):CD010410, https://doi.org/10.1002 /14651858.CD010410.pub3。
6. Dina Ibrahim Tawfik 等,“低剂量纳曲酮治疗
实验性大鼠克罗恩病”,神经肽59(2016 年 10 月):39–45, https://doi.org/10.1016/j.npep.2016.06.003。
7.Tawfik 等人,“治疗效果评估”。
8.Gwenny Fuhler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降低体外内质网应激并刺激肠上皮细胞伤口愈合”(海报展示),欧洲克罗恩病和结肠炎组织,
2016 年。
9. K. Shard,《挪威 LDN 纪录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rBd2gv8UGU0&feature=youtu.be&fbclid
=IwAR2TqrplHgQ6eWSYmcBsYJdb336aES0rXcTswaySchativVljxb8eXufGaw。
10. Guttorm Ranknes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对炎症药物治疗的影响
肠道疾病:一项准实验性处方数据库前后研究”, 《克罗恩病和结肠炎杂志》第 12 卷,第 6 期(2018 年 6 月):677–86, https://
doi.org/10.1093/ecco‑jcc/jjy008。
11. Mitchell RKL Lie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用于诱导炎症性肠病患者缓解”,《转化医学杂志》第 16 期(2018 年 3 月):第 55 篇文
章, https://doi.org/10.1186/s12967‑018‑1427‑5。
12. Jill P. Smith 等人,“阿片类拮抗剂纳曲酮治疗促进活动性克罗恩病的粘膜愈合:一项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消化疾病与科学》 56
卷,第 7 期(2011 年 7 月):2088–97 页。
13. Leonard B. Weinstock,“纳曲酮治疗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
《临床胃肠病学杂志》 48,第 8 期(2014 年 9 月):742, https://doi.org/10.1097 /MCG.00000000000000093。
14. Hans Törnblom 等人,“胃肠动力和神经胃肠病学”,斯堪的纳维亚
《胃肠病学杂志》 50,第 6 期,(2015 年 3 月):685–97, https://doi.org/10.3109/00365521.2015.1027265 。
15. Michael Gershon,“评论文章:血清素受体和转运体 在正常
和异常胃肠运动”, 《消化药理学和治疗学》 20,第 7 期(2004 年 11 月):3‑14, https://doi.org/10.1111/
j.1365‑2036.2004.02180.x。
16. Michael Camilleri,“慢性便秘的新治疗选择:机制、疗效和安全性”, 《加拿大胃肠病学杂志》 25 卷,增刊 B(2011 年 10 月):
29B–35B。
17. J. Grider 和 GM Makhlouf,“阿片类神经元在肠道调节中的作用
蠕动”,美国生理学杂志253(1987 年 8 月):G226–31, https://doi.org/10.1152/ajpgi.1987.253.2.G226 。
18. J. Grider 等人,“生长抑素、阿片类药物和 GABA 神经元在蠕动反射调节中的相互作用”, 《美国生理学杂志》 267(1994 年 10
月):G696–701, https://doi .org/10.1152/ajpgi.1994.267.4.G696。
19. Raymond Jian 等,“甲硫氨酸脑啡肽类似物对运动活动的影响
胃肠道”,胃肠病学93(1987):114‑20。
20. Peter Holzer,“胃肠道中的阿片类受体”,调节肽155(六月
2009):11‑17。
21. Aitak Farzi 等人,“Toll 样受体 4 参与吗啡对
《体外和体内结肠运动》, 《科学报告》第 5 卷,第 9499 号(2015 年 3 月), https://doi.org/10.1038/
srep09499 。
22. M. Jiménez 等人,《阿片类药物诱导鸡的迁移性运动活动》, 《生命科学》
50,第 7 期(1992):465–72, https://doi.org/10.1016/0024‑3205(92)90385‑3。
23. Jennifer Ploesser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治疗胃肠道疾病的副作用和疗效”, 《国际药物配制杂志》 14,第 2 期
(2010 年 3 月 ‑ 4 月):171‑73。
24. Beth Livengood,“胃轻瘫 案例研究”, https://ldnresearchtrust.org/dr‑elizabeth‑
livengood%E2%80%99s‑presentation‑胃轻瘫。
25. Henry Parkman,“纳洛昔康治疗阿片类药物相关胃轻瘫”, ClinicalTrials.gov。标识符:
NCT03036891, https://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3036891。
26. George F. Longstreth 等人,“功能性肠道疾病”,胃肠病学130,第5期(2006 年 4 月):1480‑91;APS Hungin 等人,
“美国的肠易激综合征:患病率、症状模式和影响”,消化药理学和治疗学21,第 21 期。
11 (2005 年 6 月):1365‑75;Yuri A. Saito 等人,“北美肠易激综合征的流行病学:系统评价”,美国胃肠病学杂志97,第 8
期 (2002 年 8 月):1910‑15。
27. Longstreth 等人,“功能性肠道疾病”;Hungin 等人,“肠易激综合征
美国。”
28. Hungin 等,“美国的肠易激综合征”;Saito 等,“流行病学
“北美肠易激综合征”。
29. Hungin 等人,“美国的肠易激综合征”;Saito 等人,“北美肠易激综合征的流行病学”;Bradley C. Martin 等人,“肠易激综合征的利用模式和医疗补助
的净直接医疗成本”,《当代医学研究与观点》第 19 卷,第 8 期(2003 年 10 月):771–80,https: //doi.org/10.1185 /030079903125002540。
30. Hungin 等人,“美国的肠易激综合征”;Longstreth 等人,“功能性
肠道疾病”。
31. Brooks D. Cash 和 William D. Chey,《肠易激综合征的诊断》,
北美胃肠病学诊所34,第 2 期 (2005):205–20;Brooks D. Cash 等人,“诊断测试对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效用:系统评
价”,
美国胃肠病学杂志97,第 11 期(2002 年 11 月):2812‑19。
32. W. Grant Thompson,“通往罗马之路”,胃肠病学130,第 5 期(2006 年 4 月):1552–56, https://doi.org/
10.1053/j.gastro.2006.03.011。
33. Mark Pimentel 等人,“在患有异常的 IBS 患者中发现 MMC 频率较低
乳果糖呼气试验提示细菌过度生长”, 《消化系统疾病与科学》 47 卷,第 12 期(2002 年 12 月):2639–43。
34. Mark Pimentel 等人,“自身免疫将黏着斑蛋白与大鼠模型中空肠弯曲杆菌感染后慢性功能性肠道变化的病理生
理学联系起来”,
消化疾病与科学60,第 5 期(2015 年 5 月):1195–1205。
35. Walter Morales 等人,“肠易激综合征的第二代生物标志物检测
使用血浆抗 Cdtb 和抗粘连蛋白水平”, 《消化疾病与科学》第 64 卷,第 11 期(2019 年 5 月):3115–21,
https://doi.org/10.1007/s10620‑019‑05684‑6。
36. Ali Rezaie 等人,“基于氢气和甲烷的呼气测试在胃肠道疾病中的应用:
北美共识”,美国胃肠病学杂志112,第 5 期(2017 年 5 月):775–84, https://doi.org/10.1038/ajg.2017.46。
37. Mark Pimentel 等,“消除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可减轻肠易激综合征的症状”,美国胃肠病学杂志95,第 12 期(2000 年 12
月):3503‑06。
38. Cash 和 Chey,“肠易激综合征的诊断”。
39. Cash 和 Chey,“肠易激综合征的诊断”。
40. Mark Pimentel 等人,“利福昔明治疗和再治疗对非便秘型 IBS患者的影响”, 《消化疾病与科学》 56 卷,第 7 期
(2011 年 7 月):2067–72 页, https://doi.org/10.1007/s10620‑011‑1728‑5 ; Mark Pimentel 等人,“利
福昔明治疗无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364 卷(2011 年 1 月):22–32 页, https://
doi.org/10.1056/NEJMoa1004409; Jun Li 等人,“利福昔明治疗肠易激综合征: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的荟萃分
析”, 《医学》(巴尔的摩)第 95 卷,第 4 期(2016 年 1 月):e2534, https://doi.org/10.1097/
MD.00000000000002534。
41. Ali Rezaie 等人,“乳果糖呼气试验作为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对利福昔明反应的预测指标”,美国胃肠病学杂志
114,no.
12 (2019 年 12 月):1886–93, https://doi.org/10.14309/ajg.00000000000000444。
42. Anthony Lembo 等人,“对于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利福昔明重复治疗是安全有效的”,胃肠病学151,第 6 期
(2016 年 12 月):1113–21, https://doi.org/10.1053/j.gastro.2016.08.003。
43. Mark Pimentel 等,“基于推测的细菌过度生长,低剂量夜间服用替加色罗或红霉素可延迟肠易激综合征治疗后
的症状复发”, 《胃肠病学与肝病学》(纽约) 5,第 6 期(2009 年 6 月):435‑42;Leonard B.
Weinstock,“利福昔明治疗非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的长期结果”,《消化疾病与科学》 56,第 11 期(2011
年 11 月):3389‑90, https://doi.org/10.1007/s10620‑011‑1889‑2。
44. Revital Kariv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治疗肠易激综合征:一项初步研究”, 《消化疾病与科学》 51 卷,第 12 期(2006
年 12 月):2128‑33。
45. Ploesser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
46. Lawrence B. Afrin 等人,“肥大细胞活化综合征的特征”,美国医学科学杂志353,第 3 期(2017 年 3 月):
207–15, https://doi.org/10.1016/j.amjms.2016.12.013 。
47. Gerhart J. Molderings 等人,“系统性肥大细胞活化疾病的家族性发病”,
PLOS One 8,第 9 期(2013 年 9 月 30 日):e7624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76241 。
48. Cash 和 Chey,“肠易激综合征的诊断”。
49. Mark Pimentel 等人,“乳果糖呼气测试正常化与症状相关
肠易激综合征的改善:一项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研究”,美国胃肠病学杂志,第 98 卷,第 2 期(2003 年 2 月):
412‑19。
50. Lawrence B. Afrin 和 Gerhard J. Molderings,“诊断的简明实用指南
肥大细胞活化疾病的评估”,世界血液学杂志3,第1期(2014 年 2 月 6 日):1‑17。
51. Leonard B. Weinstock 等人,“肥大细胞活化在精准医学时代的重要性”,美国胃肠病学杂志113,第 11 期(2018
年 11 月):1725–26, https://doi.org/10.1038/s41395‑018‑0257‑7。
52. Giovanni Barbara 等人,“靠近结肠神经的肥大细胞活化与
肠易激综合征中的腹痛”,胃肠病学126,第 3 期(2004 年 3 月):693–702, https://doi.org/10.1053/
j.gastro.2003.11.055; Giovanni Barbara 等人,“肠易激综合征中肥大细胞依赖性内脏痛性感觉神经
元的兴奋”,
Gastroenterology 132, no. 1 (2007 年 1 月):26–37, https://doi.org/10.1053/j.gastro.2006.11 .039;
Stefan Wirz 和 Gerhard J. Molderings,“系统性肥大细胞活化疾病患者疼痛治疗实用指南”, Pain
Physician 20, no. 6 (2017 年 9 月):E849–E861。
53. Rezaie 等人,“乳果糖呼气试验作为利福昔明反应的预测指标。”
54. Gabrio Bassotti 等,“排便阻塞时结肠肥大细胞增多及其
与肠道胶质细胞的关系”,消化疾病和科学57,第 1 期(2012 年 1 月):65–71, https://doi.org/10.1007/
s10620‑011‑1848‑y。
55. Cash 和 Chey,“肠易激综合征的诊断”;Mark J. Hamilton,“非克隆肥大细胞活化综合征:越来越多的证据”,《北
美免疫学和过敏诊所》第 38 卷,第 3 期(2018 年 8 月):469–81 页;Fred H. Hsieh,“肥大细胞活化障碍中的胃肠道
病变”, 《北美免疫学和过敏诊所》第 38 卷,第 3 期(2018 年 8 月):429–41 页。
56. Anupam Aich 等人,“肥大细胞介导的痛觉机制”,国际分子科学杂志16,第 12 期(2015 年 12 月)29069–92,
https://doi.org/10.3390/ijms161226151 。
57. Harissios Vliagoftis 等人,“粘膜前沿的肥大细胞”, 《当代分子医学》 5 卷,第 6 期(2005 年 10 月):573–
89, https://doi.org/10.2174/1566524054863915。
58. Leonard B. Weinstock 等人,“肥大细胞沉积和激活可能是导致肠系膜阑尾炎的新原因”,英国医学杂志病例报告
2018 年,bcr–2018–224689, http://doi.org/10.1136/bcr‑2018‑224689。
59. T. Frieling,“治疗抵抗性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肥大细胞活化证据
Bowel Syndrome”, Zeitschrift für Gastroenterologie 49,第 2 期(2011 年 2 月):191–94, http://
doi.org/10.1055/s‑0029‑1245707 ; Lei Zhang 等人,“肥大细胞与肠易激综合征:从实验室到临床”,
Neurogastroenterology and Motility 22,第 2 期(2016 年 4 月):181–92, http://doi.org/10.5056/
jnm15137; Beatriz Lobo 等人,“口服色甘酸二钠下调腹泻‑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粘膜肥大细胞活化和免疫反
应:一项初步研究”, 《欧洲联合胃肠病学杂志》 5,第 6 期(2017 年 10 月):887–97, http://doi.org/
10.1177/2050640617691690; Tamira K. Klooker 等人,“肥大细胞稳定剂酮替芬降低内脏高敏感性并改善肠
易激综合征患者的肠道症状”, Gut 59,第 9 期(2010 年 9 月):1213‑21, http://doi.org/10.1136/
gut.2010.213108。
60. Leonard B. Weinstock 等人,“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在肥大细胞活化综合征中很常见”, 《美国胃肠病学杂志》第
114 期,2019 年 ACG 年会摘要(2019 年 10 月)。
61. Anneleen B. Beckers 等人,“关节过度活动引起的胃肠道疾病
综合征/埃勒斯‑丹洛斯综合征活动过度类型:胃肠病学家的综述”,
Neurogastroenterology & Motility 29,第 8 期(2017 年 8 月):e13013, https://doi.org/10.1111/nmo.13013
; John K. DiBaise,“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 (POTS) 和胃肠道:胃肠病学家入门指南”,美国胃肠病学杂志113,第
10 期(2018 年 10 月):1458–67, https://doi.org/10.1038/s41395‑018‑0215‑4。
62. Suranjith L. Seneviratne 等人,“Ehlers‑Danlos 综合征中的肥大细胞疾病”, 《美国医学遗传学杂志》C 部分:
医学遗传学研讨会175,第 1 期(2017 年 3 月):226–36, https://doi.org/10.1002/ajmg.c.31555; Emily
M. Garland,“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超越直⽴不耐受”, 《当前神经病学和神经科学报告》 15,第 60 期
(2015 年 7 月), https://doi.org/10.1007/s11910‑015‑0583‑8; Taylor A. Doherty 等人,“体位性心动过速
综合征和肥大细胞活化的潜在作用”,
自主神经科学215 (2018 年 12 月):83–88, https://doi.org/10.1016/j.autneu.2018.05.001 。
63. Pimentel 等人,“乳果糖呼气测试正常化与症状相关
改善”;Susan V. Jennings 等人,“肥大细胞增生症协会关于肥大细胞疾病的调查:患者体验和看法”, 《过
敏与临床免疫学杂志》 2,第 1 期(2014 年 1 月 ‑2 月):70‑76, https://doi.org/10.1016/j.jaip.2013.09.004;吉
尔·斯科菲尔德
Lawrence B. Afrin,“肥大细胞活化综合征患者药物辅料反应性的识别和管理”, 《美国医学科学杂志》 357,
第 6 期(2019 年 6 月):507–11, https://doi.org/10.1016/j.amjms.2019.03.005; Lawrence B. Afrin 等
人,“肥大细胞活化疾病和微生物相互作用”,临床治疗学37,第 5 期(2015 年 2 月):941–53, http://doi.org/
10.1016/j.clinthera.2015.02.008; Aarane M. Ratnaseelan 等人,“霉菌毒素对神经精神症状和免疫过程的影
响”,临床治疗学40,第 6 期(2018 年 6 月):903–17, https://doi.org/10.1016/j.clinthera.2018.05.004。
64. Leonard B. Weinstock 等,“体位性直⽴性心动过速的成功治疗和
使用纳曲酮、免疫球蛋白和抗生素治疗肥大细胞活化综合征”,
英国医学杂志病例报告2018(2018 年 1 月):bcr‑2017‑221405, https://doi.org/10.1136/bcr‑2017‑221405 。
65. K. Iida 等人,“肺结节病患者的 T 细胞亚群和 β 趋化因子分析”, Thorax 52,第 5 期(1997 年 5 月):431–
37, https://doi.org/10.1136/thx.52.5.431。
66. Robert P. Baughman 和 Jan C. Grutters,“肺结节病的新治疗策略:抗代谢物、生物药物和其他治疗方法”,《柳叶
刀呼吸医学》第 3 卷,第 10 期(2015 年 10 月):813–22, https://doi.org/10.1016/S2213‑2600(15)00199‑
X。
67. Miguel Giovinale 等人,“非典型结节病:病例报告和文献综述”,
欧洲医学和药理学评论13,第 1 期(2009 年 3 月):37‑44。
68. Leonard B. Weinstock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治疗结节病”,
结节病血管炎和弥漫性肺疾病34,第 2 期(2017 年 8 月):184–97, https: //doi.org/10.36141/svdld.v34i2.5303。
69. Gaelle Guettrot‑Imberta 等人,“肠系膜脂膜炎”, La Revue de Médecine Interne 33,第 3 期。
11 (2012 年 11 月):621–27, https://doi.org/10.1016/j.revmed.2012.04.011。
70. Mahmoud R. Hussein 和 Saad R. Abdelwahed,“肠系膜脂膜炎:最新进展”, 《胃肠病学与肝病学专家评论》 9,第 1 期(2015 年 1 月):67–78,
https://doi.org/10.1586/17474124.2014.939632 。
71. Mamoon H. Al‑Omari 等,“肠系膜脂膜炎:计算机断层扫描比较
《恶性肿瘤患者和非恶性肿瘤患者的研究结果》, 《临床和实验胃肠病学》 2019 年第 12 期(2018 年 8 月):
1‑8, https://doi.org/10.2147/CEG.S182513。
72. Eli D. Ehrenpreis 等人,“恶性肿瘤患者腹部计算机断层扫描中肠系膜脂膜炎样异常的临床意义”,世界胃肠病学杂志22,第 48 期(2016 年 12 月):
10601–08, https://doi.org/10.3748/wjg.v22.i48.10601 。
73. Nienke van Putte‑Katier 等人,“肠系膜脂膜炎:患病率、临床放射学
表现和 5 年随访”,英国放射学会第 87 卷,第 1044 号(2014 年 12 月):20140451, https://doi.org/
10.1259/bjr.20140451。
74. Michael S. Green 等人,“硬化性肠系膜炎:综合临床回顾”,转化医学年鉴6,第 17 期(2018 年 9 月):336, https://doi.org/10.21037/atm.2018.07.01 。
75. Roberto Mazure 等,“口服药物成功治疗回缩性肠系膜炎
黄体酮”,胃肠病学114,第 6 期(1998 年 6 月):1313–17, https://doi.org/10.1016/S0016‑5085 (98)70438‑
X。
76. Prabin Sharma 等人,“硬化性肠系膜炎:192 例病例的系统评价”, 《临床胃肠病学杂志》 10,第 2 期(2017 年 4 月):103–11, https://doi.org/
10.1007/s12328‑017‑0716‑5 。
77. Grigory Roginsky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治疗症状性肠系膜脂膜炎的开放标签试验的初步结果”, 《临床胃肠病
学杂志》 49,第 9 期(2015 年 10 月):794–95, https://doi.org/10.1097/MCG.00000000000000398。
78. Angus G. Dalgleish 和 Wai M. Liu,《癌症》,Elsegood, 《LDN 书》; S. Zagon 和
Patricia J. McLaughlin,“阿片类生长因子 (OGF) 抑制人类癌细胞的锚定非依赖性生长”,国际肿瘤学杂志24,第 6
期(2004 年 7 月):1443‑48。
79. Wai M. Liu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上调正常剂量下未见的独特基因表达:对其在癌症治疗中的应用意义”,国际肿瘤学
杂志49,第 2 期(2016 年 6 月):793–802, https://doi.org/10.3892/ijo.2016.3567。
80. Renee N. Donahue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靶向阿片类生长因子 ‑ 阿片类生长因子受体通路抑制细胞增殖:来自组
织培养模型的机制证据”, 《实验生物学和医学》(梅伍德) 236,第 9 期(2011 年 9 月):1036‑50,
https://doi.org/10.1258/ebm.2011.011121。
81. Staci D. Hytrek 等人,“间歇性阿片类受体抑制人类结肠癌
使用纳曲酮进行阻断”, Cancer Letters 101,第 2 期(1996 年 3 月):159–64, https://doi.org/
10.1016/0304‑3835 (96)04119‑5。
82. Qiush Wang 等人,“蛋氨酸脑啡肽 (MENK) 通过抑制调节性 T 细胞 (Treg) 改善 50 名癌症患者外周血中的淋巴细胞
亚群”,
人类疫苗与免疫治疗学10,第 7 期(2014 年 4 月):1836–40, https://doi.org/10.4161 /hv.28804。
83. Diego M. Avella 等人,“阿片类生长因子‑阿片类生长因子受体轴
调节人类肝细胞癌的细胞增殖”,美国生理学杂志 调节、整合和比较生理学298,第 2 期(2010 年 2 月):459–66,
https://doi.org/10.1152/ajpregu.00646.2009。
84. Xiaonon Wang 等,“蛋氨酸脑啡肽在体内和体外诱导 G0/G1 细胞周期停滞和胱天蛋白酶依赖性细胞凋亡对胃癌产
生抗癌作用的新机制”,癌症管理与研究2018 年,第 10 期(2018 年 10 月 18 日):4773–87, https://doi.org/
10.2147/CMAR.S178343。
85. Burton M. Berkson 等人,“接受静脉注射硫辛酸/低剂量纳曲酮方案治疗后胰腺癌肝转移患者的长期生存情况”,
综合癌症治疗杂志5,第 1 期(2006 年 3 月 1 日):83–89, https://doi.org/10.1177/1534735405285901 。
86. Burton M. Berkson 等人,“重新审视 ALA/N(α‑硫辛酸/低剂量纳曲酮)
转移性和非转移性胰腺癌患者的治疗方案:3 例新病例报告”,综合癌症治疗杂志8 卷,第 4 期(2009 年 12 月):416–22, https://doi.org/10.1177 /
1534735409352082。
87. Jill P. Smith 等人,“阿片类生长因子改善患者的临床获益和生存率
与晚期胰腺癌”, 《临床试验开放获取杂志》 2010 年第 2 期(2010 年 3 月):37–48, https://doi.org/
10.2147/OAJCT.S8270。
88. Laurent Schwartz 等人,“癌症的代谢治疗:前瞻性病例系列的中期结果”,抗癌研究34,第 2 期(2014 年 2 月):
973–80。
89. Moshe Rogosnitzky 等人,“治疗肝母细胞瘤的阿片类生长因子 (OGF):一种新型非
毒性治疗”, 《临床试验新药》 31 卷,第 4 期(2013 年 8 月):1066–70, https://doi.org /10.1007/s10637‑012‑9918‑3。
90. Ruizhe Wang 等,“阿片类生长因子 (OGF) 与阿片类拮抗剂的相互作用及
它们在癌症治疗中的意义”,国际免疫药理学75 (2019 年 10 月):105785, https://doi.org/10.1016/
j.intimp.2019.105785。
第 4 章:皮肤病1. IS Zagon 等人,“阿片类生长因子
受体的生物学”, 《脑研究评论》
38 (2002): 351‑76。
2. PL Bigliardi 等人,“阿片类药物和皮肤,我们的⽴场是什么?”,实验皮肤病学18,第 5 期(2009 年 5 月):
424‑30。
3. PL Bigliardi 等人,“Mu 阿片受体激动剂对人类角质形成细胞迁移的特殊刺激”,受体与信号转导杂志22(2012
年):191‑99。
4. M. Bigliardi‑Qi 等人,“β‑内啡肽刺激细胞角蛋白 16 表达和
下调人类表皮中的 Mu 阿片受体表达”, 《皮肤病学研究杂志》 114(2000 年):527‑32;M. Bigliardi‑Qi 等
人,“慢性和急性伤口中 Mu 阿片受体的特征以及 β‑内啡肽对转化生长因子 β II 型受体和细胞角蛋白 16
表达的影响”,《皮肤病学研究杂志》 120(2003 年):145‑52。
5.Bigliardi等人,“对人类角质形成细胞迁移的特殊刺激。”
6. PL Bigliardi 等人,“激活 Delta 阿片受体促进皮肤伤口
通过影响角质形成细胞间粘附和迁移来实现愈合”,英国药理学杂志172(2015):501‑14。
7. PL Bigliardi 等人,“阿片类药物与皮肤稳态、再生和衰老 什么是
证据?》,实验皮肤病学第 6 卷,第 25 期(2016 年):586–91。
8. PL Bigliardi 和 M. Bigliardi‑Qi,“外周阿片类药物”,载于 EA Carstens 和 T. Akiyama 所著《瘙痒:机制与
治疗》 (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CRC Press,2014 年);S. Kauser 等人,“β‑内啡肽对人类表皮黑素细
胞生物学的调节”, 《研究皮肤病学杂志》 120(2003 年):173‑180。
9. F. Yuan、H. Xiaozhou、Y. Yilin 等,“阿片类受体功能研究现状”, Current
Drug Targets 13,第 2 期(2012 年 2 月):230–46。
10. Z. Dembic,“Toll 样受体的功能”,居里夫人生物科学数据库,
兰德斯生物科学(2000‑13)。
11. DK Patten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在治疗
多发性硬化症、纤维肌痛、克罗恩病和其他慢性疼痛疾病中的慢性疼痛和炎症”,药物治疗学38 (2018): 382–89。
12. AJ Bower 等人,“局部类固醇治疗后不良反应的纵向体内追踪”,实验皮肤病学25,第 5 期(2016 年 5 月):362–
67。
13. AD Papoiu 和 G. Yosipovitch,“外用辣椒素 ‘热’药之火重新点燃”, 《药物治疗专家意见》
第 11 卷,第 8 期(2010 年):1359 页。
14. J. Rivard 和 HW Lim,“紫外线光疗法治疗瘙痒症”,皮肤病治疗学18,no.
4 (2005): 344。
15. M. Metz 和 S. Stander,“慢性瘙痒症 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和治疗”,
欧洲皮肤病和性病学会杂志24,第11期(2010):1249。
16. M. O Donoghue 和 MD Tharp,“抗组胺药及其作为止痒药的作用”,
皮肤病治疗18,第4期(2005):333。
17. TA Kouwenhoven 等人,“口服抗抑郁药在慢性瘙痒症患者中的应用:系统评价”, 《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
第 77 期第 6 期(2017 年 10 月):1068。
18. BM Matsuda 等人,“加巴喷丁和普瑞巴林治疗慢性瘙痒症”,
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75,第3期(2016年5月):619。
19. D. Sharma 和 SG Kwatra,“沙利度胺治疗慢性顽固性瘙痒症”,
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74,第2期(2016):363。
20. LP Bigliardi‑Qi 等,“皮肤中的 Mu 阿片受体系统及其与瘙痒的关系”, 《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 50,第 3 期
(2004 年 3 月):29。
21. J. Lee 等人,“纳曲酮联合治疗重度瘙痒症老年患者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皮肤病学年鉴28(2016 年):159–63;
W. Siemens 等人,
“成人姑息治疗患者瘙痒症的药物干预”, Cochrane 数据库系统评价11(2016 年 11 月)。
22. NQ Phan,“全身性 Mu 阿片受体拮抗剂止痒治疗:
评论”,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63,第 4 期(2010 年 10 月):680–88。
23. PL Bigliardi,“局部应用阿片受体拮抗剂治疗瘙痒症”,
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56,第 6 期(2007 年 6 月):979–88。
24. Kent Holtorf,《甲状腺疾病》, 《LDN 之书:鲜为人知的仿制药 低剂量纳曲酮 如何彻底改变自身免疫性疾病、
癌症、自闭症、抑郁症等的治疗》 ,Linda Elsegood 编辑(佛蒙特州怀特里弗交界处:Chelsea Green,2016
年)。
25. T. Frech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治疗系统性硬化症瘙痒症”,国际风湿病学杂志(2011 年 9 月 12 日)。
26. T. Tran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成功治疗皮肌炎”,
皮肤病治疗学31,第 6 期(2018 年 9 月):e12720。
27. Z. Xu、L. Zhang 等,“一例患有新 ATP2C1 基因突变的婴儿 Hailey‑Hailey 病
基因突变”,儿科皮肤病学, 28,第2期(2011):165。
28. SM Burge,“Hailey‑Hailey 病:临床特征、治疗反应和
《预后》,英国皮肤病学杂志126,第3期(1992):275。
29. A. Borghi 等人,“氯化镁在治疗 Hailey‑Hailey 病中的疗效:从偶然发现到其对细胞内 Ca(2+) 稳态影响的证
据”,国际皮肤病学杂志54,第 5 期(2015 年):543–48。
30. B. Farahnik 等人,“Hailey‑Hailey 病的介入治疗”, 《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 76,第 3 期(2017
年):551。
31. LN Albers 等人,“使用低剂量纳曲酮治疗 Hailey‑Hailey 病”, JAMA
皮肤病学153, no. 10 (2017 年 10 月): 1018–20。
32. O. Ibrahim 等,“低剂量纳曲酮治疗家族性良性天疱疮(Hailey‑
Hailey 病),” JAMA Dermatology 153, no. 10 (2017): 1015。
33. Albers 等人,“使用低剂量纳曲酮治疗 Hailey‑Hailey 病。”
34. S. Cao 等,“Hailey‑Hailey 病患者对纳曲酮的不同反应”, JAMA
皮肤病学154,第3期(2018):362。
35. C. Riquelme‑McLoughlin 等人,“良性慢性天疱疮(Hailey‑Hailey 病)的低剂量纳曲酮疗法:病例系列”, 《美
国皮肤病学会杂志》第 81 卷,第 2 期(2019 年 8 月):644–46。
36. M. McBride,“低剂量纳曲酮治疗顽固性 Hailey‑Hailey 病”, 《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第 81 卷,第 4 期(2019
年 10 月):AB264。
37. A. Alajmi 等人,“纳曲酮和镁成功治疗 Hailey‑Hailey 病”,
JAAD 病例报告5,编号。 9(2019 年 8 月):760–62。
38. S. Sonthalia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诱导 Hailey‑Hailey 病缓解
通过局部联合使用氯胺酮和苯海拉明维持缓解”,印度皮肤病学在线杂志10,第 5 期(2019 年 8 月):567–70。
39. DA Mehregan 等,“扁平苔藓:45 例患者的临床和病理学研究
患者”,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第 27 卷,第 6 期,第 1 部分(1992 年 12 月):935–42。
40. S. Vano‑Galvan,“额叶纤维化脱发:355 名患者的多中心回顾”,期刊
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70, no. 4 (2014 年 4 月): 670–78。
41. A. Tosti 等人,《绝经后妇女额叶纤维化脱发》,《 Journal of the
美国皮肤病学会52,第 1 期(2005 年 1 月):55‑60。
42. N. Atanaskova Mesinkovska 等人,《扁平苔藓与甲状腺疾病的关系:一项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 《美国皮肤病
学会杂志》 70,第 5 期
(2014): 889。
43. E. Racz 等,“额叶纤维化脱发和扁平苔藓的治疗:系统综述”, 《欧洲皮肤病和性病学会杂志》 27,第 12 期
(2013 年 3 月):1461;C. Chieregato 等,“扁平苔藓:30 例病例报告及文献综述”, 《国际皮肤病学杂志》
42,第 5 期(2003 年):342。
44. EK Ross 等,《原发性瘢痕性脱发的最新进展》,《美国科学院院刊》
皮肤病学杂志53,1号(2005):1。
45. Mehregan 等人,“地衣平毛虫”。
46. C. Chiang 等,“羟氯喹和扁平苔藓:疗效和扁平苔藓活动指数评分系统介绍”, 《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 62,
第 3 期(2010 年 3 月):387‑92;E. Racz 等,“额叶纤维化脱发和扁平苔藓的治疗:系统评价”,《欧洲皮
肤病和性病学会杂志》 27,第 12 期(2013 年 3 月):1461。
47. LC Strazzulla 等人,“使用低剂量纳曲酮治疗扁平苔藓的新方法”,
《皮肤病学药物杂志》 16,第 11 期(2017 年 11 月):1140–42。
48.美国国家牛皮癣基金会,“牛皮癣病因和诱因”, https://www.psoriasis.org /causes/ (2018 年 10
月)。
49. JL Lopez‑Estebaranz 等人,“银屑病家族史和年龄对中度至重度银屑病患者合并症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来自
ARIZONA 研究的结果”,《皮肤病学杂志》第 43 卷,第 4 期(2016 年):第 395 页。
50. F. Elsholz 等人,“钙 健康和疾病中角质形成细胞分化的中心调节剂”, 《欧洲皮肤病学杂志》 24 卷,第 6 期
(2014 年):650–61。
51. EG Harper 等人,“Th17 细胞因子在体外和体内刺激角质形成细胞中的 CCL20 表达:对银屑病发病机制的影响”,
《研究皮肤病学杂志》 129,第 1 期。
9 (2009):2175;NJ Wilson 等人,“产生人类白细胞介素 17 的辅助 T 细胞的发育、细胞因子谱和功能”,
Nature Immunology 8,no.9 (2007):950。
52. DD Gladman 等人,“银屑病关节炎 (PSA) 220 名患者的分析”,季刊
医学杂志62,第238期(1987):127。
53. AM Jensen 等,“卡泊三醇抑制银屑病表皮中过度增生的 CD29 阳性角质形成细胞的增生,但对抗原呈递细胞的功
能和数量没有影响”,英国皮肤病学杂志139,第 6 期(1998 年):984。
54. CA Elmets 等,“美国皮肤病学会‑国家银屑病基金会
《光疗治疗和治疗银屑病的护理指南》, 《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第 81 卷,第 3 期(2019 年):775。
55. RM Pujol 等,“中度至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心理健康自我评估
牛皮癣:西班牙 1164 名患者的观察性多中心研究 (VACAP 研究)”,
Actas Dermo‑Sifiliográficas 104,no。 10(2013):897‑903。
56. AC Bridgmen,“使用低剂量纳曲酮治疗寻常型银屑病”, 《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第 4 卷,第 8 期(2018 年 9
月):827–29。
57. G. Muller 等人,“复方低剂量纳曲酮治疗点滴状银屑病:病例报告”,国际药物配制杂志22 (2018): 270–78。
58.欧洲议会议员 Beltran,“低剂量纳曲酮:红皮病型银屑病的替代治疗方法”,
Cureus 医学科学杂志11,第 1 期(2019 年 1 月):3943。
59. PJ McLaughlin、JA Immonen 和 IS Zagon,“纳曲酮加速全层
通过刺激血管生成促进 1 型糖尿病大鼠伤口闭合”,实验生物学和医学,238,第 7 期(2013 年 7 月):733‑43。
第五章:帕金森病
1. Martin Parent 和 André Parent,“黑质与帕金森病:二者长期亲密关系简史”, 《加拿大神经科学杂志》第 37 卷,
第 3 期(2010 年 5 月):313–19, https://doi.org/10.1017/S0317167100010209; M. Gourie‑Devi,MG
Ramu 和 BS Venkataram,《‘阿育吠陀’(古印度医学体系)对帕金森病的治疗:讨论文件》, 《皇家医学会杂
志》 84,第 8 期(1991 年 8 月):491‑92。
2. Patricia Inacio,“弓形虫脑寄生虫调节帕金森氏症信号通路”,
帕金森新闻今日, 2017 年 9 月 20 日, https://parkinsonsnewstoday.com/2017/09/20/toxoplasma‑
brain‑parasite‑modulates‑signaling‑pathways‑common‑parkinsons‑disease ; C.
Warren Olanow 和 Patrik Brundin,“帕金森病和 α‑突触核蛋白:帕金森病是一种类似朊病毒的疾病吗?”,运动障碍杂志28 卷 1 期(2013 年 2
月):31–40, https: //doi.org/10.1002/mds.25373; Patrik Brundin 和 Ronald Melki,“探究帕金森病的朊病毒假说”,神经科学杂志37 卷 41
期(2017 年 10 月):9808–18, http://doi.org/10.1523/JNEUROSCI.1788‑16.2017; Leonid Breydo、Jessica W. Wu 和
Vladimir N. Uversky,“α‑突触核蛋白错误折叠和帕金森病”,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 (BBA) 1822,第 2 期 (2012):261–85, https: //
doi.org/10.1016/j.bbadis.2011.10 .002。
3. Maria G. Cersosimo 和 Eduardo E. Benarroch,“胃肠道疾病的病理相关性
帕金森病中的功能障碍”,神经生物学疾病46,第 3 期(2012 年):559–64, https://doi.org/10.1016/
j.nbd.2011.10.014 。
4. Christine Klein 和 Ana Westenberger,“帕金森病的遗传学”,冷泉港医学展望2,第 1 期(2012 年 1 月):
a008888, https://doi.org/10.1101/cshperspect.a008888 ; Anna Oczkowska 等人,“PRKN 和 SNCA 基
因突变对帕金森病进展至关重要”,当代基因组学14,第 8 期(2013 年 12 月):502–17, https://doi.org/
10.2174/1389202914666131210205839; DB Calne 等人,“MPTP 后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与帕金森
病病因相关的观察”, 《自然》 317(1985 年 9 月):246–48, https://doi.org/10.1038/317246a0; KJ
Billingsley 等人,“帕金森病的遗传风险因素”,细胞和组织研究373,第 1 期 (2018):9–20, https://doi.org/
10.1007/s00441‑018‑2817‑y; Petar Podlesniy 等人,“特发性和 LRRK2 相关帕金森病中线粒体 7S
DNA 的积累”,
EBioMedicine 48(2019 年 10 月):554–67, https://doi.org/10.1016/j.ebiom.2019.09.015。
5. Hiroyoshi Ariga 等人,“DJ‑1 在帕金森病中的神经保护功能”, 《氧化医学与细胞长寿》2013(2013 年 5 月):683920, https://doi.org/
10.1155/2013 /683920。
6. Ana Pena,“研究表明,LRRK2 值得成为帕金森病治疗研究的目标”,
帕金森新闻今日, 2018 年 5 月 3 日, https://parkinsonsnewstoday.com/2018/05/03/parkinsons‑lrrk2‑
mutation‑potential‑therapy‑target‑study‑suggests 。
7. David Sulzer 等人,“勘误表:帕金森病患者的 T 细胞识别 α‑
突触核蛋白肽”, 《Nature》 549,第 7671 期 (2017):292, https://doi.org/10.1038/nature23896;
Stephen Mullin 和 Anthony HV Schapira,“帕金森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致病机制”, Neurologic Clinics 33,
第 1 期 (2015):1–17, https://doi.org/10.1016/j.ncl.2014.09.010 ; Asa Abeliovich 和 Aaron D. Gitler,
“运输桥梁帕金森病病理学和遗传学中的缺陷”, Nature 539,第 7628 期 (2016):207–16, https: //doi.org/
10.1038/nature20414 ; “帕金森病与高铁摄入量有关”,美国神经病学学会,2003 年 6 月, https://
www.aan.com/PressRoom/Home/PressRelease/30;马西奥·S.
Medeiros 等人,“帕金森病中的铁和氧化应激:损伤生物标志物的观察性研究”, PLoS One 11,第 1 期(2016
年 11 月):e0146129, https://doi.org/10.1371 /journal.pone.0146129;Mike A. Nalls 等人,“NeuroX,
一种快速高效的基因分型平台
用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 《神经生物学老年学》 36 卷,第 3 期 (2015):1605.e7–1605.e12, https://
doi.org/10.1016/j.neurobiolaging.2014.07.028; Vera Dias、Eunsung Junn 和 M. Maral Mouradian,“氧化应
激在帕金森病中的作用”, 《帕金森病杂志》 3,第 4 期 (2013): 461–91, https://doi.org/10.3233/jpd‑130230;
Henry Jay Forman、Hongqiao Zhang 和 Alessandra Rinna,“谷胱甘肽:其保护作用、测量和生物合成概述”, 《分
子医学》第 30 卷,第 1‑2 期 (2009):1‑12, https: //doi.org/10.1016/j.mam.2008.08.006; Malú G. Tansey 和
Marina Romero‑Ramos,“帕金森病的免疫系统反应:早期和动态”, 《欧洲神经科学杂志》第 49 卷,第 3 期(2018
年 10 月):364–83, https://doi.org/10.1111/ejn.14290。
8. Gloria E. Meredith 和 David J. Rademacher,“帕金森病的 MPTP 小鼠模型:
更新”, 《帕金森病杂志》 1,第 1 期 (2011):19–33, https://doi.org/10.3233/JPD‑2011‑11023; J. William
Langston,“MPTP 的故事”, 《帕金森病杂志》 7,补编 1 (2017):S11–S19, https://doi.org/10.3233/
JPD‑179006; JW Langston,“哌替啶类似物合成产物导致人类慢性帕金森病”,科学219,no.
4587 (1983 年 2 月):979–80,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6823561; Serge Przedborski 等人,“MPTP 作
为帕金森病的线粒体神经毒性模型”, 《生物能量学与生物膜杂志》第 36 卷,第 4 期(2004 年 8 月):375–
79, https://doi.org/10.1023 /B:JOBB.0000041771.66775.d5;N . Schmidt 和 B. Ferger,“帕金森病 MPTP
模型中的神经化学发现”,《神经传递杂志》第 108 卷(2001 年):1263–82, https://doi.org/10.1007/
s007020100004。
9. Angela Spivey,“鱼藤酮和百草枯与帕金森病有关:人类暴露研究支持多年的动物研究”, 《环境健康展望》 119,第 6 期 (2011):A259, https://
doi.org/10.1289/ehp.119‑a259a; Elisa Caggiu 等人,“炎症、感染诱因和帕金森病”, Frontiers in Neurology 10 (2019), https ://doi.org/
10.3389/fneur.2019 .00122; Robert D. Abbott 等人,“中年牛奶消费量与死亡时黑质神经元密度”, Neurology 86,第 6 期(2015 年 9 月):
512–19, https://doi.org/10.1212/wnl .0000000000002254。
10. Michael A. Collins 和 Edward J. Neafsey,“帕金森病中的潜在神经毒性‘诱因’”, 《神经毒理学和畸形学》
24,第 5 期(2002 年 9 月 ‑10 月):571‑77, https://doi.org/10.1016/S0892‑0362(02)00210‑6; Edward A.
Lock、Jing Zhang 和 Harvey Checkoway,“溶剂和帕金森病:毒理学和流行病学证据的系统评价”,毒理学和应用
药理学266,第 3 期 (2013):345–55, https://doi.org/10.1016/j.taap.2012.11.016。
11. Seung‑Jae Lee 等人,“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蛋白质聚集体扩散:问题与观点”, 《神经科学研究》 70,第 4 期(2011
年):339–48, https://doi.org/10.1016/j.neures.2011.05.008 ; Michelle Smeyne 和 Richard Jay Smeyne,
“谷胱甘肽代谢与帕金森病”, 《自由基生物学与医学》 62(2013 年 9 月):13–25, https://doi.org/10.1016/
j.freeradbiomed.2013.05.001 。
12. Smeyne 和 Smeyne,“谷胱甘肽代谢和帕金森病。”
13. Shankar J. Chinta 等人,“成人多巴胺能中脑神经元谷胱甘肽水平的诱导性改变导致黑质纹状体变性”,《神经科学杂
志》第 27 卷,第 51 期(2007 年 12 月):13997–14006, https://doi.org/10.1523/JNEUROSCI.3885‑07.2007。
14. Carolina Cebrián 等人,“MHC‑I 表达使儿茶酚胺能神经元易受T 细胞介导的变性影响”, 《自然通讯》 5,(2014 年 4 月):3633, https: //doi.org/
10.1038/ncomms4633。
15.David Sulzer 等人,“帕金森病患者的 T 细胞识别 α‑突触核蛋白肽”, Nature 546,(2017 年 6 月):656–66,
https://doi.org/10.1038/nature22815。
16. Kemal Ugur Tufekci 等人,“帕金森病中的炎症”,蛋白质组学进展
化学与结构生物学88 (2012): 69–132, https://doi.org/10.1016/b978‑0‑12‑398314‑5.00004‑0 ; Li Qian、Patrick
M. Flood 和 Jau‑Shyong Hong,“神经炎症是帕金森病的关键因素,也是治疗的主要目标”,神经传递杂志117,第
8 期 (2010): 971–79, https://doi.org/10.1007/s00702‑010‑0428‑1; Zhichun Chen、Shengdi Chen 和 Jun
Liu,“T 细胞在帕金森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神经生物学进展169 (2018): 1–23, https://doi.org/10.1016/
j.pneurobio.2018.08.002; Sulzer 等人,“勘误表:帕金森病患者的 T 细胞”,292。
17. “攻击性免疫细胞加重帕金森病”, ScienceDaily, 2018 年 7 月 19 日, www
.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8/07/180719094349.htm。
18. Richard Gordon 等人,“小胶质细胞中的蛋白激酶 Cδ 上调驱动帕金森病实验模型中的神经炎症反应和多巴胺能神经变性”,神经生物学疾病93 (2016):
96–114, https://doi.org/10.1016/j.nbd.2016.04 .008。
19. Carolina Cebrián、John D. Loike 和 David Sulzer,“帕金森病动物模型中的神经炎症:细胞应激反应还是神经退行性病变的一个步骤?”,亨廷顿
病和帕金森病的行为神经生物学22 (2014):237–70, https://doi .org/10.1007/7854_2014_356; Fabio Blandini,“帕金森病
发病机制中的神经和免疫机制”,神经免疫药理学杂志8,第 1 期(2013 年 3 月):189–201, https://doi.org/10.1007/s11481‑013‑9435‑
y; Sara A. Ferreira 和 Marina Romero‑Ramos,“帕金森病期间的小胶质细胞反应:α‑突触核蛋白干预”, 《细胞神经科学前沿》
第 12 卷,第 247 期(2018 年 6 月), https://doi.org/10.3389/fncel.2018.00247 。
20. Tansey 和 Romero‑Ramos,“帕金森病中的免疫系统反应”;Susanne
Fonseca Santos 等人,“肠道与帕金森病 双向通路”, 《神经病学前沿》第10 期 (2019 年 4 月), https://
doi.org/10.3389/fneur.2019.00574; Ma gorzata Kujawska 和 Jadwiga Jodynis‑Liebert,“有什么证据表明
帕金森病是一种源自肠道的朊病毒病?” 《国际分子科学杂志》 19,第 11 期(2018 年 12 月):3573,
https://doi.org/10.3390/ijms19113573; Rodger A. Liddle,“从肠道看帕金森病”, Brain Research 1693
(2018): 201–06, https://doi.org/10.1016/j.brainres .2018.01.010; Olanow 和 Brundin,“帕金森病和 α‑突触
核蛋白”;Shakshi Sharma、Anupam Awasthi 和 Shamsher Singh,“帕金森病中肠道菌群和肠道通透性的改变:病
理学重点及治疗”, Neuroscience Letters 712 (2019 年 11 月):134516, https://doi.org/10.1016/
j.neulet.2019.134516。
21. Javier Campos‑Acuña、Daniela Elgueta 和 Rodrigo Pacheco,“T 细胞驱动的炎症作为与帕金森病有关的肠脑轴的
介质”,免疫学前沿10 (2019), https://doi.org/10.3389/fimmu.2019.00239。
22. Fredric P. Manfredsson 等人,“大鼠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肠神经系统中 α‑突触核蛋白病理诱导导致胃肠道运动障碍
和短暂性中枢神经系统病理”,神经生物学疾病112(2018 年 4 月):106–18, https ://doi.org/10.1016/
j.nbd.2018.01.008 。
23. Chen, Chen 和 Liu,“T 细胞在帕金森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24. Valentina Caputi 和 Maria Giron,“肠道‑脑‑微生物轴和 Toll 样受体在
帕金森病”,国际分子科学杂志19,第 6 期(2018 年 6 月):1689, https://doi.org/10.3390/ijms19061689;
Denise Barbut、Ethan Stolzenberg 和 Michael Zasloff,“胃肠道免疫和 α‑突触核蛋白”, 《帕金森病杂志》 9,
第 s2 期 (2019):S313–S322, https://doi.org/10.3233/jpd‑191702。
25. Laurie K. Mischley 等人,“鼻腔内给药的随机、双盲 I/IIa 期研究
帕金森病中的谷胱甘肽”,运动障碍30,第 12 期(2015 年):1696–701, https://doi.org/10.1002/mds.26351 。
26. Montserrat Marí 等人,“线粒体谷胱甘肽,一种关键的生存抗氧化剂”, 《抗氧化剂与氧化还原信号》 11,第 11
期 (2009):2685–700, https://doi.org/10.1089/ars.2009.2695。
27. Vicent Ribas、Carmen García‑Ruiz 和 Jose C. Fernandez‑Checa,“谷胱甘肽和
线粒体”, 《药理学前沿》第5 期(2014 年 1 月), https://doi.org/10.3389/fphar.2014.00151 。
28. RKB Pearce 等人,“帕金森病中黑质中谷胱甘肽分布的改变”,神经传递杂志104,第 6‑7 期 (1997):第 661‑77
页, https://doi .org/10.1007/bf01291884; Forman、Zhang 和 Rinna,“谷胱甘肽:其保护作用概述”;IP
Hargreaves 等人,“线粒体疾病患者的谷胱甘肽缺乏症:对发病机制和治疗的影响”,遗传代谢病杂志28,第 1 期
(2005):第 81‑88 页, https://doi.org/10.1007/s10545‑005‑4160‑1; Katalin Sas 等人,“线粒体、代谢紊乱、
氧化应激和犬尿氨酸系统,重点关注神经退行性疾病”,神经科学杂志257,第 1‑2 期 (2007):221‑39, https://
doi.org/10.1016/j.jns.2007.01.033。
29. Paul Held,“活性氧简介:细胞中 ROS 的测量”, Bio Tek Instruments, 2015 年 1 月 26 日, https://
www.biotek.com/assets/tech_resources /ROS%20White%20Paper_2015.pdf。
30. OW Griffith 和 A. Meister,“线粒体谷胱甘肽的起源和周转”,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82,第 14 期(1985 年 1 月):4668–72, https://doi.org/10.1073/pnas.82.14.4668 。
31. Mario Rango 和 Nereo Bresolin,“脑线粒体、衰老和帕金森病”, Genes 9,第 5 期(2018 年 11 月):250,
https://doi.org/10.3390/genes9050250。
32. Hansruedi Büeler,“帕金森病发病机制中线粒体动力学和功能受损”, 《实验神经病学》 218 卷,第 2 期
(2009):第 235–46 页, https://doi.org/10.1016/j.expneurol.2009.03.006 ; Vera Dias、Eunsung Junn
和 M. Maral Mouradian,“氧化应激在帕金森病中的作用”, 《帕金森病杂志》 3 卷,第 4 期 (2013):第 461–
91 页, https://doi.org/10.3233/jpd‑130230。
33. Sinee Weschawalit 等人,“谷胱甘肽及其抗衰老和抗黑素生成作用”,
临床、美容和研究皮肤病学2017,第 10 期 (2017 年 4 月):147–53, https://doi.org/10.2147/ccid.s128339 ;
Smeyne 和 Smeyne,“谷胱甘肽代谢与帕金森病”;Igor Rebrin 和 Rajindar S. Sohal,“衰老过程中谷胱甘肽
氧化还原状态中的促氧化剂转变”,高级药物输送评论60,第 13–14 期 (2008):1545–52, https://doi.org/
10.1016/j.addr.2008.06.001 ; Dikran Toroser 和 Rajindar S. Sohal,“小鼠肝脏中谷胱甘肽合成的年龄相关扰
动”,生化杂志405,第3(2007):583‑89, https://doi.org/10.1042/bj20061868; Honglei Liu
等人,“衰老和阿尔茨海默病过程中的谷胱甘肽代谢”,纽约科学院年鉴1019,第 1 期(2004 年):346–49,
https://doi.org/10.1196/annals.1297.059; J. Viña 等人,“衰老对谷胱甘肽代谢的影响。抗氧化剂的保护作
用”, 《自由基与衰老》 62 (1992): 136–44, https://doi.org/10.1007/978‑3‑0348‑7460‑1_14;
Tadayasu Furukawa、Simin Nikbin Meydani 和 Jeffrey B. Blumberg,“通过补充小鼠膳食中的谷胱甘肽
来逆转与年龄相关的免疫反应性下降”,《衰老与发育机制》 38,第 2 期 (1987):107–17,https: //doi.org/
10.1016/0047‑6374(87)90071‑6。
34. Sara Sepe 等人,“DNA 修复效率低下是与衰老相关的帕金森病修饰因素”,
Cell Reports 15, no. 9 (2016): 1866–75, https://doi.org/10.1016/j.celrep.2016.04.071; Chiara
Milanese 等人,“在突触核蛋白病模型中体内激活 DNA 损伤反应
帕金森病”,细胞死亡与疾病9,第 8 期 (2018):818, https://doi.org/10.1038 /s41419‑018‑0848‑7。
35. DJ Kurz,“慢性氧化应激损害端粒完整性并加速
人类内皮细胞衰老的开始”, 《细胞科学杂志》 117,第 11 期(2004 年 1 月):2417‑26, https://doi.org/
10.1242/jcs.01097; Consuelo Borrás 等人,“谷胱甘肽调节 3T3 成纤维细胞中的端粒酶活性”, 《生
物化学杂志》 279,第 33 期(2004 年 7 月):34332–35, https://doi.org/10.1074/jbc.m402425200。
36. Dean P. Jones 等人,“通过对人体血浆进行氧化还原分析,可以分离促氧化物
抗氧化防御能力下降引起的衰老事件”,自由基生物学和医学33,第 9 期 (2002):1290–300, https://doi.org/10.1016/s0891‑5849(02)01040‑7;
Marí 等人,“线粒体谷胱甘肽。”
37. Bernard Schmitt 等人,“N‑乙酰半胱氨酸、口服谷胱甘肽 (GSH) 和新型
舌下服用 GSH 对氧化应激标志物的影响:一项比较交叉研究”, Redox Biology 6(2015 年 12 月):198–205,
https://doi.org/10.1016/j.redox.2015.07.012; Furukawa、Meydani 和 Blumberg,“逆转与年龄相关的免
疫反应性下降。”
38. Robert A. Hauser 等,“静脉注射的随机、双盲、试点评估
帕金森病中的谷胱甘肽”,运动障碍24,第 7 期 (2009):979–83, https://doi .org/10.1002/mds.22401。
39. M. Otto、T. Magerus 和 JO Langland,“静脉注射谷胱甘肽用于帕金森病症状管理:病例报告”, 《健康与医
学替代疗法》第 4 期(2018 年 7 月):56–60。
40. Gianpietro Sechi 等人,“减少静脉注射谷胱甘肽在早期帕金森病治疗中的作用”, 《神经精神药理学和生物精神
病学进展》 20,第 7 期 (1996):1159–70, https://doi.org/10.1016/s0278‑5846(96)00103‑0。
41. Ines Elbini Dhouib 等人,“N‑乙酰半胱氨酸的简评:一种具有新药作用的老药
方法”,生命科学151(2016 年 4 月):359–63, https://doi.org/10.1016/j.lfs.2016.03.003; Edward A.
Lock、Jing Zhang 和 Harvey Checkoway,“溶剂和帕金森病:毒理学和流行病学证据的系统评价”, 《毒
理学和应用药理学》 266,第 3 期(2013 年):345–55, https://doi.org/10.1016/j.taap.2012.11.016。
42. A. Sharma 等人,“1‑甲基‑4‑苯基‑1, 2,3,6‑四氢吡啶诱导的
N‑乙酰半胱氨酸对小鼠黑质纹状体毒性的影响”,细胞与分子生物学53,第 1 期(2007 年 4 月):48–55;Negin
Nouraei 等人,“N‑乙酰半胱氨酸的治疗潜力研究以及用于定义体内黑质纹状体变性的工具”,毒理学与应用
药理学296(2016 年 4 月):19–30, https://doi.org/10.1016/j.taap.2016.02.010; Arman Rahimmi 等
人,“N‑乙酰半胱氨酸预防鱼藤酮诱发的大鼠帕金森病:对 Parkin 和 Drp1 蛋白相互作用的研究”,脑研究公报113
(2015 年 4 月):34–40, https://doi.org/10.1016/j.brainresbull.2015.02.007。
43. Mary J. Holmay 等人,“N‑乙酰半胱氨酸促进戈谢病和
Parkinson s Diseases”,临床神经药理学36,第 4 期 (2013):103–06, https: //doi.org/10.1097/
wnf.0b013e31829ae713 ; Hunter G. Moss 等人,“通过磁共振波谱测量缺氧缺血性脑病人类新生儿的 N‑乙
酰半胱氨酸快速补充中枢神经系统谷胱甘肽”,脑血流与代谢杂志38,第 6 期 (2018):950–58, https://doi.org/
10.1177/0271678x18765828; Jie Zhou 等人,“静脉注射稳定标记的 N‑乙酰半胱氨酸可间接促进谷
胱甘肽分泌并改善氧化还原状态”, 《药学杂志》 104,第 8 期 (2015):2619–26, https://doi.org/10.1002/
jps.24482。
44. Ajay S. Unnithan 等人,“利用 N‑乙酰半胱氨酸拯救两次打击、高通量神经退行性疾病模型”, 《国际神经化学》第
61 卷,第 3 期 (2012):356–68 页, https://doi.org
/10.1016/j.neuint.2012.06.001。
45. MM Banaclocha,“N‑乙酰半胱氨酸在与年龄相关的线粒体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治疗潜力”, 《医学假说》 56,第 4
期(2001 年):472–77, https://doi.org/10.1054/mehy.2000.1194 。
46. Joanne Clark 等人,“口服 N‑乙酰半胱氨酸可减轻 α‑突触核蛋白过度表达小鼠的多巴胺能终端丢失”, PLoS One 5,
第 8 期 (2010):e12333, https://doi.org/10.1371 /journal.pone.0012333。
47. Daniel A. Monti 等人,“N‑乙酰半胱氨酸与多巴胺能改善有关
帕金森病”,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106,第 4 期 (2019):884–90, https://doi.org/10.1002/cpt.1548 。
48. Todd B. Sherer 等人,“帕金森病鱼藤酮模型中的毒性机制”,
神经科学杂志23,第 34 期 (2003) : 10756–64, https://doi.org/10.1523/jneurosci.23‑34‑10756.2003 。
49. Barry Halliwell 和 John MC Gutteridge, 《生物学和医学中的自由基》 (牛津,
UK: Clarendon Press, 1989 年);Volodymyr I. Lushchak,“谷胱甘肽稳态和功能:医学干预的潜在靶点”, Journal of Amino Acids 2012(2012
年 2 月):736837, https://doi.org/10.1155/2012/736837; Young‑Sam Keum,“Nrf2 介导的 II 期解毒和抗氧化基因的调节”, 《生物
分子与治疗学》 20,第 2 期(2012 年 3 月):144–51, https://doi.org/10.4062/biomolther.2012.20.2.144; Young‑Joon Surh、Joydeb Kumar
Kundu 和 Hye‑Kyung Na,“Nrf2 作为主氧化还原开关,启动参与某些化学预防植物化学物质诱导细胞保护基因的细胞信号传导”, Planta
Medica 74,第 13 期 (2008):1526–39, https://doi.org/10.1055/s‑0028‑1088302 。
50. Yasushi Honda 等人,“谷胱甘肽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疗效:一项开放标签、单组、多中心、试点研究”, BMC
Gastroenterology 17(2017 年 8 月):96, https://doi.org/10.1186/s12876‑017‑0652‑3。
51. Rudie Kortekaas 等人,“体内帕金森病中脑的血脑屏障功能障碍”,
神经病学年鉴57,第 2 期 (2005):176–79, https://doi.org/10.1002/ana.20369; Annika Sommer 等人,
“Th17 淋巴细胞在基于人类 IPSC的帕金森病模型中诱导神经元细胞死亡”, Cell Stem Cell 24,第 6 期 (2019):1006,
https://doi.org/10.1016/j.stem .2019.04.019; Shaji Theodore 等人,“人类 α‑突触核蛋白的靶向过表达触发帕
金森病小鼠模型中的小胶质细胞活化和适应性免疫反应”, Journal of Neuropathology & Experimental Neurology
67,第 12 期 (2008):1149–58, https://doi.org/10.1097/nen.0b013e31818e5e99。
52. Dilini Rathnayake、Thashi Chang 和 Preethi Udagama,“选定的血清细胞因子和一氧化氮作为不同持续时间的帕金森
病的潜在多标志物生物特征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 BMC Neurology 19,第 1 期 (2019 年 4 月):56,
https://doi.org/10.1186/s12883‑019‑1286‑6 ; B. Adams 等人,“帕金森病:伴有细菌炎性原的全身性炎症疾病”,
Frontiers in Aging Neuroscience 11 (2019 年 8 月):210, https://doi.org/10.3389/fnagi.2019.00210;
Donghui Li 等人,“帕金森病相关疼痛与血浆白细胞介素‑1、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10 和肿瘤坏死因子‑α 的关系”,神
经科学快报683 (2018 年 9 月):181–84, https : //doi.org/10.1016/j.neulet.2018.07.027; Xiao‑Yan Qin
等人,“帕金森病患者外周炎症细胞因子水平异常: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 JAMA Neurology 73,第 11 期 (2016 年 11
月):1316–24, https://doi.org/10.1001/jamaneurol.2016.2742 ; M. Menza 等人,“炎性细胞因子在帕金森病的认知
和其他非运动症状中的作用”,心身医学51,第 6 期(2010 年 10 月):474–79, https://doi.org/10.1176/
appi.psy.51.6.474; Ryul Kim 等,“外周血炎症
《早期帕金森病的标志物》,《临床神经科学杂志》 58,(2018 年 12 月):30–33, https://doi.org/10.1016/
j.jocn.2018.10.079。 2018 年 10 月 24 日电子出版。
53. Doris Blum‑Degen 等人,“白细胞介素‑1β 和白细胞介素‑6 在
阿尔茨海默病和新生帕金森病患者的脑脊液”,神经科学快报202,第 1‑2 期 (1995):17‑20, https://doi.org/
10.1016/0304‑3940(95)12192‑7; Richard Gordon 等人,“小胶质细胞中的蛋白激酶 Cδ 上调驱动帕金森
病实验模型中的神经炎症反应和多巴胺能神经变性”, 《神经生物学疾病》第93 期(2016 年 9 月):
96–114, https://doi.org/10.1016/j.nbd .2016.04.008; T. Nagatsu 和 M. Sawada,“帕金森病死
后大脑的生物化学:历史概述和未来前景”,《神经精神障碍:综合方法》第 72 期(2007 年):113–20, https://
doi.org/10.1007/978‑3‑211‑73574‑9_14。
54. Stefan Liebner 等,“健康人血脑屏障的功能形态与
疾病”, Acta Neuropathologica 135 (2018): 311–36, https://doi.org/10.1007/s00401‑018‑1815‑ 1;
Javier Campos‑Acuña、Daniela Elgueta 和 Rodrigo Pacheco,“T 细胞驱动的炎症作为与帕金森病有关的肠
脑轴的介质”,免疫学前沿10(2019 年 2 月):239, https://doi.org/10.3389/fimmu.2019.00239。
55.Yuhua Chen 等,“伴有便秘的帕金森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和外周 T 细胞亚群”,国际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8,第 3 期
(2015 年):2495–504。
56. Michelle Block、Luigi Zecca 和 Jau‑Shyong Hong,“小胶质细胞介导的神经毒性:
揭示分子机制”, 《自然神经科学评论》第 8 期(2007 年):57–69, https://doi.org/10.1038/nrn2038 ; Bianca Marchetti 等人,“糖皮质
激素受体‑一氧化氮串扰和实验性帕金森病的脆弱性:神经胶质细胞‑神经元相互作用的关键作用”, 《脑研究评论》第 48 期第 2 期
(2005 年 4 月):302–21, https://doi.org/10.1016/j.brainresrev.2004.12.030 。
57. LJ Lawson 等人,“小胶质细胞在大脑中的分布和形态的异质性
正常成年小鼠大脑”, 《神经科学》 39 卷,第 1 期 (1990):151–70, https://doi.org/10.1016 /
0306‑4522(90)90229‑w; Doris Blum‑Degena 等人,“阿尔茨海默病和新生帕金森病患者脑脊液中白细
胞介素‑1β 和白细胞介素‑6 升高”,
神经科学快报202,第 1‑2 期 (1995):17‑20, https://doi.org/10.1016/0304‑3940 (95)12192‑ 7;M. Mogi 等
人,“帕金森病患者的脑纹状体中 β2 微球蛋白水平升高”,神经传递杂志 帕金森病和痴呆症第9 部分,第 1 期
(1995):87–92, https://doi.org/10.1007/bf02252965; Dariusz Koziorowski 等人,“帕金森病患者中的炎
症细胞因子和 NT‑ProCNP”,细胞因子60,第 1 期。 3(2012):762‑66, https://doi.org/10.1016/
j.cyto.2012.07.030; Thorsten Schulte 等人,“白细胞介素‑1 α 和 β 基因的多态性与帕金森病风险”,神经科
学快报326,第 1 期 (2002):70–72, https://doi.org/10.1016/s0304‑3940(02)00301‑4。
58. Iwona Kurkowska‑Jastrzebska 等人,“地塞米松防止帕金森病小鼠模型中的多巴胺能神经元损伤”,国际免疫
药理学4,no.
10–11 (2004 年 10 月):1307–18, https://doi.org/10.1016/j.intimp.2004.05.006; Vincenzo Di
Matteo 等人,“阿司匹林保护纹状体多巴胺能神经元免于神经毒素诱导的退化:一项体内微透析研究”,
Brain Research 1095,no. 1 (2006): 167–77, https://doi.org/10.1016/j.brainres.2006.04.013; Bin
Liu、Lina Du 和 Jau‑Shyong Hong,“纳洛酮通过抑制小胶质细胞活化和超氧化物生成保护大鼠多巴胺
能神经元免受炎症损伤”, 《药理学与实验治疗学杂志》 293,第 2 期(2000 年 5 月):607‑17;
Ashley S. Harms 等人,“延迟显性负性 TNF 基因疗法阻止帕金森病大鼠模型中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进行性
丧失”, 《分子治疗》 19,第 1 期(2011 年):46‑52,
https://doi.org/10.1038/mt.2010.217; Neha Sharma 和 Bimla Nehru,“Apocyanin,一种小胶质细胞
NADPH 氧化酶抑制剂,可预防脂多糖诱发的帕金森病模型中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分子
神经生物学53 (2016): 3326–37, https://doi.org/10.1007/s12035‑ 015‑9267‑2; Sushruta Koppula 等
人,“帕金森病实验模型中的活性氧和炎症酶、NADPH 氧化酶和 iNOS 抑制剂”,炎症介质2012(2012
年 4 月):823902, https://doi.org/10.1155/ 2012/823902; Richard Gordon 等人,“小胶质细胞中
的蛋白激酶 Cδ 上调驱动帕金森病实验模型中的神经炎症反应和多巴胺能神经变性”, 《神经生物学疾病》第
93 期(2016 年 9 月):96–114, https ://doi.org/10.1016/ nbd.2016.04.008。
59. Shu G. Chen 等人,“接触功能性细菌淀粉样蛋白 Curli 可增强
《老年 Fischer 344 大鼠和秀丽隐杆线虫中的 Alpha‑Synuclein 聚集》, 《科学报告》第 6 卷,第 1 期(2016
年 6 月):34477, https://doi.org/10.1038/srep34477; Timothy R. Sampson 等人,“肠道微生物群调节帕
金森病模型中的运动缺陷和神经炎症”, Cell 167,第 6 期 (2016):1469–80, https://doi.org/10.1016/
j.cell.2016.11.018; Heiko Braak 等人,“帕金森病相关脑病理学病例中迈斯纳神经丛和奥尔巴赫神经丛中
的胃 α‑突触核蛋白免疫反应性内含物”,神经科学快报396,第 1 期 (2006):67–72, https://doi.org/
10.1016/j.neulet.2005.11.012;凯瑟琳· M.
Shannon 等人,“早期未治疗的帕金森病患者的结肠粘膜下层中的 α‑突触核蛋白”,运动障碍27,第 6
期 (2011): 709–15, https://doi.org/10.1002/mds.23838; Heiko Braak 等人,“特发性帕金森病:脆弱
神经元类型可能受到未知病原体神经侵入的可能途径”,神经传递杂志110 (2003):517–36, https://
doi.org/10.1007/s00702‑002‑0808‑2。
60. Francisco Pan‑Montojo 等人,“环境毒素通过
“小鼠肠道神经元中 α‑突触核蛋白释放增加”,科学报告2,第 1 期(2012 年):898, https://doi.org/
10.1038/srep00898。
61. Theodore 等人,“人类 α‑突触核蛋白的靶向过度表达”;Anke Perren 等人,“FK506 减少基于 α‑突触核蛋白的
帕金森病大鼠模型中的神经炎症和多巴胺能神经变性”, 《神经生物学》第 36 卷,第 3 期 (2015):1559–68 页,
https://doi.org/10.1016/j.neurobiolaging.2015.01.014 。
62. Perren 等人,“FK506 减少神经炎症。”
63. Kazuhiro Imamura 等人,“帕金森病患者脑组织中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II 类阳性小胶质细胞的分布和细胞因
子谱”, Acta Neuropathologica 106,no.
6 (2003 年 1 月):518–26, https://doi.org/10.1007/s00401‑003‑0766‑2; Patrick L. McGeer 等人,“帕金
森病中的细胞死亡率表明活跃的神经病理学过程”,神经病学年鉴24,第 4 期 (1988):574–76, https://
doi.org/10.1002/ana.410240415。
64. Yasuomi Ouchi 等人,“帕金森病患者活体大脑中的神经炎症”,
Parkinsonism & Related Disorders 15,补编 2(2009 年 12 月):S25, https: //doi.org/10.1016/
s1353‑8020 (09)70109‑9; Denise K. Patten、Bob G. Schultz 和 Daniel J. Berlau,“低剂量纳曲酮在治疗
多发性硬化症、纤维肌痛、克罗恩病和其他慢性疼痛障碍中的慢性疼痛和炎症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Pharmacotherapy 38,第 3 期(2018 年):382–89, https://doi.org/10.1002/phar.2086; Alexander
Gerhard 等人,“利用 [11C](R)‑PK11195 PET 对特发性帕金森病中的小胶质细胞活化进行体内成像”,
《神经生物学疾病》 21 卷,第 2 期 (2006):404–12, https: //doi.org/10.1016/j.nbd.2005.08.002;
Yasuomi Ouchi 等人,“早期帕金森病中的小胶质细胞激活和多巴胺终末丢失”,神经病学年鉴57,第 2 期
(2005):168–75, https://doi.org/10.1002/ana.20338。
65. A. Roy 等人,“NEMO 结合结构域肽对小胶质细胞 RANTES 的衰减抑制了半帕金森病猴黑质中 CD8 T 细胞的浸润”,神经科学302(2015 年 8
月):36–46, https://doi.org/10.1016/j.neuroscience.2015.03.011; Goutam Chandra 等人,“中和 RANTES 和 Eotaxin 可防止帕金
森病小鼠模型中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丢失”, 《生物化学杂志》 291,第 29 期(2016 年 12 月):15267–81, https://doi.org/10.1074/
jbc.m116.714824。
66. Mona Sadeghian 等人,“沙芬酰胺在帕金森病 6‑羟基多巴胺模型中的神经保护作用”,神经病理学和应用神经生物学42,第 5 期 (2015):423–35,
https://doi.org/10.1111/nan.12263; Shi Zhang 等人,“CD200 ‑CD200R 功能障碍加剧帕金森病大鼠模型中的小胶质细胞活化和多巴胺能
神经变性”, 《神经炎症杂志》 8,第 1 期 (2011):154, https://doi.org/10.1186/1742‑2094 ‑8‑154。
67. Julie Rowin 等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治疗重症肌无力危象患者:对调节性 T 细胞的影响”,肌肉与神经46,第 3 期 (2012):449–53,
https://doi.org/10.1002/mus.23488; D. Games 等人,“通过免疫疗法减少 C 端截短的 α‑突触核蛋白可减弱帕金森病样模型中的神经变性和
增殖”,神经科学杂志34,第 28 期(2014 年 9 月):9441–54, https://doi.org/10.1523/jneurosci.5314‑13.2014 。
68. K. Noon 等人,“一种新型胶质细胞抑制剂,低剂量纳曲酮,可减轻疼痛和
抑郁症,并改善慢性疼痛功能:CHOIR 研究”, 《疼痛杂志》 17,第 4 期 (2016):S79, https://doi.org/10.1016/j.jpain.2016.01.395。
69. Jarred Younger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治疗纤维肌痛:一项评估每日疼痛水平的小型、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平衡、交叉试验的结果”,关节炎与风
湿病65,第 2 期 (2013):529–38, https: //doi.org/10.1002/art.37734; Bruce AC Cree、Elena Kornyeyeva 和 Douglas S. Goodin,
“低剂量纳曲酮与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生活质量的试点试验”,神经病学年鉴68,第 2 期 (2010 年 8 月), https: //doi.org/10.1002/ana.22006;
Jill P. Smith 等人,“阿片类拮抗剂纳曲酮治疗促进活动性克罗恩病的粘膜愈合:一项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消化疾病与科学》 56,第 7 期(2011
年 8 月):2088–97, https://doi.org/10.1007/s10620‑011‑1653‑7; Daniel J. Clauw、Lesley M. Arnold 和 Bill H.
McCarberg,“纤维肌痛的科学”, Mayo Clinic Proceedings 86,第 9 期(2011 年):907–11, https://doi.org/10.4065/mcp.2011.0206;
Jarred Younger 和 Sean Mackey,“低剂量纳曲酮可减轻纤维肌痛症状:一项初步研究”,《疼痛医学》第 10 卷,第 4 期 (2009):663–
72, https://doi.org/10.1111/j.1526‑4637.2009.00613.x; Brandon R. Selfridge 等人,“(+)‑纳曲酮激发的 Toll 样受体 4 (TLR4) 的
结构‑活性关系
Antagonists”,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58,第 12 期(2015 年 5 月):5038–52, https: //doi.org/10.1021/
acs.jmedchem.5b00426; Xiaohui Wang,“阿片类无活性异构体 (+)‑纳曲酮和 (+)‑纳洛酮作为 Toll 样受体 4 拮抗剂的药理学表征”,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171 (2017 年 2 月):e212, https: //doi.org/10.1016/j.drugalcdep .2016.08.580; Mark R. Hutchinson
等人,“纳洛酮和纳曲酮对神经性疼痛的非⽴体选择性逆转:Toll 样受体 4 (TLR4) 的参与”,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8,no. 1
(2008):20–29, https://doi.org/10.1111/j.1460‑9568.2008.06321.x; Luke Parkitny 和 Jarred Younger,“低剂量纳曲酮治疗纤维肌痛
八周后促炎细胞因子减少”, 《生物医学》 5,第 4 期(2017 年):16, https://doi.org/10.3390 /biomedicines5020016。
70. Guus Wolswijk,“慢性期病变中少突胶质细胞的存活、丢失和诞生
多发性硬化症”, Brain 123,第 1 期(2000):105–15, https://doi.org/10.1093/brain/123.1.105; Antoine Lampron 等人,“小胶质
细胞清除髓鞘碎片效率低下会损害
髓鞘再生过程”,实验医学杂志212,第4期(2015 年):481‑95, https://doi.org/10.1084/jem.20141656 ;
Elizabeth Gray 等人,“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白质中髓过氧化物酶活性升高”,神经科学快报444,第2期(2008
年):195‑98, https://doi.org/10.1016/j.neulet.2008.08.035 ; Judy SH Liu 等人,“多发性硬化症病变中诱
导型一氧化氮合酶和硝基酪氨酸的表达”,美国病理学杂志158,第6(2001):2057–66, https://doi.org/
10.1016/s0002‑9440(10)64677‑9; Marie T. Fischer 等人,“活动性多发性硬化症病变中 NADPH 氧化酶表达
与氧化性组织损伤和线粒体损伤的关系”, Brain 135,第 3 期 (2012):886–99, https://doi.org/10.1093/
brain/aws012 ; Marie T. Fischer 等人,“皮质多发性硬化症病变中的疾病特异性分子事件”, Brain
136,第 6 期 (2013):1799–815, https://doi.org/10.1093/brain/awt110 ; Thomas Zeis 等人,“早期多发
性硬化症中活动性脱髓鞘病变附近白质中的分子变化”, Brain Pathology 19,第 1 期3 (2009): 459–66,
https://doi.org/10.1111/j.1750‑3639.2008.00231.x。
71. M. Gironi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治疗原发性进展型多发性硬化症的试点试验”,多发性硬化症杂志14,第 8
期 (2008):1076–83, https://doi.org/10.1177/1352458508095828 ; Anthony P. Turel 等人,“低
剂量纳曲酮治疗多发性硬化症”,临床精神药理学杂志35,第 5 期 (2015):609–11, https://doi.org/10.1097/
jcp.0000000000000373 ; Cree、Kornyeyeva 和 Goodin,“低剂量纳曲酮试点试验”; Michael D. Ludwig
等人,“长期使用低剂量纳曲酮治疗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可维持稳定健康”,《多发性硬化症杂志实验、转化
和临床》 2 (2016):1‑11, https://doi.org/10.1177 /2055217316672242; Guttorm Raknes 和 Lars
Småbrekke,“低剂量纳曲酮治疗多发性硬化症:对药物使用的影响。一项准实验研究”,《 PloS One》 12,
第 11 期(2017 年 3 月),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87423; Michael
D. Ludwig、Ian S. Zagon 和 Patricia J. McLaughlin,“专题文章:多发性硬化症患者血清 [Met5]‑脑啡肽水平降
低,低剂量纳曲酮可恢复”, 《实验生物学与医学》 242,第 15 期(2017 年 2 月):1524–33, https://
doi.org/10.1177/1535370217724791。
72. Liu, Du 和 Hong,“纳洛酮保护大鼠多巴胺能神经元免受炎症
损害。”
73. Yuxin Liu 等,“纳洛酮⽴体异构体对β‑淀粉样肽(1‑42)诱导的
小胶质细胞中的超氧化物产生以及皮质和中脑神经元的退化”,
《药理学与实验治疗学杂志》 302,第 3 期(2002 年 1 月):1212–19, https://doi.org/10.1124/jpet.102.035956; Qingshan Wang 等人,“纳
洛酮通过与NADPH 氧化酶的 gp91 Phox 亚基直接相互作用抑制超氧化物产生,从而抑制免疫细胞功能”, 《神经炎症杂志》 9,第 1 期 (2012):32,
https ://doi.org /10.1186/1742‑2094‑9‑32。
74. Thomas Guttuso Jr.、Naomi Salins 和 David Lichter,“摘要 #13:低剂量纳曲酮对疲劳帕金森病患者的耐受性
和效果:一项开放标签研究”,
神经治疗学7,第 3 期(2010):332, https://doi.org/10.1016/j.nurt.2010.06.015。
75. Bernard Bihari,“低剂量纳曲酮可使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化”,《健康与医学替代疗法》第 19 卷,第 2 期(2013 年
3 月 ‑4 月):56‑65。
76. Xuan Liang 等人,“阿片类药物系统调节免疫功能:综述”,转化围手术期和疼痛医学1,第 1 期(2016 年 3 月):
5‑13;Jana Ninkovi 和 Sabita Roy,“Mu‑阿片类受体在阿片类药物调节免疫功能中的作用”,氨基酸45,第
1 期(2011 年):9‑24, https://doi.org/10.1007/s00726‑011‑1163‑0; Patricia J. McLaughlin 和 Ian S.
Zagon,“阿片类生长因子‑阿片类生长因子受体轴:细胞增殖的稳态调节剂及其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生化药理
学84,第 6 期 (2012):746–55, https: //doi.org/10.1016/j.bcp.2012.05.018。
77. Astrid Nehlig,“可可黄烷醇的神经保护作用及其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英国临床药理学杂志》 75,第 3 期
(2013 年 5 月):716–27, https: //doi.org/10.1111/j.1365‑2125.2012.04378.x; Paul W. Bosland,“辣
的东西 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们喜欢吃辣的食物吗?”《温度》 3,第 1 期(2016 年 2 月):41–42, https://
doi.org/10.1080/23328940.2015.1130521; PC Dinas、Y. Koutedakis 和 AD Flouris,“运动和体力活动对抑
郁症的影响”,爱尔兰医学科学杂志180,第 2 期 (2010):319–25, https://doi.org/10.1007/s11845‑010‑0633‑9;
Jan G. Veening 和 Henk P. Barendregt,“β‑内啡肽的作用:状态改变修饰”,中枢神经系统液体和屏障12,
第 1 期 (2015):3, https://doi.org/10.1186/2045‑8118‑12‑3;图尔库大学,“社交笑声释放大脑内啡肽” ,
神经科学新闻, 2017 年 6 月 2 日, http://neurosciencenews.com/endorphins‑social‑laughter‑6825;
Ji‑Sheng Han,“针灸和内啡肽”,神经科学快报361,第 1‑3 期(2004 年):258‑61, https://doi.org/
10.1016/j.neulet .2003.12.019; Tongjian You 等人,“太极拳对患有慢性疼痛的老年人的 β 内啡肽和炎症标
志物的影响:一项探索性研究”,老龄化临床和实验研究(2019 年), https://doi.org/10.1007/
s40520‑019‑01316‑1。
78. Helle Mørch 和 Bente Klarlund Pedersen,“β‑内啡肽和免疫系统 可能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作用”, Autoimmunity 21,第 3 期(1995 年):161–71, https://doi.org/10.3109 /
08916939509008013; TG Shrihari,“β‑内啡肽:疾病整体治疗中的抗炎活性”, EC Microbiology 14,第 11
期(2018 年 10 月):732–35, https://www.ecronicon.com/ecmi/pdf/ECMI‑14‑00557.pdf ;
Junichi Hosoi、Hiroaki Ozawa 和 Richard D.
Granstein,“β‑内啡肽结合和调节朗格汉斯细胞中的细胞因子表达”,
纽约科学院年鉴885,第 1 期(2006 年 6 月):405–13, https ://doi.org/10.1111/j.1749‑6632.1999.tb08700.x 。
79. Massimo Franceschi 等人,“帕金森病患者血浆 β‑内啡肽和 β‑促脂蛋白”,临床神经药理学第 9 卷,第 6 期
(1986 年):549–55, https://doi.org/10.1097/00002826‑198612000‑00006 ; G. Nappi 等人,“未
经治疗的帕金森病患者 β‑内啡肽脑脊液减少”,神经病学第 35 卷,第 9 期 (1985 年 1 月):1371, https ://doi.org/
10.1212/wnl.35.9.1371 ; H. Khalil 等人,“帕金森病患者血液中的血清素、β‑内啡肽和多巴胺水平及其与疼痛
感知的关系 [摘要]”,
运动障碍34,补充 2(2019 年), https://www.mdsabstracts.org/abstract/the‑circulatory‑levels‑
of‑serotonin‑beta‑endorphin‑and‑dopamine‑and‑their‑relations‑to‑pain‑perception‑in‑people‑
with‑parkinsons‑disease。
80. Jarred Younger 和 Sean Mackey,“低剂量阿司匹林可减轻纤维肌痛症状
纳曲酮:一项初步研究”, 《疼痛医学》第 10 卷,第 4 期 (2009 年):663–72, https://doi.org/10.1111/j .1526‑4637.2009.00613.x; Guttorm
Raknes 和 Lars Småbrekke,“更正:低剂量纳曲酮:对类风湿性和血清阳性关节炎药物的影响。一项基于全国登记册的对照准实验前后研
究”, 《PloS One》第 14 卷,第 10 期 (2019 年 1 月), https://dx.doi.org/10.1371%2Fjournal.pone.0223545; Kirbie M. Bostick、
Andrew G. McCarter 和 Diane Nykamp,“低剂量纳曲酮治疗慢性疼痛的应用”, 《高级护理药剂师》 34,第 1 期(2019 年 1 月):43–
46, https://doi.org/10.4140/tcp.n .2019.43。
81. Ketaki S. Bhalsing、Masoom M. Abbas 和 Louis CS Tan,“体育活动在
帕金森病”,印度神经病学学会年鉴21,第 4 期(2018 年 10 月至 12 月):242–49, https://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238554/; Barbara Pickut 等人,《帕金森病患者的正念训练:神
经行为影响》,
帕金森病2015 (2015): 1–6, https://doi.org/10.1155/2015/816404; Corjena Cheung 等人,“瑜伽对帕金
森病的氧化应激、运动功能和非运动症状的影响:一项初步随机对照试验”, 《初步与可行性研究》 4,
号。
1(2018):162, https://doi.org/10.1186/s40814‑018‑0355‑8; Sook‑Hyun Lee 和 Sabina Lim,“针
灸治疗帕金森病的临床疗效”, 《医学》 96,第 3 期(2017 年):e5836, https://doi.org/10.1097/
md.0000000000005836; Sujung Yeo 等人,“8 周针灸治疗对帕金森病患者的影响研究”, 《医学》
第 97 卷,第 50 期 (2018):e13434, https://doi.org/10.1097/md.0000000000013434 ; Jaung‑Geng Lin
等人,“电针促进帕金森病啮齿动物模型运动功能恢复并减少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国际分子科学杂志18,第
9 期 (2017):1846, https://doi。网址: Karishma Smart 等人,“帕金森病缓解的潜在案例”, 《补充与整合
医学杂志》第 13 卷,第 3 期(2016 年 1 月):311–15, https://doi.org/10.1515/jcim‑2016 ‑0019;
Marieke Van Puymbroeck 等人,《瑜伽随机试验后帕金森病的功能改善》, 《循证补充和替代医学》 2018
年(2018 年 3 月):1‑8, https://doi.org/10.1155/2018/ 8516351; Barbara A. Pickut 等人,“以
正念为基础的帕金森病干预导致MRI 上的脑结构变化”, 《临床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 115,第 12 期 (2013):
2419–25, https://doi.org/10 .1016/j.clineuro.2013.10.002; Long Zhang 等,“太极拳对不同人群的心理
效应综述”,循证补充和替代医学2012 年 (2012):1–9, https https://doi.org/10.1155/2012/678107;玛
德琳·E.
Hackney 和 Gammon M. Earhart,“舞蹈对重度帕金森病患者平衡和步态的影响:一个案例研究”,《残疾与康
复》第 32 卷,第 8 期(2009 年 8 月):第 679–84 页, https: //doi.org/10.3109/09638280903247905; ME
Mcneely、RP Duncan 和 GM Earhart,“舞蹈对帕金森病患者和健康老年人的非运动症状、参与度和生
活质量的影响”, 《Maturitas》第 82 卷,第 4 期(2015 年):第 336–41 页, https://doi.org/10.1016/
j.maturitas.2015.08.002 ; Gammon M. Earhart,《舞蹈作为帕金森病患者的治疗方法》, 《欧洲物理与康
复医学杂志》第 45 期第 2 期(2009 年 6 月):231–3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
19532110。
82. Stefania Kalampokini 等人,“帕金森病慢性炎症的非药物调节:饮食干预的作用”, 《帕金森病》 2019
年 (2019):1‑12, https://doi.org/10.1155/2019/7535472; Valentina Caputi 和 Maria Giron,“帕
金森病中的微生物‑肠‑脑轴和 Toll 样受体”, 《国际分子科学杂志》第 19 卷,第 6 期(2018 年 6 月):
1689, https://doi.org/10.3390/ijms19061689; Agata Mulak,“帕金森病中的脑‑肠‑微生物轴”,世界胃肠
病学杂志21,第 37 期 (2015): 10609, https://doi.org/10.3748/wjg.v21.i37.10609; Lisa
Klingelhoefer 和 Heinz Reichmann,“帕金森病的肠道和非运动症状”,国际神经生物学评论134 (2017): 787–
809, https://doi.org/10.1016/bs.irn.2017.05.027; Meng‑Fei Sun 和 Yan‑Qin Shen,“帕金森病中的
肠道菌群和微生物代谢物失调”,衰老研究评论45 (2018): 53–61, https://doi.org/10.1016/
j.arr.2018.04.004; Meng‑Fei Sun 等人,“粪便微生物移植对 MPTP 诱发的帕金森病小鼠的神经保护作用:肠道
微生物、神经胶质反应和 TLR4/TNF‑α 信号通路”, 《大脑、行为与免疫》70(2018 年 5 月):48–60,
https://doi.org/10.1016/j.bbi .2018.02.005; Feng Lai 等人,“甲基‑4‑苯基‑1,2,3,6‑四氢吡啶 (MPTP) 帕金
森病小鼠模型的肠道病理学和肠道微生物改变”,
神经化学研究43,第 10 期 (2018):1986–99, https://doi.org/10.1007/s11064‑018‑2620‑ x;Javier Campos‑
Acuña、Daniela Elgueta 和 Rodrigo Pacheco,“T 细胞驱动的炎症作为与帕金森病有关的肠脑轴的介质”,免
疫学前沿10 (2019), https://doi.org/10.3389/fimmu.2019.00239; Rodrigo Pacheco,“神经退行性疾病
中 T 细胞与肠道微生物群之间的相互作用”,神经再生研究14,第 12 期 (2019):2091, https://doi.org/
10.4103/1673‑5374.262582;牛小鲁等人,“患病率
中国帕金森病患者小肠细菌过度生长的影响”,神经传递杂志123,第 12 期 (2016 年 2 月):1381–86, https://doi.org/
10.1007/s00702‑016‑1612‑8 ; Zhi‑Lan Zhou 等人,“模拟禁食饮食通过肠道微生物群和代谢物对 MPTP 诱导的帕
金森病小鼠的神经保护作用”,神经治疗学16,第 3 期 (2019 年):741–60, https://doi.org/10.1007/
s13311‑019‑00719‑2。
83. Ai Huey Tan 等人,“帕金森病中的小肠细菌过度生长”,
帕金森病及相关疾病20,第 5 期 (2014):535–40, https://doi.org/10.1016/j.parkreldis.2014.02.019 。
84. Xiao‑Lu Niu 等,“小肠细菌过度生长的流行率。”
85. Luca Magistrelli 等人,“益生菌可能对帕金森病有益:体外证据”, 《免疫学前沿》第 10 期 (2019 年 7 月), https://
doi.org/10.3389/fimmu.2019.00969; Parisa Gazerani,“益生菌治疗帕金森病”, 《国际分子科学杂志》 20,第
17 期 (2019):4121, https://doi.org/10.3390/ijms20174121; E. Cassani 等人,“益生菌在帕金森病患者
便秘治疗中的应用”, Minerva Gastroenterologica e Dietologica 57, no. 2 (2011): 117–21, https://
www.ncbi.nlm.nih.gov /pubmed/21587143; Stefania Kalampokini 等人,“帕金森病慢性炎症的非药物
调节:饮食干预的作用”, Parkinson s Disease 2019 (2019): 1–12, https://doi.org/
10.1155/2019/7535472; Ma gorzata Kujawska 和 Jadwiga Jodynis‑Liebert,“有什么证据表明帕金森病是一
种源自肠道的朊病毒病?” 《国际分子科学杂志》 19,第 11 期(2018 年 12 月):3573, https://doi.org/
10.3390/ijms19113573; Ying Chen 等人,“肠脑轴中 α‑突触核蛋白的朊病毒样传播”,脑研究公报140
(2018):341–46, https://doi .org/10.1016/j.brainresbull.2018.06.002; Paula Perez‑Pardo 等人,“帕金森
病中的肠脑轴:基于食物的疗法的可能性”,欧洲药理学杂志817 (2017):86–95, https://doi.org/10.1016/
j.ejphar.2017.05.042; Dongming Yang 等人,“肠道微生物群在帕金森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神经病学前沿》
第 10 卷 (2019 年 6 月), https://doi.org/10.3389/fneur.2019.01155; Michal Lubomski 等人, “帕金森病与胃
肠道微生物组”, 《神经病学杂志》 2019, https://doi.org/10.1007/s00415‑019‑09320‑1 ; Sarah M.
O Donovan 等人,“大鼠帕金森病模型中黑质 α 突触核蛋白的过度表达表明肠神经系统和肠道微生物
组发生了改变”, 《神经胃肠病学与运动学》 32,第 1 期(2019 年 2 月), https://doi.org/10.1111/nmo.13726;
Visonneau Leclair 等人,“帕金森病中的肠道: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还是两者都不是?”, 《神经胃肠病学与运动》 32,
第 1 期 (2019), https://doi .org/10.1111/nmo.13777; Arthur Lionnet 等人,“帕金森病是从肠道开始的吗?”
Acta Neuropathologica 135, no. 1 (2017): 1–12, https://doi.org/10.1007/s00401‑017‑1777‑8; David K.
Simon、Caroline M. Tanner 和 Patrik Brundin,《帕金森病流行病学、病理学、遗传学和病理生理学》,《老年医学诊
所》 36,第 1 期 (2020):1–12, https://doi.org/10.1016/j.cger.2019.08.002。
86. Mitchell RKL Lie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用于诱导炎症性肠病患者缓解”,《转化医学杂志》 16 卷,第 1 期(2018 年 9
月):55, https://doi.org/10.1186/s12967‑018‑1427‑5; J. Ploesser、LB Weinstock 和 E. Thomas,“低剂量
纳曲酮:治疗胃肠道疾病的副作用和疗效”,《国际药物配制杂志》 14,第 2 期 (2010):171–73, https://
www.ncbi.nlm.nih.gov /pubmed/23965429。
87. Robert A. Hauser 等,“静脉注射的随机、双盲、试点评估
帕金森病中的谷胱甘肽”,运动障碍24,第 7 期 (2009):979–83, https://doi .org/10.1002/mds.22401。
第 6 章:儿科1.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
心,“儿童心理健康数据和统计”,
2019 年 4 月, https://www.cdc.gov/childrensmentalhealth/data.html。
2. Jon Baio 等人,“8 岁儿童自闭症谱系障碍患病率 自闭症和发育障碍监测网络,美国 11 个站点,2014 年”,
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监测摘要67,第 6 期(2018 年 4 月 27 日):1‑23。
3. 互动自闭症网络,《自闭症谱系障碍的诊断标准》,载于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5 版。
(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美国精神病学协会,2013 年),第 50‑51 页。
4. Baio 等人,“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患病率。”
5. 互动自闭症网络,“自闭症谱系障碍的诊断标准”,52。
6. Audrey Thurm 等人,“该领域的现状:区分智力障碍与自闭症
谱系障碍”, 《精神病学前沿》第 10 卷 (2019 年 7 月):526, https://doi.org/10.3389/fpsyt.2019.00526 。
7. M. Harada 等人,“使用临床 3 特斯拉仪器通过 MEGA 编辑质子 MR 波谱观察自闭症患者的 Gabaergic/谷氨酸系统无创评估”,
《自闭症与发育障碍杂志》第 41 卷,第 4 期(2011 年 4 月):447–54。
8. S. Braat 和 RF Kooy,“GABAA 受体作为神经发育障碍的治疗靶点”, 《神经元》 86 卷,第 5 期(2015
年 6 月):119–30。
9. Marvin Boris 等人,《MTHFR 基因变异与自闭症的关系》,《美国医学会杂志》
医生和外科医生9,第 4 期 (2004): 106–08。
10. David Rosenberg,“儿童和青少年强迫症: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表现、病程、评估和诊断”, UpToDate, https: //
www.uptodate.com/contents/obsessive‑compulsive‑disorder‑in‑children‑and‑adolescents‑epidemiology‑
pathogenesis‑clinical‑manifestations‑course‑assessment‑and‑diagnosis,最后编辑于 2019 年 6 月 7 日。
11. Sandra Meier 等人,“强迫症和自闭症谱系障碍:
《纵向和后代风险》, PLoS One,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41703。
12. Helen E. Vuong 等人,“肠道微生物组在自闭症谱系障碍中发挥的新作用”,
《生物精神病学》 81,第 5 期(2017 年 3 月):411–23;Jennifer G. Mulle 等人,“肠道微生物组:自闭症研究的新前
沿”, 《当前精神病学报告》 15,第 2 期(2013 年 2 月):337;SM O Mahony 等人,“血清素、色氨酸代谢和脑‑肠‑微
生物组轴”, 《行为脑研究》 277(2015 年):32–48。
13.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儿童焦虑和抑郁:了解
事实”,2019 年 4 月, CDC.gov。
14.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儿童心理健康数据和统计”,
2019 年 4 月, https://www.cdc.gov/childrensmentalhealth/data.html。
15. Jean‑Philippe Boulenger 等人,“恐慌症患者对咖啡因的敏感性增加
障碍。初步证据”, 《普通精神病学档案》 41,第 11 期(1984 年):1067–71。
16.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味精问答”
(味精)”,https: //www.fda.gov/food/food‑additives‑petitions/questions‑and‑answers‑monosodium
‑glutamate‑msg, 2012 年 11 月 19 日。
17. SE Jacob 和 S. Stechschulte,“甲醛、阿斯巴甜和偏头痛:可能的联系”,皮炎19,第 3 期(2008 年 5 月):E10–E11。
18. Karol Rycerz 和 JE Jaworska‑Adamu,“阿斯巴甜代谢物对星形胶质细胞和神经元的影响”, Folia
Neuropathologica 51,第 1 期(2013 年):10‑17。
19. Dana L. McMakin 和 Candice A. Alfano,“儿童晚期和青春期早期的睡眠与焦虑”, 《当代精神病学观点》第 28 卷,第 6 期
(2015 年 11 月):483–89 页。
20. TA Mellman 和 TW Uhde,《睡眠惊恐发作:新的临床发现和理论意义》, 《美国精神病学杂志》 146,第 9 期(1989 年 9 月):
1204‑07 页。
21. Cara A. Palmer 等人,“学龄焦虑儿童和非焦虑儿童的同睡:与睡眠变化和时间的关系”, 《异常儿童心理学杂志》第 46 卷,第 1 期,
2017 年。
6 (2018 年 8 月):1321–32。
22. Siri Carpenter 博士,《直觉》,美国心理学会第 43 卷,第 8 期(2012 年 9 月):第 50 页。
23.Pandasnetwork.org , “PANDAS/PANS 流行率”, http://pandasnetwork.org/statistics。
24. Maryann P. Platt 等人,“来自另一边的问候:自身抗体如何在自身免疫性脑炎中绕过血脑屏障”,免疫学前沿第 8 卷,第 442 期(2017
年)。
25. Carol Cox 等,“来自 Sydenham 舞蹈症的脑人类单克隆自身抗体靶点
转基因小鼠中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和多巴胺 D2 受体信号:对人类疾病的影响”,免疫学杂志191,第 11 期(2013 年 12 月):5524‑41;
Linor Brimberg 等人,“链球菌暴露后的行为、药理学和免疫学异常:Sydenham 舞蹈症和相关神经精神疾病的新型大鼠模
型”,神经精神药理学37,第 9 期(2012 年 8 月):2076‑87;Christine A. Kirvan 等人,“链球菌拟态和抗体介导的细胞
信号在 Sydenham 舞蹈症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自身免疫性39,第 1 期(2006 年 2 月):21‑29; Christine A. Kirvan 等人,“微管
蛋白是 Sydenham 舞蹈症中自身抗体的神经元靶点”,免疫学杂志178,第 11 期(2007 年 6 月):7412‑21。
26. HS Singer 等,“Sydenham 舞蹈症的神经元抗体生物标志物确定了一种新的
“链球菌感染后出现慢性复发性发作性抽搐和强迫症状急性加重的儿童群体”, PLoS One 10,第 3 期(2015 年 3 月):
e0120499。
27. PANDAS 医师网络,“基于症状严重程度的治疗”, https://www.pandasppn
.org/symptom‑severity。
28. Gina Chun Kost 等人,“克拉维酸通过增强囊泡运输的机制增加神经元细胞中的多巴胺释放”,神经科学快报504,第 2 期(2011 年 10
月):170‑75。
29. Jennifer Frankovich 等人,“儿童急性发作神经精神综合征治疗概述”,《儿童与青少年精神药理学杂志》第 27 期,第 7 期(2017
年 9 月)。
30. B. Muhammad 等人,“青少年原发性纤维肌痛综合征。一项针对 30 名
三名患者和匹配的正常对照”,关节炎和风湿病学,28,第 2 期(1985 年 2 月):137–45。
31. B. Muhammad 等人,“青少年原发性纤维肌痛综合征”。
32. B. Muhammad 等,“原发性纤维肌痛(纤维炎):50 名患者与正常对照者的临床研究”,关节炎和风湿病研讨会11,第 1 期(1981
年 8 月):151‑71。
33. J. Younger 和 S. Mackey,“低剂量纳曲酮可减轻纤维肌痛症状:
《疼痛医学》第 10 卷,第 4 期(2009 年 5 月):663–72。
第 7 章:女性健康1.“什么是子宫内膜异位症?”
子宫内膜异位症,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 2019 年 1 月更新, https://www.acog.org/patient‑resources/faqs/gynecologic‑problems/
endometriosis 。
2. N. Gleicher 等,“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吗?”妇产科70,
第 1 期(1987 年 7 月):115–22,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3110710。
3.“多囊卵巢综合征:ACOG 实践通讯摘要,第 194 号”,妇产科131,第 6 期(2018 年 6 月):1174–76, https://doi.org/
10.1097/AOG.0000000000002657。
4. Brigitte J. Roozenburg 等人,“成功诱导正常促性腺激素水平的排卵
通过联合纳曲酮和柠檬酸氯米芬治疗对氯米芬有抵抗性的无排卵女性”, 《人类生殖》12,第 8 期(1997 年 8 月):
1720–22, https://doi.org/10.1093 /humrep/12.8.1720。
5. L. Wildt 等人,“纳曲酮治疗下丘脑性卵巢功能衰竭:诱导
排卵和怀孕”, 《人类生殖》第 8 卷,第 3 期(1993 年 3 月):350–58, https://doi.org /10.1093/
oxfordjournals.humrep.a138050。
第 8 章:创伤性脑损伤
1. Suzanne Polinder 等人,“轻度创伤性脑损伤后脑震荡症状的多维方法”, 《神经病学前沿》第 9 期(2018 年 12 月):文章 1113, http: //
doi.org/10.3389/fneur.2018.01113。
2. Daniel Laskowitz 和 Gerald Grant 编辑,《创伤性脑损伤转化研究》 (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CRC Press/Taylor
and Francis Group,2016 年),2‑12。
3. Kathryn E. Saatman 等人,“创伤性脑损伤的分类及其针对性治疗”,
神经创伤杂志25,第 7 期(2008 年 7 月):719–38, https://doi.org/10.1089/neu.2008.0586。
4. Laskowitz 和 Grant, 《创伤性脑损伤转化研究》。
5. Laskowitz 和 Grant, 《创伤性脑损伤转化研究》。
6. Zoe M. Tapp、Jonathan P. Godbout 和 Olga N. Kokiko‑Cochran,“倾斜的轴:适应不良的炎症和 HPA 轴功能障碍导
致 TBI 后果”,神经病学前沿10(2019 年 4 月):第 345 篇文章, https://doi.org/10.3389/fneur.2019.00345。
7. David J. Sharp 和 Peter O. Jenkins,“脑震荡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困惑”, 《实用神经病学》 15 卷,第 3 期
(2015 年 6 月):172–86, https://doi.org/10.1136/practneurol‑2015‑001087。
8. Polinder 等人,“多维方法”。
9. Polinder 等人,“多维方法”。
10. Polinder 等人,“多维方法”。
11. Laskowitz 和 Grant, 《创伤性脑损伤转化研究》。
12. Polinder 等人,“多维方法”。
13. Jerrold R. Turner,“肠道粘膜屏障功能在健康和疾病中的作用”, 《自然免疫学评论》第 9 卷,第 11 期(2009 年 11
月):799–809, https://doi.org/10.1038/nri2653。
14. Mark EM Obrenovich,《肠漏,脑漏?》微生物学第 6 卷,第 4 期(2018 年 10 月):
107, https://doi.org/10.3390/microorganisms6040107。
15. Datis Kharrazian,《为什么我的大脑不工作?:对大脑的革命性理解》
衰退以及恢复大脑健康的有效策略(加利福尼亚州卡尔斯巴德:大象出版社,2013 年 7 月)。
16. Kharrazian,为什么我的大脑不工作了?
17. Gerwyn Morris 等人,“神经和精神疾病中的漏脑:驱动因素和
后果”,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精神病学杂志》第 52 卷,第 10 期(2018 年 10 月):924–48, https://doi.org/
10.1177/0004867418796955。
18. Kharrazian,为什么我的大脑不工作了?
19. Obrenovich,“肠漏,脑漏?”
20. Anthony Samsel 和 Stephanie Seneff,“草甘膦,现代疾病的途径 II:乳糜泻
腹泻和麸质不耐症”,跨学科毒理学,第 6 卷,第 4 期 (2013):159–84, https://doi.org/10.2478/intox‑2013‑0026 。
21. Obrenovich,“肠漏,脑漏?”
22. Kharrazian,为什么我的大脑不工作了?
23. Obrenovich,“肠漏,脑漏?”
24. Khalafalla O. Bushara,“乳糜泻的神经系统表现”,胃肠病学128,no.
4 (2005 年 4 月):S92–S97, https://doi.org/10.1053/j.gastro.2005.02.018。
25. David J. Wallace 等人,“脊髓损伤与人类微生物组:超越脑肠轴”, 《神经外科焦点》第 46 卷,第 3 期(2019 年 3 月):E11, https://doi.org/
10.3171/2018.12.FOCUS18206 。
26. Kiran V. Sandhu 等人,“微生物‑肠道‑脑轴:饮食、微生物组和
《神经精神病学》,转化研究179(2017 年 1 月):223–44, https://doi.org/10.1016/j.trsl.2016.10.002 。
27. Ana Agustí 等人,“肠脑轴、肥胖和认知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12(2018 年 3 月):第 155 篇文章, https://doi.org/10.3389/fnins.2018.00155 。
28. Julia König 等人,“人类肠道屏障功能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临床与转化胃肠病学7,第 10 期 (2016):e196,
https://doi.org/10.1038/ctg.2016.54。
29. Tapp,Godbout 和 Kokiko‑Cochran,《倾斜的轴》。
30. Tapp,Godbout 和 Kokiko‑Cochran,《倾斜的轴》。
31. Elisa Bisicchia 等人,“局灶性脑损伤后远端区域小胶质细胞的可塑性”,
细胞与发育生物学研讨会94 (2019 年 10 月):104–11, https://doi.org/10.1016/j.semcdb.2019.01.011 。
32. ME Tremblay 等人,“小胶质细胞在健康大脑中的作用”, 《神经科学杂志》第 9 卷,第 31 期(2011 年 11 月):
16064–69, https://doi.org/10.1523/JNEUROSCI.4158‑11.2011。
33. Sudhakar R. Subramaniam 和 Howard J. Federoff,“以小胶质细胞激活状态为靶点治疗帕金森病”, 《衰老
神经科学前沿》第 9 卷,第 176 期(2017 年 6 月), https://doi.org/10.3389/fnagi.2017.00176。
34. A. Dalgleish,《LDN 在癌症管理中的作用》,LDN 会议上发表的研究
AIIC 2018 大会,苏格兰格拉斯哥,2018 年 7 月 7 日。
35. Jarred Younger、Luke Parkitny 和 David McLain,“低剂量纳曲酮 (LDN) 作为慢性疼痛新型抗炎治疗的应用”,临
床风湿病学33,第 4 期(2014 年 4 月):451–59, https://doi.org/10.1007/s10067‑014‑2517‑2。
36. Jacqueline R. Kulbe 和 James W. Geddes,“轻度抑郁症中液体生物标志物的现状
创伤性脑损伤”,实验神经病学275,第 3 期(2016 年 1 月):334–52, https://doi.org/10.1016/
j.expneurol.2015.05.004 。
37. Si Yun Ng 和 Alan Yiu Wah Lee,“创伤性脑损伤:病理生理学和潜在治疗靶点”, 《细胞神经科学前沿》第 13
期(2019 年 11 月):第 528 篇文章, https://dx.doi.org/10.3389%2Ffncel.2019.00528。
38. Maria Teresa Viscomi,“可塑性的可塑性:从局部中枢神经系统损伤诱发的远端小胶质细胞中吸取的教训”,神经
再生研究15,第 1 期 (2020):57–58, https://doi.org/10.4103/1673‑5374.264448。
39. Xiangrong Chen 等,“补充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可减轻
通过抑制实验性创伤性脑损伤后的 HMGB1/TLR4/NF‑κB 通路来减轻小胶质细胞诱导的炎症”, 《神经炎症杂
志》 14,第 1 期(2017 年 7 月):第 143 篇文章, https://doi.org/10.1186/s12974‑017‑0917‑3。
40. Bisicchia 等人,“偏远地区小胶质细胞的可塑性。”
41. “生酮饮食”,载于《营养与创伤性脑损伤:改善军事人员的急性和亚急性健康结果》, John Erdman、Maria
Oria 和 Laura Pillsbury 编(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社,2011 年),第 11 页, https: //doi.org/
10.17226/13121。
42. Jama Lambert、Soledad Mejia 和 Aristo Vojdani,“植物和人类水通道蛋白:从肠道到大脑的发病机制”,免疫学研究67(2019 年 2 月):12–20,
https://doi.org/10.1007 /s12026‑018‑9046‑z。
43. Kharrazian,为什么我的大脑不工作了?
44. Heather M. Wilkins 和 Jill K. Morris,“调节神经退行性疾病线粒体功能的新疗法”, 《当代药物设计》 23 卷,
第 5 期 (2017):731–52, https://doi.org/10.2174/1381612822666161230144517。
45. “大脑基础:了解睡眠”,美国国⽴卫生研究院:美国国⽴卫生研究院
神经系统疾病和中风,最后更新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 https://www.ninds.nih.gov /Disorders/patient‑
caregiver‑education/Understanding‑sleep。
46. MS Cooper,“LDN、内体和自身免疫运动的纳米生理学
障碍。”该研究于 2019 年 6 月 7 日至 9 日在俄勒冈州波特兰举行的 LDN AIIC 2019 会议上发表, https: //
www.ldnresearchtrust.org/conference‑2019/ldn‑endosomes‑and‑nanophysiology‑autoimmune‑
movement‑disorders; Aamir Hadanny 等人,“高压氧疗法对创伤后脑损伤患者慢性神经认知缺陷的影响:回
顾性分析”, BMJ Open 8,第 9 期 (2018):e023387, https://doi.org/10.1136/bmjopen‑2018‑023387。
47. David J. Eve 等人,“高压氧疗法作为与创伤性脑损伤相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潜在治疗方法”, 《神经精神疾
病与治疗》第 12 卷(2016 年 10 月):2689–705, https://doi.org/10.2147/NDT.S110126。
48. Rahav Boussi‑Gross 等人,“高压氧疗法可改善脑震荡后
轻度创伤性脑损伤数年后的 IL‑12 综合征 随机前瞻性试验”, PLoS One 8,第 11 期(2013 年 11 月):
e79995,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79995。
49. Paul G. Harch 等人,“病例对照研究:高压氧治疗轻度创伤性脑损伤持续性脑震荡后综合症和创伤后应激障
碍”,
医用气体研究7,第 3 期(2017 年 10 月):156–74, https://doi.org/10.4103/2045‑9912.215745 。
第 9 章:分离性障碍1. David Spiegel 等人,
“DSM‑5 中的分离性障碍”,《抑郁和焦虑》第 28 卷,第 9 期(2011 年 9 月):824–52, http://doi.org/
10.1002/da.20874。
2. Marlene Steinberg, 《DSM‑IV 结构化临床访谈访谈员指南》
《分离性障碍:修订版》 (华盛顿特区:美国精神病学出版社,1994 年),11。
3.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5 版(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美国精神病学协会,2013 年);另请参阅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什
么是分离性障碍?”, https://www.psychiatry.org/patients‑families /dissociative‑disorders/what‑are‑dissociative‑disorders。
4. Emily A. Holmes 等,“是否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解离形式?
评论和一些临床意义”, 《临床心理学评论》 25,第 1 期(2005 年 1 月):1‑23, http://doi.org/10.1016/
j.cpr.2004.08.006。
5.Spiegel 等人,“DSM‑5 中的分离性障碍。”
6. Marlene Steinberg,《深入理解分离性障碍》, Psych Central,上
2020 年 1 月 14 日更新, http://psychcentral.com/disorders/dissociative‑identity‑disorder/in‑
depth。
7. Chris R. Brewin,“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ICD‑11 中的新诊断”,
BJPsych Advances (2019), 1–8, https://doi.org/10.1192/bja.2019.48。
8. Ulrich Lanius,“阿片类拮抗剂和解离:药物干预”,
创伤性分离的神经生物学和治疗:走向自我体现, Ulrich F. 编辑。
Lanius、Sandra L. Paulsen 和 Frank M. Corrigan(纽约:Springer,2014 年),第 471‑98 页。
9. Ulrich F. Lanius,“解离和内源性阿片类药物:基础作用”,
《创伤性分离的神经生物学和治疗》 ,Lanius、Paulsen 和 Corrigan 编辑,第 81‑104 页。
10. Henry Krystal, 《巨大的精神创伤》 (纽约:国际大学出版社,1968 年),
117.
11. Martin J. Bohus 等人,“纳曲酮治疗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的分离症状:一项开放标签试验”, 《临床精神病学杂志》
60,第 9 期 (1999):598–603, https://doi.org/10.4088/jcp.v60n0906; Christian Schmahl 等人,《纳曲酮对边缘
性人格障碍分离症状的评估》, 《国际临床精神药理学》 27 卷,第 1 期(2012 年):61–68。
12. Gad Lubin 等人,“纳曲酮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短期治疗:一项开放标签初步研究”,《人类精神药理学》第 17 卷,第 4 期
(2002 年):181‑85, http://doi.org/10.1002/hup.395 ; Ulrich F. Lanius,“EMDR 对分离性患者的处理:阿片类
拮抗剂的辅助使用”, 《EMDR 解决方案:治愈之路》,Robin Shapiro 主编(纽约:WW Norton,2005 年),
第 121‑46 页。
13. W. Pape 和 W. Wöller,“Niedrig Dosiertes Naltrexon in Der Behandlung Dissoziativer”
症状,” Der Nervenarzt 86 (2015): 346–51。
第 10 章:创伤后应激障碍1. Dean G. Kilpatrick 等人,“全国创
伤事件和 PTSD 暴露估计
使用 DSM‑IV 和 DSM‑5 标准评估抑郁症的患病率”,《创伤应激杂志》第 26 卷,第 5 期(2013 年):537–47,
https://doi.org/10.1002/jts.21848。
2. T. Karatzias 等人,“ICD‑11 PTSD 和复杂性 PTSD 的风险因素和共病:
基于英国受创伤人群样本的调查结果”,
《抑郁与焦虑》 36,第 7 期(2019 年 7 月): https://doi.org/10.1002/da.22934。
3. Jytte van Huijstee 和 Eric Vermetten,“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分离性亚型:临床和神经生物学特征研究更新”,载于
《PTSD 的行为神经生物学》,Eric Vermetten、Dewleen G. Baker 和 Victoria B. Risbrough 编辑(瑞
士卡姆:Springer International,2017 年),第 229–48 页。
4. Vincent J. Felitti 等人,“童年虐待和家庭功能失调与成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间的关系。不良童年经历 (ACE) 研究”,
美国预防医学杂志14,第 4 期 (1998):245–58, https://doi.org/10.1016 /S0749‑3797(98)00017‑8。
5. Bessel A. van der Kolk,“重复创伤的冲动”,北美精神病诊所12,第 2 期(1989 年):389–411, https://doi.org/
10.1016/s0193‑953x(18)30439‑8。
6. Marc Schmid 等人,“发育性创伤障碍:将正式标准纳入精神病诊断系统的利与弊”, BMC Psychiatry 13,第 3
期(2013 年 1 月): https://bmcpsychiatry.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1471‑244X‑13‑3。
7. Philip Hyland 等,“ICD‑11 PTSD、复杂性 PTSD 和
分离体验”, 《创伤与分离杂志》第 21 卷,第 1 期(2019 年 10 月):1‑11, https://doi.org/
10.1080/15299732.2019.1675113。
8. Hiroaki Hori 和 Yoshiharu Kim,《炎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精神病学和临床神经科学73, no. 4 (2019): 143–53, https://doi.org/10.1111/pcn .12820。
9. Joseph A. Boscarino,“创伤后应激障碍和身体疾病: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结果”, 《纽约科学院年鉴》 1032,第 1 期
(2005 年 1 月):141–53, https://doi.org/10.1196/annals.1314.011。
10. Aoife O Donovan 等人,“伊拉克和阿富汗自身免疫性疾病风险增加
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 《生物精神病学》 77,第 4 期(2015 年):365–74, https://doi.org/
10.1016/j.biopsych.2014.06.015。
11. Mark W. Miller 等,“慢性肾病中的氧化应激、炎症和神经进展
PTSD”, 《哈佛精神病学评论》 26,第 2 期(2018 年 4 月):57–69, htpps://
doi.org/10.1097/HRP.0000000000000167。
12. Martin R. Cohen 等,“人类应激中内源性阿片类药物系统的研究
反应”,载于《脑啡肽和内啡肽》 ,NP Plotnikoff 等人编辑(马萨诸塞州波士顿:Springer,1986 年);Paula
P. Schnurr 和 Bonnie L. Green,“理解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健康结果之间的关系”,载于《创伤与健康:
极端压力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Paula P. Schnurr 和 Bonnie L. Green 编辑(美国心理学会,2004 年),第
247–75 页, https://doi.org/10.1037/10723‑010; Ruth A. Lanius、Eric Vermetten 和 Clare
Pain 编辑,《早期生活创伤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隐藏的流行病》 (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 年),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777042。
13. Ulrich F. Lanius,“解离和内源性阿片类药物:基础作用”,
创伤性分离的神经生物学和治疗:走向自我体现, Ulrich F. 编辑。
Lanius、Sandra L. Paulsen 和 Frank M. Corrigan(纽约:Springer,2014),第 471‑98 页; J。
Douglas Bremner 和 Elizabeth Brett,“创伤相关的分离状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长期精神病理学”,《创
伤应激杂志》第 10 期(1997 年 1 月):37–4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9018676/。
14. Henry K. Beecher,《战争中受伤人员的疼痛》, 《外科年鉴》 123,第 1 期(1946 年):96–
105, https://doi.org/10.1097/00000658‑194601000‑00008。
15. RF Mucha,“纳洛酮和吗啡对豚鼠强直性静止状态的影响”,行为与神经生物学28,第 1 期 (1980):111–15,
https://doi.org/10.1016/s0163‑1047(80)93230‑6。
16. Jaak Panksepp, 《情感神经科学:人类和动物情感的基础》
(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年)。
17. Jaak Panksepp 和 Lucy Biven, 《心智考古学:人类情感的神经进化起源》 (纽约:WW Norton,2012 年)。
18. Claudia Regina Monassi、Andrade Leite‑Panissi 和 Leda Menescal‑de‑Oliveira,“腹外侧中脑导水管周围灰
质与强直性静止的控制”,《脑研究通讯》 50,第 3 期 (1999):201–08, https://doi.org/10.1016/
S0361‑9230(99)00192‑6。
19. Osamu Sakurada、Louis Sokoloff 和 Yasuko F. Jacquet,“局部脑葡萄糖利用
在大鼠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注射 β‑内啡肽后”,《脑研究》 153,第 2 期 (1978):403–07, https://doi.org/
10.1016/0006‑8993(78)90423‑7。
20. Monassi、Leite‑Panissi 和 Menescal‑de‑Oliveira,“导水管周围腹外侧灰质”。
21. Rebecca Valle、Negin Mohammadmirzaei 和 Dayan Knox,“单一长期压力改变
情绪学习和记忆过程中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和丘脑中线核的神经激活”, 《学习与记忆》 26 (2019): 403–11, https://doi.org/10.1101/
lm.050310.119 。
22. Francesca Farabollini 等人,“雄性和雌性大鼠对约束的免疫和神经内分泌反应”,心理神经内分泌学18,第 3
期 (1993):175–82, https://doi.org/10.1016 /0306‑4530(93)90002‑3。
23. A. Kling 和 Horst D. Steklis,“非人类的亲和行为的神经基础
灵长类动物”,大脑、行为和进化13,第 2‑3 期 (1976):216‑38, https://doi.org/10.1159 /000123811。
24. John D. Newman、MR Murphy 和 CR Harbough,《吗啡注射后纳洛酮可逆性抑制松鼠猴的隔离叫声产生 [摘
要]》 ,
神经科学8(1982):940。
25. Bessel A. van der Kolk,“发展性创伤障碍:对创伤的合理诊断
《具有复杂创伤史的儿童》, 《精神病学年鉴》 35,第 5 期(2005 年 1 月):401‑08, https://doi.org/
10.3928/00485713‑20050501‑06。
26. Allan N. Schore,“早期关系创伤对右脑发育、情感调节和婴儿心理健康的影响”,婴儿心理健康杂志22,第 1‑2 期
(2003):201‑69,https://doi.org/10.1002/1097‑0355(200101/04)22:1<201::AID‑IMHJ8>3.0.CO;2‑9。
27. KA Bonnet 等,“慢性阿片类药物治疗和社会隔离受体对啮齿动物大脑的影响”, 《阿片类药物和内源性阿片类
肽》, HW Kosterlitz 编辑(阿姆斯特丹:北荷兰出版社,1976 年)。
28. Schore,“早期关系创伤的影响”。
29. Kathleen T. Brady 等,“精神障碍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共病
Disorder”,临床精神病学杂志61,补编 7(2000):22–32;Deborah S. Lipschitz 等人,“住院青少年的创伤后应激
障碍:精神共病和临床相关因素”,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学会杂志38,第 4 期(1999):385–92, https://
doi.org/10.1097/00004583‑199904000‑00010。
30. Israel Liberzon 等人,“心理创伤后中枢 μ‑阿片受体结合改变”,
生物精神病学61,第 9 期(2007):1030–38, https://doi.org/10.1016/j.biopsych.2006.06.021 。
31. Ulrich F. Lanius 和 Frank. M. Corrigan,“阿片类拮抗剂和解离:辅助治疗
药物干预”,载于《神经生物学与创伤性分离治疗》,编辑。
Lanius、Paulsen 和 Corrigan,第 471‑98 页。
32. Monica Bolton 等,“安慰剂随机对照试验中报告的严重不良事件
口服纳曲酮试验: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 BMC Medicine 17,第 1 期 (2019), https://doi.org/10.1186/
s12916‑018‑1242‑0。
33. Martin J. Bohus 等人,“纳曲酮在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分离症状治疗中的作用”, 《临床精神病学杂志》 60,第 9
期 (1999):598–603, https://doi.org/10.4088/jcp.v60n0906; David Mischoulon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
对抗抑郁药突破性重度抑郁症症状患者的随机概念验证试验” ,情感障碍杂志208 (2017):6‑14, https : //doi.org/
10.1016/j.jad.2016.08.029; Wiebke Pape 和 Wolfgang Wöller,“Niedrig Dosiertes Naltrexon in Der
Behandlung Dissoziativer Symptome”, Der Nervenarzt 86,no。 3 (2014): 346–51, https://doi.org/
10.1007/s00115‑014‑4015‑9 。
34. Claudio Castellano 和 Stefano Puglisi‑Allegra,“纳洛酮和纳曲酮对
C57BL/6 和 DBA/2 小鼠的运动活动”,药理学生物化学和行为学16,第 4 期 (1982):561–63, https://doi.org/
10.1016/0091‑3057(82)90415‑4。
35. James Belluzzi 和 Larry Stein,“脑内啡:在长期记忆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纽约科学院年鉴398,第 1 期(1982 年):221–29, https://doi.org/10.1111/j.1749‑6632.1982.tb39496.x 。
36. ES Collin 等人,“к‑阿片受体刺激可消除 μ 而非 δ 介导的脊髓甲硫氨酸‑脑啡肽释放抑制控制”,神经科学快报134,
第 2 期 (1992):238–42, https://doi.org/10.1016/0304‑3940(92)90525‑c。
37. Liberzon 等人,“改变的中枢 μ‑阿片受体结合。”
38. Leigh McCullough 等编,治疗情感恐惧症:短期动态
心理治疗(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2003 年)。
39. Lanius 和 Corrigan,“阿片类拮抗剂和分离。”
40. Lanius 和 Corrigan,“阿片类拮抗剂和分离。”
41. Mark Hyman Rapaport 等人,“纳美芬增强治疗对神经安定剂稳定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有益作用”, 《神经
精神药理学》 9(1993 年 9 月):111–15, https://doi.org/10.1038/npp.1993.49。
42. Mischoulon 等人,“低剂量纳曲酮的随机概念验证试验。”
43. Revital Amiaz 等人,“使用纳曲酮治疗难治性抑郁症
帕罗西汀的增强作用 病例报告”,精神药理学143,第 4 期(1999 年):433–34, https://doi.org/10.1007/
s002130050969。
44. Daniel J. Siegel, 《发展中的心智:人际关系和大脑如何相互作用塑造我们》 (纽约:Guilford Press,1999 年)。
45. Luby Elliot 和 Mary Ann Marrazzi,“阿片类药物阻断引起的惊恐发作 案例研究”, 《临床心理学杂志》第 7 卷,第 5 期(1987 年 10 月):361,
https://doi.org/10.1097 /00004714‑198710000‑00025。
46. Lanius 和 Corrigan,“阿片类拮抗剂和分离。”
47. RB Hemingway 和 TG Reigle,“内源性阿片类药物系统在
习得性无助和压力引起的镇痛”,精神药理学93,第 3 期(1987 年), https://doi.org/10.1007/bf00187256。
第 11 章:莱姆病和其他蜱传疾病1. Christina A. Nelson 等人,“美国临床诊断莱
姆病的发病率,
2005–2010”,新发传染病21,第 9 期(2015 年 9 月):1625–31, https://doi.org/10.3201/eid2109.150417 。
2. Elisabeth Baum、Fong Hue 和 Alan G. Barbour,“莱姆病病原体伯氏疏螺旋体不同菌株对宿主物种
Peromyscus Leucopus的实验性感染”, mBio 3,第 6 期(2012 年 11 月至 12 月):e00434–12,
https://doi.org/10.1128/mBio.00434‑12 ; Kit Tilly、Patricia A. Rosa 和 Philip E. Stewart,“伯氏疏螺旋
体感染生物学”,北美传染病诊所22,第 2 期(2008 年 6 月):217–34, http://doi.org/10.1016/
j.idc.2007.12.013 。
3. CM Shih 和 A. Spielman,“部分进食媒介蜱加速莱姆病螺旋体的传播”, 《临床微生物学杂志》第 31 卷,第 11 期(1993 年 11 月):
2878‑81 页。
4. “莱姆病在全球 80 多个国家蔓延”,莱姆病协会,2013 年 8 月 27 日, https://lymediseaseassociation.org/about‑lyme/cases‑
stats‑maps‑a‑graphs/lyme‑in‑more‑than‑80‑countries‑worldwide 。
5. Lisa A. Waddell 等人,“妊娠莱姆病对妊娠妇女的影响的系统评价”
人类对胎儿和新生儿的影响”, PLoS One 13,第 11 期(2018 年 11 月):e0207067, https://doi.org/
10.1371/journal.pone.0207067 。
6. Raphael B. Stricker 和 Marianne J. Middelveen,“莱姆病的性传播:
挑战蜱传疾病范式”,抗感染治疗专家评论13,no.
11 (2015 年 8 月):1303–06, https://doi.org/10.1586/14787210.2015.1081056。
7. Lachlan McIver 等人,“气候变化对太平洋岛国健康的影响:区域脆弱性和适应重点评估”,《环境健康展
望》第 124 卷,第 11 期(2016 年 11 月):1707–14 页, https://doi.org/10.1289/ehp.1509756。
8. SM Engstrom、E. Shoop 和 RC Johnson,“免疫印迹解释标准
《早期莱姆病的血清诊断》, 《临床微生物学杂志》第 33 卷,第 2 期(1995 年 2 月):419–27。
9.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莱姆病”,最新更新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
https://www.cdc.gov/lyme/diagnosistesting/index.html。
10. Sam T. Donta,《晚期和慢性莱姆病》, 《北美医学诊所》第 86 卷,第 2 期
(2002 年 3 月):341–49, https://doi.org/10.1016/S0025‑7125(03)00090‑7。
11. Robert B. Nadelman 等人,“单剂量强力霉素预防肩突硬蜱叮咬后莱姆病”,新英格兰医学杂志345(2001 年
7 月):79–84, https://doi.org/10.1056/NEJM200107123450201。
12. Leena Meriläinen 等人,“伯氏疏螺旋体的形态和生化特征
多形性形式”,微生物学161,第 3 期(2015 年 3 月):516–27, https://doi.org/
10.1099/mic.0.000027。
13. RB Stricker 和 L. Johnson,“莱姆病:大数据的前景,同伴
诊断与精准医学”, 《感染与耐药性》 2016 年第 9 期(2016 年 9 月):215–19, http://doi.org/10.2147/
IDR.S114770。
14. Nadelman 等人,“单剂量强力霉素预防”,79–84。
15. Darin Ingels, 《莱姆病解决方案:对抗炎症自身免疫反应和战胜莱姆病的 5 部分计划》 (纽约:企鹅兰
登书屋,2018 年)。
16. AM Ercolini 和 SD Miller,“感染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作用”,临床与实验免疫学155,第 1 期(2008 年 12 月):1‑15, https://doi.org/10.1111/
j.1365‑2249.2008.03834.x 。
17. AC Steere 等人,“抗生素治疗耐药性莱姆病的自身免疫机制
《自身免疫学杂志》 16,第 3 期(2001 年 5 月):263‑68。
18. A. Pianta 等人,“膜联蛋白 A2 是抗生素耐药性莱姆关节炎患者滑膜成纤维细胞增殖相关的自身免疫 T 细胞和
B 细胞反应的靶点”,
临床免疫学160, no. 2 (2015 年 10 月):336–41, https://doi.org/10.1016/j.clim.2015.07.005 。
19. LH Sigal 和 S. Williams,“抗伯氏疏螺旋体鞭毛蛋白的单克隆抗体
体外改变神经母细胞瘤细胞的神经突发生:自身免疫在莱姆病神经病变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感染与免疫》 65,
第 5 期(1997 年 5 月):1722‑28。
20. R. Kaiser,“神经疏螺旋体病患者的鞘内免疫反应:抗体对神经元蛋白的特异性”,神经病学杂志242,第 5 期
(1995 年 5 月):319–25, https://doi.org/10.1007/bf00878875。
21. Kristen A. Rahn、Patricia J. McLaughlin 和 Ian S. Zagon,“预防和减少
低剂量纳曲酮 (LDN) 或阿片类生长因子 (OGF) 长期作用于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的表现:对多发性硬化症的治
疗意义”, Brain Research 1381(2011 年 3 月):243–53, https://doi.org/10.1016/
j.brainres.2011.01.036。
22. Jarred Younger 和 Sean Mackey,“低剂量纳曲酮可减轻纤维肌痛症状:一项初步研究”,《疼痛医学》
第 10 卷,第 4 期(2009 年 5 月):663–72, http://doi.org/10.1111/
j.1526‑4637.2009.00613.x。
附录:给药方案
1. Pierre Dayer、Jules Desmeules 和 Laurence Collart,“Pharmacologie du Tramadol [曲马多
药理学]”, Drugs 53,补编 2(2012 年 10 月):18–24, https://doi.org/
10.2165/00003495‑199700532‑00006。
2. Karlo Toljan 和 Bruce Vrooman,“低剂量纳曲酮 (LDN) 治疗学综述
利用”,医学科学第 6 卷,第 4 期(2018 年 9 月):82, https://doi.org/
10.3390/medsci6040082。
3.Toljan 和 Vrooman,“低剂量纳曲酮”。
4. Ginevra Liptan,“结合使用阿片类药物和阿片类阻滞剂可减轻纤维肌痛疼痛?”, 2016 年 3 月 7 日,
http://www.drliptan.com/blog/2016/3/7/combine‑opiate‑and‑opiate‑blocker‑for‑less‑
纤维肌痛‑疼痛。
5. Stewart B. Leavitt,《阿片类拮抗剂在疼痛管理中的应用》, 《实用疼痛管理》 9,
第3期(2011年12月)。
贡献者
Apple Bodemer,医学博
士Apple Bodemer 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皮肤科系的副教授。完成住院医师实习后,她在亚利桑那大学完成了
整合医学研究。她是第一位获得整合医学委员会认证的皮肤科医生,目前是美国整合医学委员会委员。她热爱教学,与
威斯康星大学的皮肤科住院医师以及威斯康星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整合医学研究员一起工作。她撰写了主要整合医学教
科书的章节,并为亚利桑那大学整合医学研究金计划以及国家退伍军人协会整体健康计划编写了课程。
除了学术教学外,她还致力于预防工作,并认为影响健康的最好方法是让人们
有能力自己掌握健康。她在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包括广播、电视和印刷品)与人们
互动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与多所学校合作,向儿童宣传皮肤癌预防知识。
她在这个领域的热情在于探索生活方式如何影响慢性病
以及急性皮肤病,特别注重饮食和营养。
Darin Ingels,ND,FAAEM,FMAPS Ingels 博
士是自然医学领域受人尊敬的领导者,拥有众多出版物、国际演讲以及近 30 年的医疗保健领域经验。他获得了普渡大
学的医学技术学士学位和巴斯德大学的自然疗法医学博士学位
华盛顿州西雅图大学,在巴斯蒂尔自然健康中心完成住院医师培训计划。他是美国环境医学科学院和儿科特
殊需求医学科学院的研究员。
Ingels 博士是《莱姆病解决方案:对抗炎症性自身免疫反应和战胜莱姆病的五步计划》(Avery,2018
年)一书的作者,书中介绍了一种治疗和管理莱姆病的综合性自然方法。他战胜了自己与莱姆病长达三年的斗
争,并在过去 20 年中将同样的原则应用于 6,000 多名莱姆病和合并感染患者。作为莱姆病领域的顶尖专家之
一,Ingels 博士曾多次出现在播客、文章和纪录片中。
Ingels 博士的执业重点是环境医学,特别关注莱姆病、合并感染和慢性免疫功能障碍。他使用饮食、营养、
草药、顺势疗法和免疫疗法治疗儿童和成人,以帮助患者获得更好的健康。
Galyn Forster,MS
Galyn Forster 是一名执业专业咨询师,自 1988 年起在俄勒冈州尤金执业。
他获得了俄勒冈大学心理咨询硕士学位。他为成年人、青少年和夫妻提供服务,重点关注各种问题,包括复
杂创伤、分离、焦虑、依恋问题、身体疼痛和创伤性脑损伤。
他的临床和理论取向兼收并蓄,着眼于将最新的神经生物学发现融入到他的治疗中。他的实践核心是眼
动脱敏和再加工疗法 (EMDR)、连贯性疗法、接受和承诺疗法 (ACT)、感觉运动疗法和 LENS 神经反馈。2010
年,他开始与患者合作,这些患者被处方低剂量纳曲酮作为心理治疗的辅助治疗。从那时起,他已经帮助 60 多
名客户探索 LDN 作为心理健康问题的辅助治疗,并在当地和国际上就该主题发表演讲。
Jill Cottel 医学
博士Cottel 博士是南加州人,在圣地亚哥长大。她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加州大学学士学位。
她于 1995 年获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UCSD) 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学位。她在 UCSD 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她
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完成了内科实习和住院医师培训,然后回到了阳光和家人向她招手的圣地亚哥。
Cottel 医生拥有 20 多年的内科经验,这使她目前专注于综合护理和整体健康。她于 2007 年成为美国整体医学综
合委员会的文凭获得者。最近移居弗吉尼亚州,她在临床实践中为患者看病,并担任约克镇 Lackey 诊所的医疗主任。
Kirsten Singler,NMD
Kirsten Singler 是肯塔基州青翠山丘的本地人。她向西迁移,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以优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
她在亚利桑那州西南自然疗法医学与健康科学学院获得自然疗法医学学位。在西南治疗艺术学院的 JoAnn Sanchez
的指导下,她获得了植物药和整体营养方面的额外培训和认证。她目前是加利福尼亚州 Lee 再生医学研究所的临床主
任和自然疗法医生。
她对自己作为临床医生和合作者的角色充满热情,帮助患者增强活力、能力和能量,实现他们的梦想。
Kristen Blasingame,文学硕士
Kristen Blasingame,文学硕士,曾在医疗领域担任过各种职务,特别是在医学研究和患者护理方面。Kristen 毕业于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并毕业于伊利诺伊州森林湖森林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她继续深造,
目前正在阿瓦隆大学攻读医学学位。2019 年 8 月,她与丈夫 Benton 结婚,两人的第一个孩子将于 2020 年 6 月出生。
闲暇时,Kristen 喜欢探亲、徒步旅行和合唱。
Leonard B. Weinstock,医学博士
Leonard B. Weinstock 博士是胃肠病学和内科的认证医师。他是胃肠病学专家和高级内镜中心的主席。他是临床副教
授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医学和外科专业。博士
温斯托克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佛蒙特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并获得了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的医学
学位。他完成了研究生培训,并担任罗彻斯特综合医院内科首席住院医师。他的胃肠病学研究是
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完成的。
Weinstock 博士是一位活跃的讲师,发表了 80 多篇文章、摘要、社论和书籍章节。他是
Sundance 临床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参与了 30 多项研究。他目前正在研究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在
不安腿综合征、肠易激综合征和酒渣鼻中的作用和治疗方法。低剂量纳曲酮治疗各种炎症疾病是
临床研究的主题。他对涉及胃肠道的新综合征很感兴趣,包括肥大细胞活化综合征。完整的简历
可在www.gidoctor.net 上找到。
Mark Mandel,药学博士Mark
Mandel 是一名注册药剂师,专门从事生物同质性激素替代疗法 (BHRT)、疼痛管理以及使用天然药物替代品和补充药
物 (CAM) 治疗慢性健康状况。自 2007 年以来,他一直是 LDN 的支持者,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和临床医生提供有关其
用途和潜在益处的咨询,并以各种形式和强度配制 LDN。
他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药学院 (1983),并于 2007 年在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的美国中西部
大学获得药学博士学位。他是每周广播健康节目《医生和药剂师》的主持人,该节目于美国中部时
间周六上午10 点在 WYLL AM 1160 播出,也可以在www.1160hope上在线收听
.com。
Mark 已为数百名药剂师学生讲授了 CAM、配药和耐用医疗设备等主题。他经常与医疗保健
专业人士交流,就天然药物替代品和处方配药如何改善患者护理和生活质量提供深刻见解。
马克认为,许多慢性健康状况可以通过补充对抗疗法来改善,甚至消除
天然药物替代品与生活方式改变的结合,易于使用、安全且有效。
Neel D. Mehta,医学博士
Mehta 博士是威尔康奈尔疼痛管理中心主任,也是威尔康奈尔医学院临床麻醉学副教授。他还担任综合脊柱护理中心联合主
任、Greenberg 14 South 便利设施部门医疗主任以及患者体验工作组和综合医学中心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他是纽约介入疼
痛医师协会的常务理事,也是东部疼痛协会的候任主席。
梅塔博士体现了威尔康奈尔的三重使命,提供优质的患者护理、开展开创性研究,并为疼痛医学领
域的在职培训医生提供培训。他的作品曾在电视和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播出。梅塔博士是美国神经病协
会 Facebook 患者聊天室的受邀专家,并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和印度孟买举办过课程,培训下一代国际
疼痛医学医师。
Mehta 博士致力于改善接受手术的患者体验,同时推动慢性疼痛和脊髓刺激领域的知识进步。他
撰写了 30 多篇同行评审的论文、章节和摘要。
Olga L. Cortez,医学博士,妇产科医生,FACOG
Olga L. Cortez 博士是一名获得委员会认证的妇产科医生,在 Cross Roads Hormonal Health & Wellness 为男性
和女性提供个性化护理。除了提供产科和妇科护理外,Cortez 博士还为男性和女性提供医学监督的减肥计划和激素疗
法。
Cortez 博士在北德克萨斯大学开始学习医学。她于 2002 年从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院获得医学
学位。Cortez 博士在达拉斯的 Parkland 纪念医院完成了实习和住院医师培训,在那里她为各个年龄
段的女性提供全面的护理。
完成医学培训后,Cortez 医生回到德克萨斯州丹顿开始行医并抚养孩子。多年来,她从
亲身经历减肥的困难和荷尔蒙失衡。
这使得她致力于帮助其他有同样问题的人。
此后,科尔特斯接受了激素和甲状腺管理方面的研究生培训。
作为每个人整体健康的热情倡导者,Dr.
Cortez 的目标是支持每位患者走向最佳健康状态。
Phil Boyle,医学博
士Boyle 博士是一名全科医生,特别关注不孕症、流产和女性健康。他是爱尔兰都柏林 Neo Fertility 的创始人和董
事。
Boyle 博士于 1992 年毕业于爱尔兰国⽴大学戈尔韦分校医学专业。他是爱尔兰全科医
师学院 (MICGP) 和皇家全科医师学院 (MRCGP) 以及爱尔兰生育协会的成员。他目前担任国
际恢复性生殖医学研究所(www.iirrm.org) 的主席,旨在发布和科学验证恢复性生殖的医生
团体。
自 1998 年开始行医以来,博伊尔医生已帮助 3,500 多对夫妇成功怀孕。他在同行评议的
医学期刊上发表了关于恢复性生殖治疗的论文,这些论文旨在治疗不孕症、先前试管受精失
败和反复流产的夫妇。自 2004 年以来,博伊尔医生一直为不孕症患者开具 LDN 处方,并已安
全地治疗了 500 多名怀孕期间使用 LDN 的女性。
Sarah J. Zielsdorf,医学博
士最重要的是,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是充满激情和活力的生活。Sarah Zielsdorf 博士就读于迈阿密大学
(俄亥俄州,不是佛罗里达州),获得了微生物学学士学位,辅修分子生物学和宗教研究,主修双簧管演奏。她在
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了公共卫生、微生物学和新发传染病硕士学位,并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斯特
里奇医学院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Z 博士在洛约拉大学和海因斯退伍军人医院完成了住院医师实习。她是功能
医学研究所认证的执业医师,也是内科委员会认证的医师。她很自豪能够为世界各地的患者服务,并迅速赢得了
既熟练的诊断师又充满热情的老师的声誉。她重视变革的力量
她深谙医患关系,并理解每个人在生化和遗传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Zielsdorf 博士每天都在磨练自己的技能,向患
者学习,并且永远不会满足于自己的知识基础。她坚信医学的艺术,这让她坚持不懈地寻找答案。
Zielsdorf 博士是 Motivated Medicine (www.motivatedmedicine.com) 的所有者兼医疗总监,芝加哥西
郊的一家创新咨询医疗机构。
J. Stephen Dickson BSC (hons) MRPharmS J.
Stephen Dickson 在英国与 LDN 合作了十多年,与业内的制药合作伙伴一起稳定供应链,并以安全合规的方式标
准化获取处方的方法。除了经营 Dickson Chemist 成熟的私人医疗部门外,他还在格拉斯哥经营着七家 NHS 药房。
Stephen 还从事其他几项业务,拥有一家科技公司,负责在社区药房 (MethaMeasure) 分发英国大部分美沙
酮,以及英国最大的在线管制药物系统之一 (CDRx)。他是 Canidol Pharmaceutics 公司的顾问,该公司致力于推动
英国医用大麻事业,并帮助设计了英国大麻诊所模型,供社区药房和初级保健使用。
闲暇之余,斯蒂芬在多个乐队(包括一个 ceilidh 乐队)中弹吉他,担任一个半专业剧团的董事会成员(他通常
担任服装专家),负责监督该剧团的 MethaMeasure 北美业务,并且经常在国际 LDN 会议上发表演讲。
Ulrich Lanius 博士Ulrich
F. Lanius 博士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温哥华的注册心理学家,从事临床和神经心理学工作。他对大脑行为关系以
及后天性脑损伤、创伤和分离的影响特别感兴趣。自 1999 年以来,他一直与被处方阿片类拮抗剂(包括各种剂量的纳曲
酮,包括低剂量纳曲酮 (LDN))的精神症状患者合作,并撰写了多篇关于该主题的书籍章节。
Lanius 博士专门从事创伤性脑损伤/轻度创伤性脑损伤的治疗干预,以及创伤应激综合征、分离和依恋相关问题的治
疗。Lanius 博士曾在北美和国际上发表演讲,他最近还撰写了一本关于创伤和分离的书。
Vivian F. DeNise,DO,ABAARM,FAARFM Vivian
DeNise 博士从事儿科医学已有 35 年,自 2009 年以来一直从事综合医学工作。虽然她一直热衷于照顾儿童,但当传
统疗法根本无效时,她敏锐地意识到需要探索其他治疗方式。
当时她开始在美国抗衰老医学会学习综合医学。她于 2009 年完成培训。DeNise 医生目前在纽约长岛从事儿科医疗
实践以及为各年龄段患者提供综合医疗服务。
DeNise 博士于 1980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霍夫斯特拉大学,获得生物学文学士学位。随后,她进入纽约骨科医学
院,并于 1984 年毕业。她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浸信会医疗中心完成了轮岗实习,并于 1988 年在纽约大学温思罗普医院
完成了儿科住院医师培训。她是美国抗衰老和再生医学学会的文凭获得者,并获得了美国抗衰老和再生医学学会的认
证。
Wiebke Pape 医学博
士Wiebke Pape 医学博士是德国巴特洪内夫莱茵医院(一家提供住院治疗的心身疾病诊所)创伤相关疾病科的高
级顾问。
她曾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医学。在神经病学、内科和精神病学领域接受医学教育后,她专攻精神病学、心身医学
和心理治疗。她完成了心理动力学和系统疗法方面的心理治疗教育,并且是一名经过认证的 EMDR 治疗师。她对治疗
患有复杂 PTSD 和严重分离症状的患者特别感兴趣。
出版物:W. Pape 和 W. Wöller,《低剂量纳曲酮在治疗分离症状中的应用》, Der
Nervenarzt 86(2015 年):346–52(德文)。
关于编辑
Linda Elsegood 是 LDN 研究基金会的创始人,该基金会于 2004 年在英国成⽴,是一家注册慈
善机构,她还是《LDN 书籍》第 1 卷和第 2 卷的编辑。2000 年 8 月,她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
症,并于 2003 年 12 月开始接受 LDN 治疗,现在她的生活质量更高,对未来充满希望。通过该基
金会,她为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患者、医生和药剂师提供了有关 LDN 的信息、文章和患者故事,并
帮助组织会议、研讨会和基金会的LDN 广播节目。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将书籍视为实现文化变革的工具,并致力于让公民参与恢复我们的全球公共资源并
成为其充满热情的管理者。如果您喜欢《LDN 书籍》第2 卷,请考虑阅读这些与健康和保健相关的其他优
秀书籍。
LDN 书籍,第 1 卷
一种鲜为人知的仿制药 低剂量纳曲酮 如何彻底改变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
疾病、癌症、自闭症、抑郁症等
编辑:LINDA ELSEGOOD 9781603586641
平装
卫生专业人员草药处方集,第 4 卷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和疼痛管理,包括认知和神经系统疾病以及情绪
状况
吉尔·斯坦斯伯里
9781603588560
精装
一切都在你的嘴里生物牙科和口腔健康
对全身健康的惊人影响DR. DOMINIK NISCHWITZ 9781603589543 平装本
无谷物、无糖、无乳制品家庭食谱
简单又美味的食谱,适合在节食期间使用全食烹饪
莉亚·韦伯
9781603587594
平装
阿尔茨海默症的解药
利用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饮食对抗阿尔茨海默病、记忆力减退和认知能力下降
艾米·伯杰
9781603587099
平装
癌症的代谢途径整合深度营养、生酮饮食和无毒生物个体化疗法
DR. NASHA WINTERS 和 JESS HIGGINS KELLEY 9781603586863 精装
癌症与水的新生物学
托马斯·考恩
9781603588812
精装
生物调节医学自我修复的创新整体方法DR.
DICKSON THOM、DR. JAMES PAUL MAFFITT ODELL、DR.
JEOFFREY DROBOT、DR. FRANK PLEUS 和 JESS HIGGINS KELLEY 9781603588218 平装本
|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加入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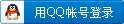
×
StarCareHome
本平台医疗信息及相关内容(含个案及研究结论)仅供参考,不构成诊疗、医学建议或疗效保证,相关结论可能存在争议。补剂/药品仅限成分分析(不涉品牌),用户自担使用相关内容、产品及外部链接风险;干预或用药前请咨询执业医师。
|